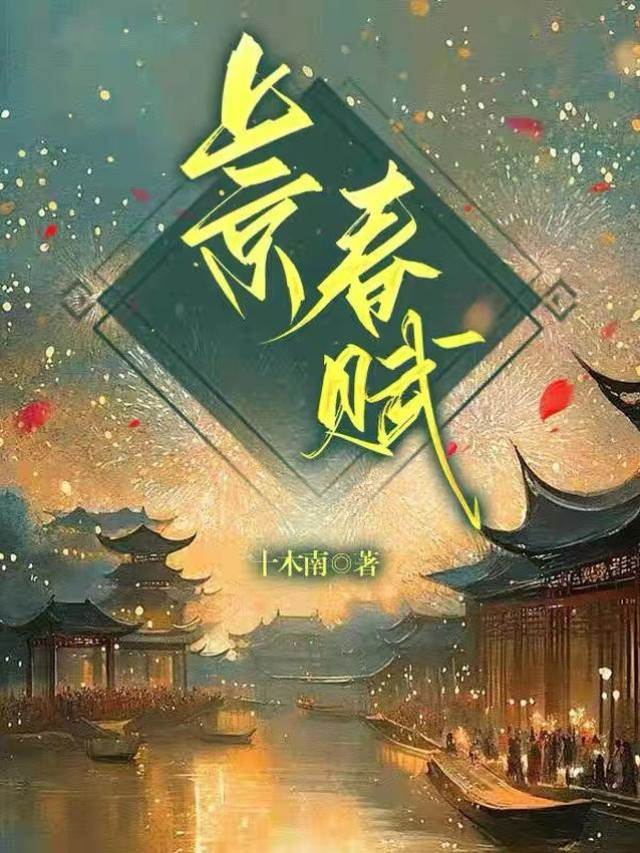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世子他為何如此黏人/世子清冷但纏人》 第9章
第9章
巳時末,章家的門房葛康提著食盒拿著令牌一路穿過奉天門、午門和皇極門,繞過文淵閣進到了閣。章鶴的值房在二樓右側,與首輔劉炳的值房相鄰。葛康與幾位書辦打過照面後上了樓,沒走兩步,遇上了尚膳監的祿太監翟公公。翟公公後跟著五六個提食盒的小太監。葛康立刻退後避讓,翟公公笑著頷了頷首,徑直領人離開了。
一直等人走出了閣,葛康才直起。他在原地站了一會兒,再次上樓。到章鶴值房門前,葛康先輕輕敲了敲門,了嗓子道:“老爺,夫人讓奴才給您送飯來了。”
“哦,進來吧。”
葛康輕手輕腳地開了門,躬彎腰走到方桌旁,打開食盒把飯菜一一揀拾出來。他走到還在埋首書案的章鶴旁道:“老爺,您請用飯。”
章鶴擱下筆,著山起走到方桌前坐下。他掃了一眼飯菜,聳著胡須笑了:“呦,還有燒鵝。”
葛康殷勤地遞上銀箸,將幾道菜往章鶴面前推了推:“夫人心疼您這幾日勞累得,特地命人趕早去買的蘇州白鵝,現殺現燒,您嘗嘗,鮮著呢!奴才提著的這一路上,都怕自個兒的口水滴上去呢。”
章鶴夾了塊嘗嘗,贊許地點了點頭,但還是叮囑道:“回去告訴夫人,家中用度,能省則省,鵝價貴,以後別再買了。”
葛康笑著應下了。見章鶴吃下去大半碗飯了,葛康左右看看,打開食盒最底下一層,將一細小竹筒雙手捧給了章鶴,幾乎是在用氣音說話:“老爺,這是馮軍爺送來的,湖廣那案子的結果,世子審出來了。”
章鶴眉心一跳,立刻擱下筷箸接過打開,出了裏面的字條,確實是宋硯的字跡。章鶴快速掃了一遍,眉頭的川字紋越皺越深。他起打開一旁的燈罩,將字條燒去,負手在背來回走。真正與那匪寨來往的是駐紮在荊州府的邊軍衛所……其中一個衛所是楚王齊信手底下的三大護衛軍之一。楚王要謀反?
Advertisement
章鶴立刻沖向門,卻在手掌到門板的一瞬停了腳步。他收回手,側問:“此事剛上報給大理寺?”
“是,但奴才估計隔壁那位也已經知道了……奴才來的時候正巧撞見了翟公公。”
翟公公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馬志才手底下的人,天底下有幾件事瞞得過馬公公?
章鶴閉了閉眼,幽嘆一聲。大理寺未出終審結果,通政司就不會將奏章遞進閣。就是遞,也有可能直接遞進劉炳的府邸裏去。去年周經業狀告一案便是如此,如果不是徐公公及時派人知會了他,恐怕連他都要被蒙在鼓裏,更不要說呈至陛下面前了。這回是宋硯命人第一時間將消息遞來的,但還是晚了一步,可見劉炳和馬志才在朝野外的滲勢力已經超出想象了。
估計是什麽時候他們收拾好了首尾,什麽時候聖上才能知道結果。不過這件事,他們收拾得了嗎?
近兩年湖廣借修漕運、修葺城牆、修整兵備等理由讓戶部撥去了至有兩百萬兩的銀子,戶部尚書與劉炳是滁州老鄉,同年進士,是劉炳一路提拔上去的,這銀子你分分我分分都進了誰的腰包,人人都清楚。一旦順藤瓜地查下去,沒一個能摘得幹淨。他們收拾不了。
章鶴抿,有了決定,轉回到書案前,命葛康磨墨,筆疾書寫了一份奏章,人快快送到司禮監秉筆兼東廠廠督太監徐亦手中去。
若徐亦能及時從中阻止并收集證據,告知聖上真相,他們說不準還能占得一點先機。
出了京城城門,宋硯縱馬疾馳,不過半個時辰就到了京郊山下的一片林中。穿過這片林,後面就是宋氏宅院,那個名義上專門買來給侯夫人養病,實則是用以關押他母親的莊子。宋硯翻下馬,立在林中,目一寸寸過林間空隙,想就這麽一直到莊子盡頭。
Advertisement
上次來見娘親,還是三年前他剛中武舉魁首的時候。那時他騎的也是這匹馬,一路躲著所有可能跟蹤他的人,張又迫切地趕來這。他翻進莊子,一間房一間房地找過去,找了一下午,終于在天黑之前過一扇小小的木窗,看見了那個他自六歲起便再沒能見過一面的娘親。
他是的孩子,可除了那十個月外,他待在邊的日子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從他存在伊始,就注定會是個被母親憎恨一生的孩子。
他還記得那天他穿的是嶄新的皂勁裝,背上背著的是牛皮膠制的羽箭。手裏拿著最好的弓,腰間懸著太合劍。那時他還很稚,他以為他長大了,足夠厲害了,能夠殺掉所有迫害娘親的人了。他以為只要殺了他們,他就能帶去一個沒有壞人的地方,為一個被母親著的孩子。他以為他不被,只是因為自己太弱小、太笨拙。
他心如擂鼓地跳進木窗,站在快要被遠山完全吞沒的夕下,著那個披頭散發窩在角落玩泥娃娃的人,像無數次睡夢中演習的那樣,一遍遍地喚娘。張開,卻發不出聲音,唯有眼淚一顆一顆往下砸。他跑向,說娘,阿墨救你,阿墨帶你走,阿墨會很乖很乖什麽都聽娘的,娘,你別不要阿墨。
人像驚的兔子,瞪著通紅的眼睛不停地尖。吼他、嚇他、打他、咬他。宋硯輕地抱著,依賴地著,可越喚,越狂躁,最後拔出一簪子,捅向了他的心口。
他是無人能敵的年魁首,他知道握住簪子時要做什麽,他知道他會死。他不願躲開,他想就這麽死在娘親手裏。可他終究沒能死。
宋硯捂住心口,著肋骨之下那總不知停歇的搏,有一重更比一重深厚的悲哀侵襲了他的五髒六腑。自那之後,關押娘親的房間裏有了捆縛手腳的鐵鎖鏈,連玩泥娃娃都沒得玩了。父親說,他的就是對最好的刑罰。
Advertisement
他再不會像十四歲時那樣橫沖直撞地去救娘親了。可他做不到不,他是的孩子,他生來就是注定要的。
如果他的是刑罰,那他對他們的恨呢?是恩賜吧。他會把此生無窮無盡的恨,都賜予他們。
宋硯著莊子的方向,在心裏回憶著娘親的模樣。他張合雙,輕輕地道:“娘親,阿墨有喜歡的人了,像你說的那樣,不管見不見得到,都會一直想著。我好想,也好想你。”
天黑之前,宋硯坐馬車回到了定國公府。碧霞閣是死一般的沉寂。從他踏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朝他看去,神不一,卻都有一致的麻木。秦老太太沉著臉盯他步步走上前來行禮。
年在面前總是沒什麽表,也沒什麽緒,偶爾才會乖巧地笑一笑。秦老太太對此一直很滿意。但現在一想到他這副無波無瀾的模樣之下實則藏有一顆忤逆的心,就恨不得親手折了他的反骨。
宋津說,宋硯審出了那個擱淺了快有一年的案子,這案子是牽一發而全,足以震整個朝野。審案的過程中,他拿鐵水灌弄死了一個囚犯,另外兩個被他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什麽見見髒就會嘔吐不止當場昏厥,本就是假的。這些年他真是演得好辛苦!
之前答應宋津會設法讓宋硯知難而退的孟博瀚,竟就這麽順水推舟地讓他審出來了,從此以後宋家別想在朝局中獨善其了。而宋硯,往後不僅會有章鶴為他作保,還會有東廠為他助力。他正在離他們的掌控。
見宋硯垂首立在底下,秦老太太緩了緩臉,聲道:“阿墨,祖母今天再最後勸你一次,你把刑部的差推了去,下個月回都督府任職。聽話,祖母都是為你好。”
“我在刑部辦案,究竟有什麽不好?”
“你還要與祖母裝糊塗嗎?別的不說,這正六品和正四品,能一樣嗎?”
宋硯擡眸,靜靜與對視著,黑漆漆的瞳仁裏沒有半分緒。他笑了下:“是像祖母和母親,也到底是不一樣的,對嗎?”
秦老太太的臉驟然白了,須臾後開始發青。了拳,在扶手上重重捶了一下,桌幾上盛著湯羹的碗盞被震落在地,嚇得在旁服侍的幾個婢都如遭大難般發著抖跪在地上,不敢彈分毫。
宋津立即起,朝宋硯喝道:“你怎麽跟祖母說話的?給我跪下!”
宋硯依言跪下,仍然是平時乖覺聽話的模樣。
秦老太太被氣得頭腦一陣陣犯昏。原來隔著一層緣的孩子,終究是養不的。他親娘那樣待他,從沒給過他一一毫的母溫,他的心都能永遠向著;呢,從他才掌點大的時候就帶在邊了,一點一點養這麽大,什麽都給他籌謀好,不用他半點心,可他就是偏要和設想的反著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農門醫妃:妖孽王爺纏上門
天師世家第八十八代嫡傳弟子阮綿綿因情而死,死後穿越到大秦朝的阮家村。睜開眼恨不得再死一次。親爹趕考杳無音訊,親娘裝包子自私自利,繼奶陰險狠毒害她性命,還有一窩子極品親戚虎視眈眈等著吃她的肉。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姐弟三個過得豬狗不如。屋漏偏逢連陰雨,前世手到擒來的法術時靈時不靈,還好法術不靈空間湊。阮綿綿拍案而起,趕走極品,調教親娘,教導姐弟,走向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可是誰來告訴為什麼她路越走越寬,肚子卻越走越大? !到底是哪個混蛋給她下了種?桃花朵朵開,一二三四五。謊話一個個,越來越離譜。俊美皇商溫柔地說:那一夜月黑風高,你我有了魚水之歡。妖孽皇子驕...
32.6萬字7.73 30934 -
連載1973 章

3歲小萌寶:神醫娘親,又跑啦!
“娘親,你兒子掉啦!”小奶包抱緊她的大腿,妖孽美男將她壁咚在墻上:“娘子,聽說你不滿意我的十八般武藝?想跑?”沈云舒扶著腰,“你來試試!”“那今晚娘子在上。”“滾!”她本是華夏鬼手神醫、傭兵界的活閻王,一朝穿越成不受寵的廢物二小姐。叔嬸不疼,兄妹刁難,對手算計,她手握異寶,醫術絕代,煉丹奇才,怕個毛!美男來..
177.8萬字8 17475 -
連載1305 章

和離后毒妃帶三寶顛覆你江山
虐渣+追妻+雙潔+萌寶新時代女博士穿成了草包丑女王妃。大婚當天即下堂,她一怒之下燒了王府。五年后,她華麗歸來,不僅貌美如花,身邊還多了三只可愛的小豆丁。從此,渣男渣女被王妃虐的體無完膚,渣王爺還被三個小家伙炸了王府。他見到第一個男娃時,怒道“盛念念,這是你和別人生的?”盛念念瞥他“你有意見?”夜無淵心梗,突然一個女娃娃頭探出頭來,奶兇奶兇的道“壞爹爹,不許欺負娘親,否則不跟你好了,哼!”另一個女娃娃也冒出頭來“不跟娘親認錯,就不理你了,哼哼。”夜無淵登時跪下了,“娘子,我錯了……
231.7萬字8.18 9007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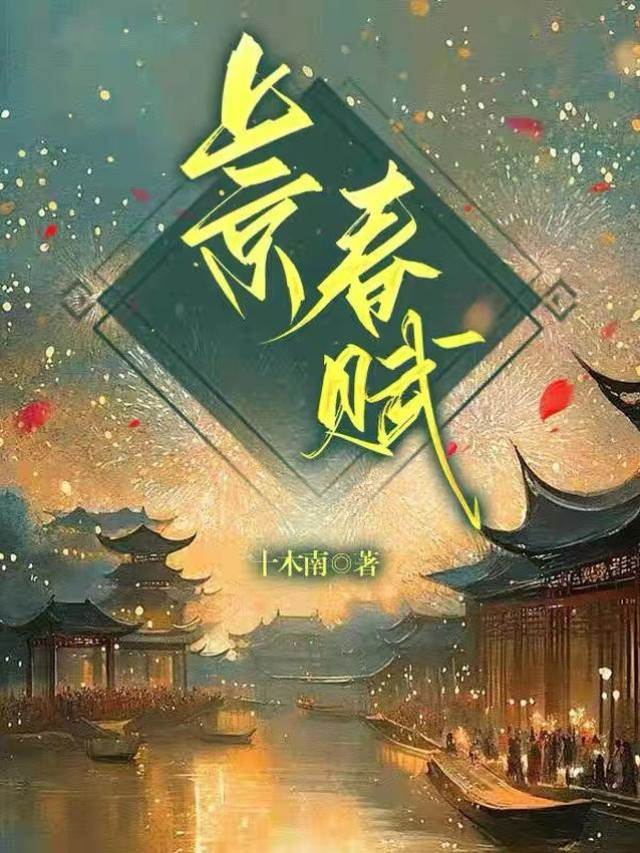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