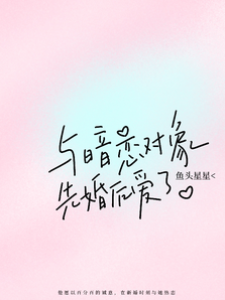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被渣后我嫁入頂級豪門》 第7章 你救了我,就當兩清了
時綏出聲之前已經有了作,幾乎想也沒想,朝幾步之外的傅時聿撲過去。
然而男人作更快,在撲過來的同時拽著的手一起退了出去,車子幾乎著兩人側嗖地沖過去,撞到了旁邊的花壇,發出巨大的撞擊聲后,停下。
時綏閉著眼,雖然沒有意料中的疼痛,卻還是臉煞白,止不住的抖。
“沒事了。”
男人聲音啞了幾分,抬手拍了拍的背。
得到安,時綏這才睜開眼,發現兩人正躺在地上,自己被他護在懷里,趕起,擔心自己傷他,“您沒事吧?”
傅時聿搖了搖頭,看并無大礙,站起朝邁赫走去,司機跌跌撞撞地下了車,看見傅時聿,嚇得一臉驚惶,“爺,你沒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剎、剎車突然失靈了……”
傅時聿朝急匆匆趕來的保鏢看了眼,容冰冷,“去哪了?”
保鏢低頭,“抱歉,我們去了洗手間。”
“兩人同時去?”
兩名保鏢互看了一眼,不說話。
傅時聿冷厲的眼神朝兩人掃了一眼,最終也沒說什麼,拿起手機打了個電話。十分鐘后,來了兩輛車。
一輛警車,一輛傅家的勞斯萊斯。
駕駛座上走下來一個寸頭的年輕男人,下車后先和警察說了幾句,然后走到傅時聿面前,恭敬道,“爺,這里給警察。”
傅時聿瞥了那司機一眼,徑自走上后座。
年輕男人上了駕駛座,轉頭問,“您現在回南苑?”
“嗯。”傅時聿應了一聲,這才想起什麼,車窗緩緩落下,狹長的眸幽幽掃了過來,“還不上車?”
時綏回過神,這才反應他是對自己說。
Advertisement
掙扎了一下,還是上了車,不為別的,好像看到他白襯衫上染了紅。
應該是當時為了救弄傷了。
傅時聿臉轉向一邊,看著車窗,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時綏也不敢打擾他。
剛才發生的事如果只是意外的話,那也太巧了。他明明也覺到了,可似乎并不在意,又好像習以為常。
就在時綏以為他到南苑之前都不會開口說話時,他忽然轉過臉,像是隨意問了句,“住哪?”
“什麼?”
“住在哪里?送你回去。”
時綏對上男人漆黑平靜的眸,愣了愣。
突然發現一件糟糕的事,自己本無可去。
自從被凌周救起來后一直住在凌周給準備的公寓里,昨天被他匆匆帶到了會所,甚至連一件換洗服都沒有拿。
如今也不可能再回去。
被傅時聿這麼一問,才想到自己困窘的境。
沉默了近一分鐘,時綏下定決心道,
“不用了,經過市中心的時候把我放下就行。”
傅時聿視線從臉上收回,邊掀起薄薄的弧度,不置可否。
然而經過市中心的時候,他卻并沒有讓停車,時綏也只能著頭皮當作不知。
當車子停在南苑門口,傅時聿才對著年輕男人說了句,“小九,去查一下司機和那兩名保鏢,最近和誰有過接。”
傅九頷首,“是。”
接著皺眉想了下,還是說出口,“以后還是我跟著爺吧。”
傅時聿勾著薄,無所謂的點頭。傅九本來就跟著他,最近不過是被他派去保護傅文舒。
現在傅文舒已經沒事了,倒也用不著傅九親力親為。
那兩名保鏢,不過是傅容禮派到他邊盯著他,其名曰是保護,其實說白了不過是監視,好讓他知道自己兒子干的第一手好事。
Advertisement
然而保鏢不跟在雇主邊,讓雇主傷,這是失職,傅家容不下只收錢不干活的人,正好有個借口換人。
“那我先去警局了解下況。”
說完就離開了。
偌大的別墅里,只剩下了兩人。
時綏心跳的厲害,男人雖然背對著站著,可高大的影仍然給帶來了無形的迫。抿了抿,視線落在他染的袖口,干的道,“我幫您理一下傷口吧。”
指了指他的袖子。
傅時聿這才注意到襯衫上的跡,起一看,左臂上手肘有一傷,因為襯衫的掀開傷口又被扯出了。
然而這點傷對于他來說不值一提,甚至都沒有覺到痛意,于是他挽起袖子,不在意道,“不用了。”
時綏堅持,“藥箱在哪?”
兩人對峙了數秒。
傅時聿先收回眼神,邊挽起袖子邊道,“廚房左邊第二個柜門。”
時綏了大掛在椅背上,走過去取了藥箱,找出碘酒和棉球。
回客廳時,傅時聿已經坐在沙發里,單手點擊著筆記本的鍵盤,時綏撇了一眼,屏幕上全是一條條波浪線,看不懂。
坐在他邊,把碘酒開蓋,然后倒了些在棉球上,隨后捧起他的手臂,看了傷口一會兒,才用棉球輕輕拭消毒。
作輕,帶著些小心翼翼,傅時聿甚至能到鼻尖的呼吸。
在的一下又一下的作間,男人頸后的神經繃,結略略滾了一下,好不容易挨到結束,他猝不及防地收回了手。
時綏不在意他的冷淡,輕聲囑咐,
“還好,不算嚴重,但是也不能水,這樣才能好得快。”
男人挑起眉,覺得有點大驚小怪。
Advertisement
然而此刻氛圍太好,以至于話到邊又咽了回去,只狀似無意地問了句,“你似乎對理傷口很有經驗?”
時綏淡笑,“也許以前經常幫人理傷口吧。”
不記得以前,但好像確實對于理傷口這件事比別人更上手一些。
傅時聿以為在說凌周,臉淡下來。
天已經黑,離休息卻還有兩三個小時,因為任務在,時綏覺得時間過得萬分煎熬,卻又希不要過得那麼快。
時綏覷著男人的側臉,比沉默是比不過他的,只能主開口,“傅,凌珊的事……”
時綏臉皮薄,已經纏了傅時聿這麼久,此刻再開口竟然底氣不足。
眼地等著他能接話。
男人睨了一眼,心底產生異樣的覺,他還真是第一次被一個人纏上,更詭異的是,他竟然沒有一反。
“我知道今天一天時間太短,不足以表達我的誠意,可是我真的沒有騙您,凌珊如果不準時注冊,學校那邊就會取消的學資格,那是申請了好久的學校。所以,我能不能請您先取消訴訟,我也保證不會食言,一定會做到讓您完完全全消氣為止。”
時綏一口氣說完,差點就要舉手發誓了。
”傅小姐那邊,我明天就去照顧,直到完全康復,這期間……”
“不用了。”
男人驟然出聲。
“什麼?”
“今天你救了我,就當兩清了。”
幸福來得太突然,時綏睜大了雙眼,一臉難以置信。
“怎麼?不愿意兩清?”
“不,不,我愿意。”時綏驚喜著擺手,立刻站起恭恭敬敬地朝他鞠了一躬,“我替凌珊謝謝您。”
傅時聿低低笑了下。
算了,難得當一次好人。
再說傅文舒剛給他打電話,不希把事鬧大,說是被三已經很丟人了,再鬧的滿城風雨臉往哪里擱。
凌家也不是無名小卒,鬧大了,這件事是一樁丑聞,也許還會影響以后嫁人。
至于凌珊,反正要出國了,最好離得遠遠的,眼不見為凈。
本也就是為了出口氣,既然凌家因為這事已經鬧得飛狗跳,那就到此為止。
“不覺得冤枉嗎?”
傅時聿靠著沙發背,長疊,移開上的電腦,神倦懶的掀起眼皮看,清冷的眼神中出幾分詢問的意思。
他是真的好奇。
事兜兜轉轉,好像損失最大的反而是眼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人。
怕聽不懂,他重復了一聲,“文舒和凌珊的損失都比不過時小姐。不冤嗎?還是說事一過,準備和凌周復合?”
猜你喜歡
-
完結688 章

戰爺的掌心寵又甜又嬌
前世,慕若晴眼瞎心盲,不顧父母的勸阻,拒嫁戰爺,非要嫁給唐千浩,結果落得個母女倆慘死的下場。重生歸來,她撕爛戰爺的衣衫,咬他一口,囂張地道:“你身上已經有我的烙印,我對你負責任!要麼你娶,我嫁,要麼,我娶,你嫁!”
121.1萬字8 401708 -
完結199 章

寶寶乖老公抱!病嬌大佬低聲誘哄
【超甜!甜就完了,團寵笨蛋小哭包×偏執病嬌自戀狂】司臨淵家族聯姻娶了一個公主,面對一個連飯都不會吃的女人,他能退貨嗎?凌洛洛一臉委屈,“洛洛會乖乖的”司臨淵一臉嫌棄,“能先把你的淚收一收嗎?”倒了八輩子大霉,碰到這麼一個祖宗。最后,司爺真香了……“寶寶,過來,老公抱抱。” ...
34萬字8.18 16980 -
完結212 章

乖,別咬
【甜寵 雙潔】薑未是個軟包子,對上傅晏又愛又怕。她扶著腰,怯生生問:“今天能休息嗎?”男人看向她。“去床上。”
35.6萬字8.18 9637 -
完結591 章

縛月
阮檸戀愛腦舔了厲城淵三年,最後卻落得遍體鱗傷,遠走他鄉的下場。五年後的重逢,她卻爲他的女孩做孕檢,看着報告單上的名字,阮檸陷入沉思。曾經他說自己是他的月光,如今沒想到月亮已經在他身邊。而她只是曾經那一抹被束縛的月色。也就是這一刻她總算明白,和厲城淵的三年成了笑話。直到,她毅然轉身,即將嫁爲人婦。他卻跪在她面前,捧出一顆真心,哭成了當年的那個少年。厲城淵說,“檸檸,別走,求你。”她卻說,“陷落的明月,如何追?”
86.2萬字8 6080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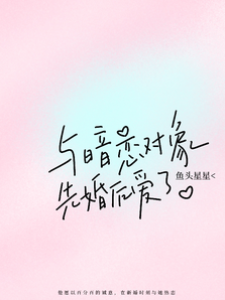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