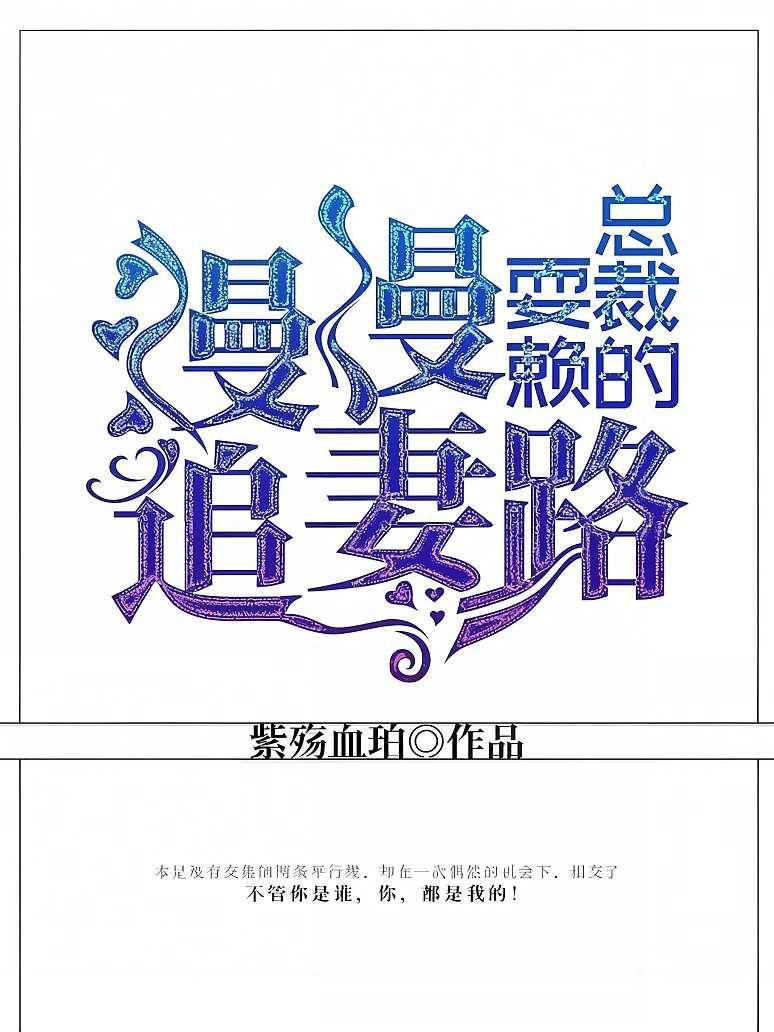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被渣后我嫁入頂級豪門》 第209章 逃避
時綏縱然想立刻和傅時聿攤牌,但是他現在喝醉了,并不是談話的好時機。所以即使在安靜的空間,也是正襟危坐保持著沉默。
傅九作為知人,如今夾在這種詭譎的氣氛中是如坐針氈。
他只好把自己當了形人,為了降低存在連呼吸都刻意緩下來。
傅時聿喝了很多酒,但他酒品好,喝的再多不僅面上毫也看不出來,連行為上都看不出什麼差異。
何況此時他閉著眼,時綏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睡著了。
一路無言回了南苑。
車子停下,時綏先下了車,想去另一邊扶傅時聿,然而男人卻避開了的手。
時綏的手尷尬的僵在半空中。
站在一旁的傅九立刻上前,“夫人,我來吧。”
時綏只好收手,退后幾步空出間隙,讓傅九扶著傅時聿從車里下來。
靜靜地跟在后,心里說不出的沉,連抬都覺得費力,這種明明頭一刀就可以解決的事,卻一直吊在半空落不了地。
難以言喻的滋味。
時綏這一天里不知道已經嘆了多氣,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把憋在口的濁氣都排出來。再次深呼吸,走進了這棟別墅。
傅九正好出來,見到時言又止。
他其實一直都覺得和傅時聿很相配,發展到這一步,他不想怪時綏,但到底心緒難平,也替傅時聿可惜。
他和傅時聿同姓,兩人在基地時認識,傅時聿又救過他的命,所以傅時聿離開基地的時候問他要不要一起走,他什麼也沒問就跟著他回到了北城。
Advertisement
這麼多年下來,從沒見過傅時聿喜歡過誰。
時綏是第一個且唯一一個進他心的人。
所以,當傅時聿看到視頻時的臉,傅九記得,那不僅僅是失,更是一種信任的破碎,對以往所有付出的否定。
時綏大概也能猜到他要說什麼,但這種事,外人無法置喙。
如果再來一次,還會這麼選擇。
既然發生了,后果認,但別無選擇。
朝傅九點點頭,轉去了廚房。
傅九神復雜地看了一眼,到底什麼都沒說,撓了撓短發,走了出去。
時綏煮了一杯醒酒茶,推開了主臥的門。
只見他靠著床頭,單手擱在額頭上,上的外套已經了,一雙筆直的被西裝包裹的長斜斜地掛在床邊。
時綏把被子放在床頭柜上,彎腰把他的抬上床,扯過被子想幫他蓋上,然而下一秒,的手腕猝不及防地被扣住。
轉過臉,恰好對上傅時聿睜開的一雙漆黑濃稠的眸,那里深不見底,像是杜絕了一切窺視,可依然讓看的人覺得他在生氣。
時綏張了張,想說些什麼,可什麼也說不出來,只能任由著他握著自己的手腕。
傅時聿著的手骨,心里恨得想要碎了。
這個人,怎麼可以這麼心狠。
他知不知道那個項目對他的意義?
雖說只是一個項目,卻是他下了軍令狀的,一旦出現差池,他會變得一無所有。
可竟然毫也不考慮他,就出來給了沈蓁。
雖然沈蓁說是在試探時綏,可也不過是被他抓到了現行才這麼說,若是功了,那現在等待他的就是大東們的審判。
Advertisement
即便是老爺子出馬,都不一定能保住他的位子。
這個人,心里真是毫也沒有他。
心一遍遍的冷,可即便如此,他竟然還是不想放手。
到了此刻,他都不知道該恨還是恨自己。
明明是幾秒鐘的時間,卻又像是世紀般漫長,傅時聿又閉上了眼,同時也松開了手。
時綏頓了一下,繼續手上的作,給他蓋好了被子,又拿起杯子了一下溫度,低聲勸道,“先醒醒把醒酒茶喝了吧。”
話說完,又等了一會兒也不見傅時聿睜眼。
時綏只好又說了一遍。
可男人就像是睡著了一樣抿著就是不睜眼。
時綏知道他還醒著,只是不愿意搭理自己,于是又只好勸道,“你喝了很多酒,就這麼睡等會兒起來頭會疼。”
“我是死是活還和你有關嗎?”
傅時聿猛然睜開眼,冷冷地看著。
時綏一噎。
并非是個有耐心的脾氣,只是因為覺得對他有愧疚,所以才耐著子勸他。
兩人就這麼對視著。
最后還是時綏先移開視線,淡淡地道,“你先把它喝了吧,有什麼話等你酒醒了我們再談。”
說著又把杯子向前遞了一分。
兩人僵持著片刻,傅時聿拿過杯子,一飲而盡。
他把空杯重重地擱在床頭柜上,然而閉著眼睛不看了。
時綏也沒再說什麼,拿起空杯子就要離開。
走到門口時,后聲音傳來,“我希我睡著的時候你不要又做出什麼事。”
心頭一梗。
時綏扯笑了笑,“不會。我等你醒。”
Advertisement
既然決定攤牌,這點時間還能等,只是時經年那邊只怕是來不及了。
已經盡力了。
走出房間,給周祁打了個電話,簡單地講了下況。
周祁沉默了一會兒,道,“我會爭取,如果實在不行,我們再上訴。”
“我知道。只是怕是要影響我弟弟了。”
周祁安,“他已經二十了,既然進了娛樂圈,這點抗風險能力還是要有的。我會盡力的,還有一下午外加一晚上的時間,說不定會出現轉機。”
時綏再單純,也知道這是安人的話了。
除非劉錦昌妻那邊有什麼進展,只是也知道這不可能。
和沈蓁易失敗,不可能會說出們的行蹤。
時綏掛了電話,心頭滋味難明。
心底的抑無法排出,便只能轉移焦點,時綏去了一趟超市,買了一堆菜回來。
一下午的時間,都在廚房度過。今天老太太壽辰,林姨也難得放了一天假回了兒婿家。整個南苑就只有和傅時聿,這樣即使發生什麼事,也不至于太難看。
并非怕傅時聿打,憑對他的了解,他不至于如此,只是吵架怕是難免。
整整四個小時,做了一整桌的菜。
等到六點半到時候,傅時聿才從樓上下來。
聽到聲音,時綏立刻從沙發中站起,一言不發地看著他。
看到一桌子菜的時候,傅時聿的表說不出來的玩味。
時綏被他這個眼神看得有點不解,正想開口說什麼,只聽傅時聿先出聲,“怎麼,最后的晚餐?”
時綏愣了下,很快否認,“不是……”
“就算是,我也沒胃口吃。”
傅時聿徑直往外面走。
時綏立刻追上來,“你去哪?”
傅時聿低頭看了一眼,眼神里除了冰冷還是冰冷。
時綏著頭皮,討好道,“你吃點東西再出去吧。”
頭頂傳來一聲呵笑,似乎被這話逗笑了,笑聲很快止住,換來的是他淡漠的強調,“做得再好吃,你以為我還能吃得下?你留著自己慢慢品嘗吧。”
沒去看時綏漸漸失了的臉,傅時聿長一邁,很快消失在花園里。
看著他冷漠的背影,時綏慢慢地蹲下來。
猜你喜歡
-
完結698 章

那一夜,她帶走了江城首富的孩子
【萌寶+總裁+甜寵+雙潔】頂著私生子頭銜長大的南宮丞是一個冷漠陰鬱的男人,不婚主義,厭惡女人。 一次偶然的機會,沈茉染上了他的床,醒來后卻被他扔在一邊。 四年後。 沈茉染蛻變歸來,南宮丞把她堵在牆角,「原來那一夜,是你」 「你不是說了嘛,數字隨意填,忘了這一夜」 南宮丞不上當,「孩子呢,是不是我的?」 「孩子跟你無關」 恰此時,一個男孩兒跳出來,「放開我媽媽,」 旁邊還有熟悉的沈柒柒。
122.1萬字8 221877 -
完結55 章

蝕骨寵溺
《蝕骨寵溺》六年前,楚聽顏遇到了那個不可一世的狂妄少年—江肆沉。在她被欺負時,他會挺身而出,也會因為她隨口的一句話,跑遍整個湘城買她最喜歡吃的鳳梨酥,甚至為了能和她上一個大學,發奮學習。多年後,楚聽顏混跡成了一個娛樂圈十八線小明星,而她的前男友卻成了她新戲的投資方。空無一人的廊道里,高大的男人壓著她,指尖捏著她的下巴,嗓音暴戾沙啞,“當年為什麼要跟我分手?”楚聽顏緊咬紅唇:“沒有為什麼,江肆沉,當年是我對不起你,過去六年了,把那些事都忘了吧!"他嗤笑一聲,“楚聽顏,你未免太自信了,以爲我對你舊情難忘?”楚聽顏:“沒有最好!”酒局上,他故意給她施壓。“我覺得楚小姐不適合《盛夏餘年》的女3一角,王導,您說呢?”王導汗顏,不敢有任何意義,“江少說得對,楚小姐是不太適合。”楚聽顏:明顯是故意針對她。後來,爲了爭取角色,她被迫去討好江肆沉,甚至還失了身。他需要一個乖巧聽話的假女友應付家裏的催婚,偏偏找到了走投無路的她,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她同意了他提出的條件。
16萬字8 9241 -
完結286 章

寵妻攻略:墨太太又在撒嬌!
替姐姐嫁給一個變態狂,結果自盡了。重生回來,沒嫁給變態,但要嫁給殘廢?老天,這人設沒咋變啊,你玩我呢!!!嫁而死,虞清霜好不容易重生一回,人設沒咋變啊!未婚夫陰測測地盯著她:“我得了癌癥,活不過三個月。”虞清霜默:這婚可以結。等男人一翹辮子,她就升級為單身貴族,還有大把遺產可以繼承,劃算!N個日夜后,虞清霜怒了,“墨臨淵,你怎麼還沒死?”“小東西,要乖,我死了,誰護著你作天作地?” 【甜寵,必戳哦!】
53.5萬字8 22640 -
完結99 章

錯撩:厲太太日常虐夫
阮薇曾深愛厲斯奕,為了他,她甚至可以付出生命,可他只愛她的妹妹。
8.9萬字8 115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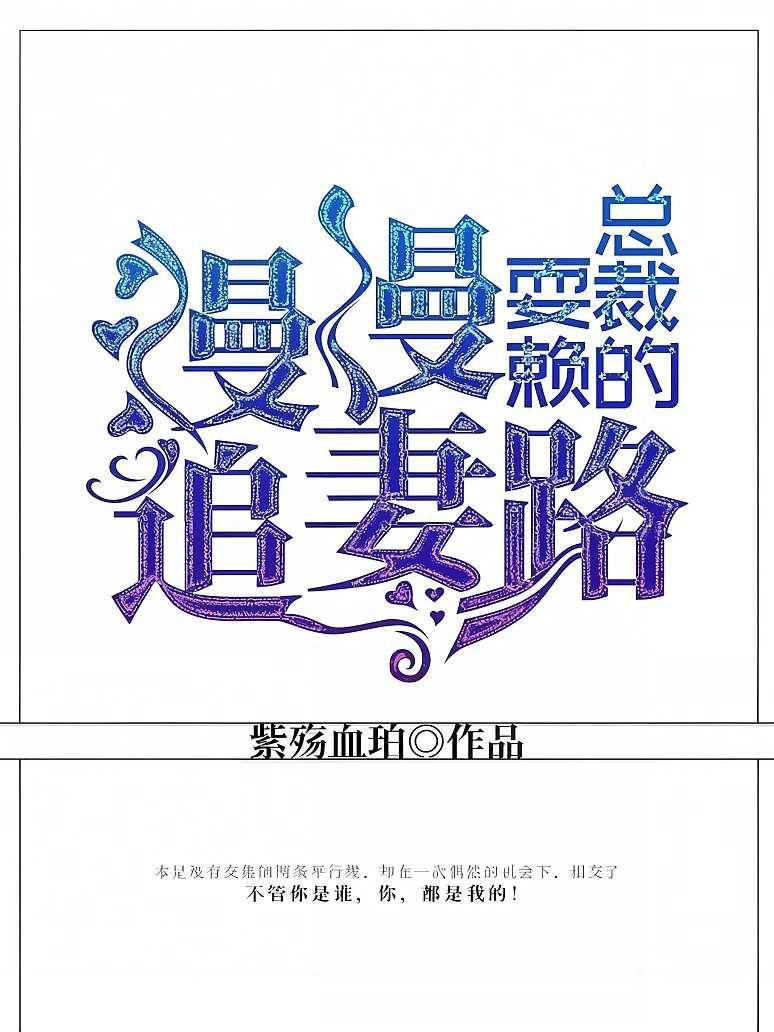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
完結318 章

插翅難逃:沈總的金絲雀只想跑路
新作品出爐,大家可以前往番茄小說閱讀我的作品哦,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你們的關注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會努力講好每個故事!
41.3萬字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