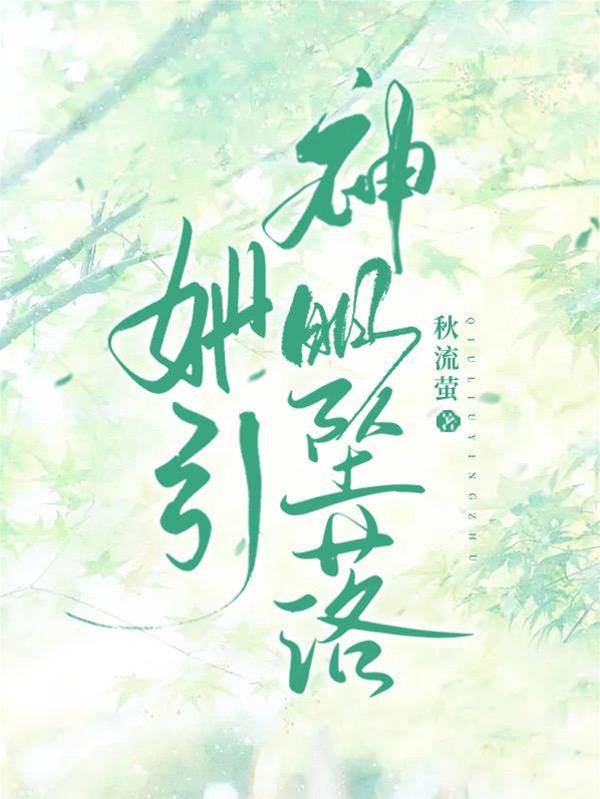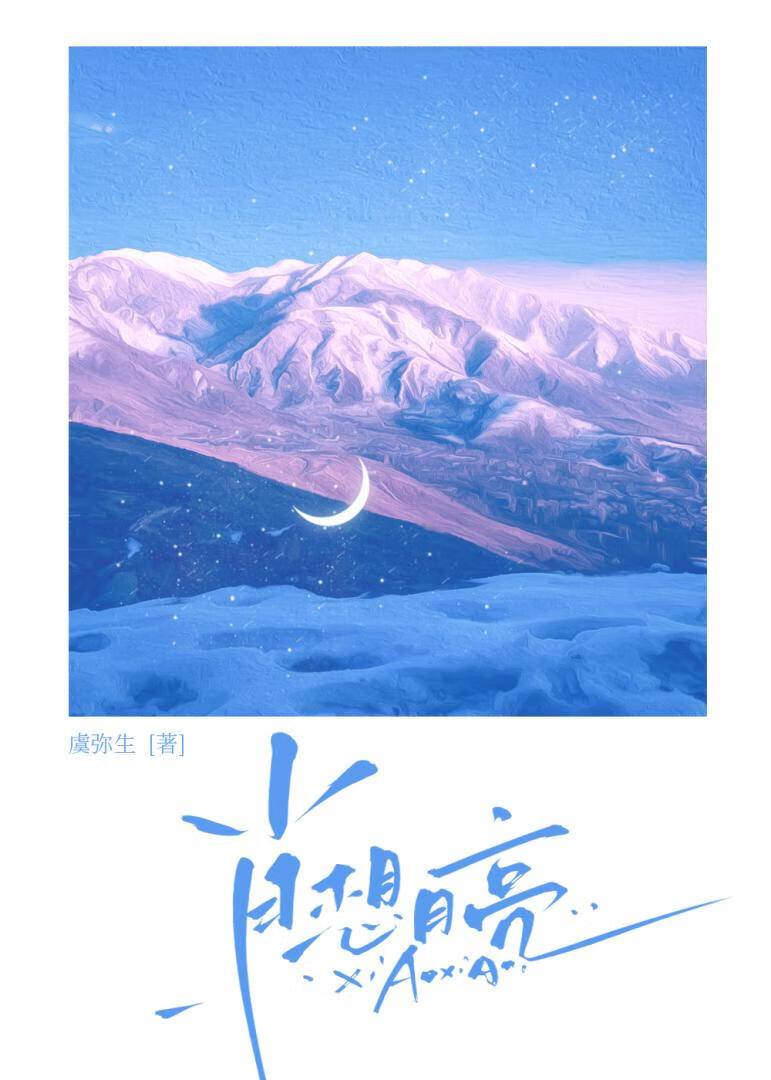《私有醉意》 第1卷 第100章 什麼工作需要這麼拼命
一想到可能會被前排的司機聽見,時晚的耳尖就不自覺地染上緋紅,像是鵪鶉一般將腦袋在傅祈安的頸窩。
傅祈安自然知道懷里的小朋友害了,他的嚨間溢出輕笑。
而后出溫熱寬大的手掌將時晚的腦袋按進自己懷里,車后座那曖昧的氣氛也悄然地散去,余留下的只是溫。
出雙臂懷抱著男人的脖頸,趴在他耳邊說話,“你覺得我們的孩子生出來是男孩還是孩?”
傅祈安抓著的手,輕輕地著的手心,腔調懶洋洋地,聲線微啞,眼角眉梢帶著清晰可見的笑意,“只要是我們兩個的孩子我都喜歡。”
“傅祈安你不要端水,我才不信你的都喜歡。”孕期的時晚并不是很好哄,撐起子,出手指了他的膛,一臉傲的小模樣。
男人笑著又手將人攬懷里,“如果是男孩,我和他一起保護你,如果是孩,我會保護你們兩個。”
“如果要你選一個呢?”時晚眨著狡黠的杏眸專門使壞。
“男孩。”傅祈安沒有毫猶豫。
“你不會……”用狐疑的目盯著他,但傅祈安下一秒就打消了的想法。
“并不是重男輕或許是其他的什麼原因,只不過是因為我想多一個人保護你,男孩保護孩天經地義。”
時晚的小版他已經見過了,還是自己親手養大的,所以他對于生兒并沒有什麼太大的執念。
只是希時晚有多一個人保護。
“如果是男寶寶,他肯定是小小男子漢。”傅祈安對于自己和時晚的基因很自信。
傅祈安的這個說法時晚有些詫異,但是后知后覺時心里像是流淌過暖流。
接下來的日子,時晚就安安心心地在溪灣做個小米蟲,
Advertisement
而傅祈安則正常去上班,但是他的上班時間延后,下班時間也提前了。
但是令時晚到疑的是,這段時間傅祈安總是把自己關在書房里,特別是深夜,基本半夜醒來的時候枕邊人已經不見了影,而且床鋪還是涼的,說明他離開了很久。
時晚并不懷疑什麼,只是覺得很奇怪,不管再忙,傅祈安的工作從來都不會帶回家,最多是看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天時晚睡得不沉,被傅祈安哄睡后一直蹙著眉,睡夢里夢到他們的孩子患了先天心臟病。
當夢到孩子每天都會被心臟病的癥狀折磨時,時晚從睡夢中驚醒。
猛地睜開眼睛,眉頭鎖,呼吸急促。
時晚后知后覺地抹了抹眼尾,發現了一陣潤,哭了。
想起夢中自己懷里痛苦嗚咽的孩子,只覺得心臟一陣陣悶痛。
下意識地轉頭想找傅祈安撒,但是邊又是空的,手一,仍然是一片冰涼。
這段時間開始孕吐了,腰間也是時不時傳來陣陣酸痛,再加上剛剛過于真實的噩夢,時晚到一種被棄的委屈,眼眶不潤起來。
時晚坐在床邊發了會兒呆,打算去找傅祈安。
有什麼工作需要這麼拼命?現在都已經凌晨一點了,還要不要了,時晚只覺得怒火中燒。
并沒有放輕腳步,踢踏著拖鞋的聲音在寂靜的深夜里顯得格外明顯。
時晚往書房的方向走,果不其然,書房的門虛掩著,出一亮,確認傅祈安真的在工作,時晚心里的那火越燒越旺。
推開書房的門,傅祈安戴著一副金眼鏡,臉上冷淡如波,鼻梁英,微垂著頭在翻閱紙張。
在只有獨自一人時,他眸中不帶毫緒,周流著凌冽的氣場。
Advertisement
時晚毫不怵,抱臂站在門口,也不出聲,等待傅祈安自己發現。
傅祈安在時晚推開門時就察覺到了,抬頭一看,見是時晚,周冷淡的氣質逐漸消散,薄勾起笑意,“怎麼到這里來了?”
將手里的東西不留痕跡地夾到旁邊的一沓文件里后,他起朝走去。
聽到他的問話,時晚冷哼了一聲,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凝著他。
剛剛時晚的臉匿在黑暗里,傅祈安看不真切,此時走近一看,發現眼眶紅紅的,泛著意。
傅祈安屈指輕的眼尾,他的目地鎖定在的臉上,“為什麼哭了?嗯?”他耐心地等待著的回答。
時晚一開口,努力按捺著的緒和哭腔卻控制不住地溢出,“你為什麼這麼晚還不睡覺?”說著說著緒逐漸失控,沒等男人回答,又再一次開口。
“以后你不用分出那麼多心神來照顧我,我不喜歡你半夜還在工作。”邊說著,眼角的那滴晶瑩的淚珠順著眼角落,偏過頭不想看他。
傅祈安知道生氣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只要哭了,都是天大的事。
他俯彎腰,視線與的齊平,他使了些力道,讓把腦袋偏過來看著自己。
見眼中含著淚,但仍然倔強著自己,他的心不一,那種心疼的覺如同水般涌上心頭。
不管怎麼樣,先道歉總是沒錯的,“對不起,我錯了。”
“你沒錯,是我錯了。”時晚忍不住和他唱反調。
知道和他犟,就說明沒有多生氣,傅祈安原本張的心此時緩解了些。
知道在鬧小別扭,至于原因,傅祈安大概能猜到一些,手著的后頸,嗓音帶著些輕哄的溫,“我以后再也不在家里工作了,陪著你好不好?”
Advertisement
他邊說著心里邊盤算著接下來的工作怎麼達到效率最大化,在上班的時間就完,且不帶回家。
時晚總覺得孕期的自己都變得不像自己了,每天和傅祈安犟,仿佛總是要找點事和傅祈安吵才痛快。
雖然大多數傅祈安總是笑著哄,可就是覺得不公平,傅祈安工作這麼累了,回來還要忍的這些小脾氣,想到這里,時晚泄了氣,覺得今天自己又是莫名其妙。
傅祈安半夜還在加班,自己還在這里鬧脾氣打擾他。
時晚此時思緒混,傅祈安越哄,越覺得自己在無理取鬧。
而傅祈安此時并不知道心里的那些小九九,只是想著,不管怎麼樣,先緩住的緒總是沒錯的,孕期的緒起伏不能太大。
見不說話,傅祈安也不惱,直起將人橫抱起來,而后邁步往臥室走。
時晚在他懷里只是抓著他的領口,將臉埋在他的膛,緒很低落。
傅祈安已經發現了一個哄時晚的最佳姿勢,就是他靠在床頭,而后時晚坐在他上,像是無尾熊一般依偎在自己懷里。
這一次來到臥室,傅祈安就自覺調整了這個姿勢,把孩的雙拉過來,手按著的腦袋朝向自己懷里。
“你能和我說說為什麼哭嗎?”男人低沉的語氣帶著哄,帶著強烈的安全。
他從來不讓兩人的矛盾過夜,他們能相已經很不容易了,不應該讓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冷戰占據他們相的時間。
這一次時晚也不再擰了,如實地說出口,“第一次哭是因為做噩夢,第二次是因為看到你還在加班有些生氣,氣你為了我付出這麼多,還要出自己的睡覺時間來工作。”
聽到的回答,傅祈安微微怔愣了下,本以為是時晚怨自己沒陪著,沒想到是心疼自己深夜加班。
看著因為委屈控訴而癟著的角,傅祈安薄微揚,含著似有若無的笑意,眼眸中的意滿得快要溢出來。
“我向你保證,我以后再也不會熬夜加班了,晚晚什麼時候睡我就什麼時候睡。”男人使壞顛了顛,讓更加摟自己的脖頸。
這段時間主要是因為在設計求婚的事宜,剛剛是在確認最終的方案,快收尾了沒想到時晚突然醒來。
他的晚晚值得最盛大的求婚,不僅僅是因為未婚先孕的原因而草率地給大家一個代。
“而且我也沒覺得自己付出了什麼,這不都是我應該做的嗎?”男人語氣認真,毫沒有摻雜半點虛假。
人懷孕已經很辛苦了,如果自己作為的伴,作為未出世的孩子父親,只是當個甩手掌柜的話,那才是真的遭人唾棄,不說別人,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不能替時晚分擔懷孕的辛苦,那他只能從其他的方面來盡力彌補,給足緒價值,照顧好生活的方方面面。
傅祈安是真的心疼時晚,特別是在看到每次吃飯還沒吃幾口就要沖去洗手間痛苦地吐個干凈,整日整夜地睡不好,孕期反應開始加劇,腰酸背痛。
雖然月份不大,但是小家伙卻沒折磨人。
再加上緒化很明顯,但是他倒是覺得很可,平日里哪能看見耍小子的小朋友。
鬧脾氣時像抓不住的泥鰍,嘟著死都不愿意看自己一眼,最后再不痛不地捶自己幾拳,他沒跟說的是的力道對自己來說就像是撓。
“你的痛苦我也想幫你分擔。”如果技允許的話,傅祈安甚至想把孩子轉移到他上,這樣時晚就不用承十月懷胎的痛苦了。
時晚抬頭看著他似水的目,直勾勾地凝視著,眼底濃厚的意沒有半點虛掩,像是波濤洶涌的海水般快要將淹沒。
“傅祈安,你會不會覺得我很煩……”不安地揪擰著手指,因為這兩個月以來,就連時晚都數不清自己耍了幾次小脾氣,十手指頭都數不過來。
男人低下頭將薄輕輕印在的眉間,溫地打破那些不安的疑慮,“寶寶,你不能這樣想,我永遠都不會覺得你煩。”
他微微頓了下,換做更認真的語氣,但又不會顯得嚴肅,“或許你會覺得永遠或者是一輩子太長,太難驗證人心了,認為我在說大話,那我們把一切給時間好不好?”
讓時間驗證他的意,日久見人心,明白他的非不可。
傅祈安打算把自己的資產全都轉移到時晚上,他確認自己不會變心,但還是想現在給一個保障。
男人總是善變的,他也說不準自己以后到底是如何,但是在最有限的年歲里,傅祈安盡自己所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給。
希在垂暮之年,回想起自己的一生,讓時晚堅定地回答自己沒有看錯人。
時晚驀然抬頭,不經意間就撞進他眼眸中的深邃漩渦中,灼熱確切的意蔓延全,讓的靈魂為之震。
傅祈安總會在每一個沒有安全的瞬間親自撥開那些焦慮張的迷霧,來到面前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永遠你,你不用懷疑,我會自己證明。”
意隨風起,在年時每一個不確定心的瞬間,年的喜歡蔓延起無止境的歡喜,直到陣陣劇烈跳的心臟確切地告訴他,是了,不要猶豫了,你認定了。
兩人額頭相,時晚閉上眼睛緩了緩心神。
意過于濃烈,讓人眩暈,明明沒有窒息和相互勾纏的吻,只是短短幾句話就足夠敗北。
兩人靜靜地相擁著,而后,傅祈安低下頭說了句話。
“你剛剛說做了一個噩夢,跟我說一說好不好?”傅祈安沒有錯過說的每一句話。
他總覺得時晚緒的突然失控應該跟這個噩夢不開干系。
被他一問,時晚就打開了話匣子,那些小脾氣又一次被傅祈安哄好。
“剛剛我夢見寶寶生下來就患有先天心臟病,從小到大都是一個藥罐子,夢里的他瘦得像小猴,剛生下來時皺皺的,但是我們找遍了全世界的醫生,都沒辦法完全地治愈他。”
傅祈安靜靜地聽著絮叨,太慌了,說起夢里的事,并不是太有條理,但是傅祈安總是能聽懂,也沒有打斷,讓把那些消極緒和擔憂都發泄出來。
“他從生下來時上就著管子,比其他的小朋友晚了一年才學會走和爬。”
猜你喜歡
-
完結476 章

穿書后大佬撕了惡毒女配劇本
擁有天煞孤星命格的玄門傳人唐荔穿書了。 穿進一本放著霸總夫人不當,天天想著害死霸總,和小白臉雙宿雙棲,最后被霸總收拾得連渣渣都不剩的惡毒女配一書中。 唐荔:“……” 這女人腦子被門夾了!放著有錢有顏有身材的老公不要,非要去喜歡個小白臉? 后來,眾人驚恐的發現,唐荔不作妖了,不養小白臉了,整天神神叨叨給人算命看病,收的小弟一個比一個厲害就算了,還總是追在霸總后面老公長老公短。 “老公,你腸胃不好,這是我特意給你煲的暖胃湯。” “老公,我怕打雷,抱抱~” …… 忍無可忍的霸總解著皮帶,語氣危險:“唐荔,你這么處心積慮讓我愛上你,我現在就讓你知道,我有多愛你!” 只想有個老公的唐荔:“……” 老公,你聽我解釋……
88.1萬字8.18 61867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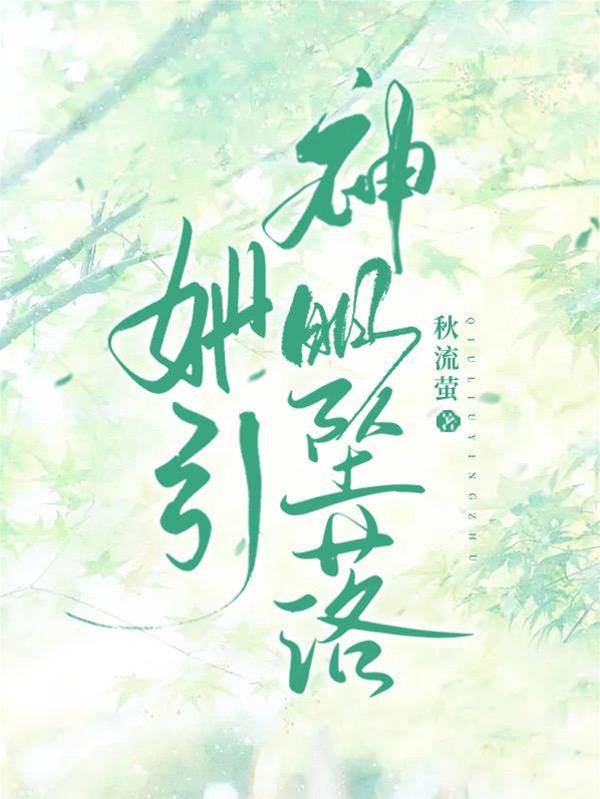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777 章

罪愛沉淪,陸少跪地輕哄
和陸祁深結婚以前,沐南煙聽說他心狠手辣,不近人情,還有個愛而不得的白月光。她以為傳聞終歸只是傳聞,婚後才知道,真相跟傳聞相比,差不了多少。 沐南煙本來只想安安分分的做好陸太太,卻逐漸沉淪在了對陸祁深的愛意裡。她以為,陸祁深對她也有不一樣的情愫,為此暗暗竊喜。卻不想,他始終愛的人不是她。 直到陸祁深的白月光回國,沐南煙幡然醒悟,遞上了離婚協議書,決定瀟灑離開,成全這一對有情人。 …… 整個北城都在等著陸祁深離婚,因為人人都知道他不愛他的妻子,心心念念的都是青梅竹馬的白月光。 終於,眾人不失所望的等來了陸祁深要離婚的消息。 就在所有人以為陸祁深終於受不了沐南煙,要和白月光在一起的時候,一向不喜出現在媒體鏡頭下的他卻抱著個孩子,笑得燦爛。 “聽說外界傳了不少我跟我太太要離婚的謠言,我特來澄清一下,我們感情很好,孩子再過幾年都能打醬油了。”
90.4萬字8 15821 -
完結167 章

總統先生,請和平離婚
她身為總統夫人卻要騙吃騙喝騙錢花?!父親販毒鋃鐺入獄,她被迫嫁到異國他鄉為恐怖組織收集情報。他是一手遮天呼風喚雨的一國領導,她是這場政治婚姻的傀儡。他是人人敬愛的總統背后卻霸道變態,她善良單純卻成了道德淪喪的棄婦!“離婚對你而言將是地獄行走的開始!”“我不是你的玩物,快放開我!”
43.3萬字8 57 -
完結2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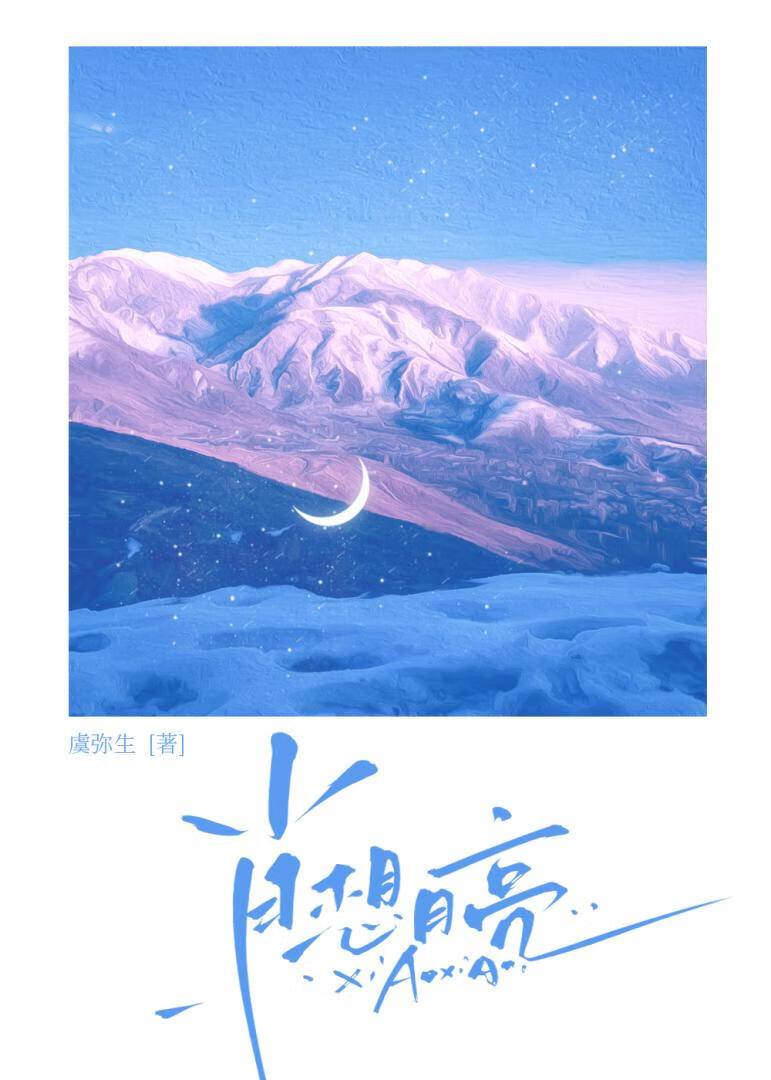
肖想月亮
林應緹第一次見江席月是在養父母的倉庫裏。 少年清俊矜貴,穿着白襯衫,雙手被反捆在身後,額前黑髮微微濡溼。 他看向自己。嗓音清冷,“你是這家的小孩?” 林應緹點頭,“我不能放你走。” 聞言,少年只是笑。 當時年紀尚小的她還看不懂江席月看向自己的的淡漠眼神叫做憐憫。 但是那時的林應緹,沒來由的,討厭那樣的眼神。 —— 被親生父母找回的第九年,林應緹跟隨父母從縣城搬到了大城市,轉學到了國際高中。 也是在這裏,她見到了江席月。 男生臉上含笑,溫柔清俊,穿着白襯衫,代表學生會在主席臺下發言。 林應緹在下面望着他,發現他和小時候一樣,是遙望不可及的存在。 所以林應緹按部就班的上課學習努力考大學。她看着他被學校裏最漂亮的女生追求,看着他被國外名牌大學提前錄取,看着他他無數次和自己擦肩而過。 自始至終林應緹都很清醒,甘願當個沉默的旁觀者。 如果這份喜歡會讓她變得狼狽,那她寧願一輩子埋藏於心。 —— 很多年後的高中同學婚禮上,林應緹和好友坐在臺下,看着江席月作爲伴郎,和當初的校花伴娘站在一起。 好友感慨:“他們還挺般配。” 林應緹看了一會,也贊同點頭:“確實般配。” 婚宴結束,林應緹和江席月在婚禮後臺相遇。 林應緹冷靜輕聲道:“你不要在臺上一直看着我,會被發現的。” 江席月身上帶着淡淡酒氣,眼神卻是清明無比,只見他懶洋洋地將下巴搭在林應緹肩上。 “抱歉老婆,下次注意。”
33萬字8 62 -
完結109 章

卻雀[京圈]
第三次遇見,江津嶼終於問了她的名字。 “蘇卻。”她答。 “麻雀的雀?” 蘇卻正欲糾正,便聽見他涼薄的聲音,帶着些許嘲弄,“人如其名,嘰嘰喳喳,吵死人了。” - 蘇卻留美十年,因姐姐的婚禮歸國。 姐姐放棄十年戀情,轉而閃婚豪門。 婚禮當天,聽說前男友要來鬧事。 蘇卻以爲是個糾纏不休的鳳凰男,擼起袖子就要截人。 “真以爲能攔得住我?”江津嶼撣了菸灰,被她視死如歸的模樣逗笑。 蘇卻恍然覺得,他還是笑起來比較好看。 她改了想法,踮起腳尖,摘下了他脣上的煙。 “我比她好,要不要和我試試?” - 蘇卻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真心得不到反饋,她放手得也快。 某日新男友帶她出席盛宴,不想卻是江津嶼的生日。 衆人都等着看蘇卻的好戲——甩了燕北城裏誰都不敢惹的太子爺,竟還敢帶着新歡來砸場子。 不過,江津嶼談笑自若,眼神都沒往她這裏來一個。 蘇卻也笑靨如花,順道將男友的手挽得更緊些。 當晚,男友的黑色幻影遭遇惡意追尾,被逼停路邊。 撞到凹陷的車門被猛地拉開,蘇卻還在怔忪間,一隻手將她拉了出來。 “膽子這麼小,也敢和我玩?” 熟悉的涼薄聲線,蘇卻不服輸地回瞪。 本以爲會是一場急風驟雨,她的嘴角突然被親了親。 江津嶼難得示弱,低聲道,“彆氣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小劇場】 聽說姐姐要和前男友在王府半島的茶室見面,蘇卻想都沒想便衝到現場阻止。 卻看見一個陌生男人。 玉石假山後,江津嶼掀簾而來。 那陌生男人垂首:“小叔。” 江津嶼看都未看,徑直將她攬入懷中:“嬸嬸在這,不打招呼?”
26.3萬字8 1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