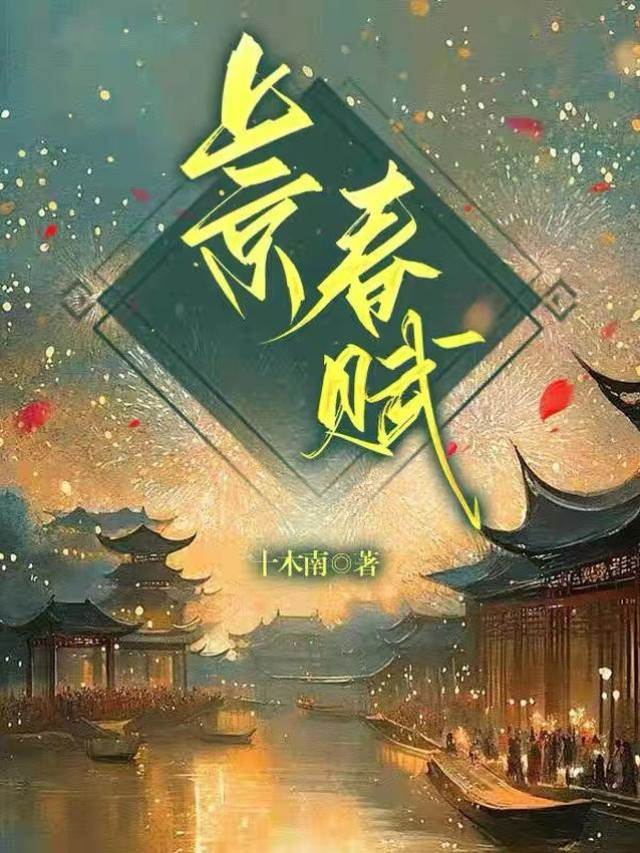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籠中青雀(重生)》 第67章 新畫 她就只需當作,楚王是在和她,約……
第67章 新畫 就只需當作,楚王是在和,約……
用來存放畫像的這間室兩面開窗, 線極好。一面窗正向西開,于是夕的照就過羽紗的窗紙,毫無保留傾灑在姜頌寧綻放的笑旁。畫工似乎在畫像上傾注過畢生的, 那雙眼睛便也在金下閃耀出生前一樣的彩, 照得仿佛下一瞬就會從畫框裏走下來,對面前凝著的人說:
“為什麽又哭了?”
但正如死去的人不可再追,太注定要西沉。
金暗下去,毫不留、更不容挽留地退出去。
先黯淡的,是畫中人的雙眼。
接著是無暇的、如生的容。
最後, 連的手腕和指節都失去溫度的時候, 站在青灰的暮影裏,楚王依舊沒有稍形,仍然僵著,著、看著他灰暗下去的, 失去的, 不會再發出任何聲音的人。
室門外, 卻響起了被寒風蓋過的輕聲議論。
“怎麽辦, 不殿下?”
一年前——江孺人還沒王府、殿下也沒回朝的時候——殿下若在這間屋子裏,除非宮中來人, 否則誰來也不出去。
如今,雖有正經大事,殿下便不會耽延,可——
“從前大姐兒、大郎、二郎滿月,殿下都不在京啊。”
既滿月宴當日不在京, 之後才回,當然也沒留下“滿月宴當天晚上,是不是要去看孩子母親”的規矩。
那, 到底要不要提醒殿下,鹿鳴堂的宴早已散了?
“哎!起開起開。”張岫籠著手走過來,用胳膊肘推開聚在一的人,俯在門邊,低聲地喚,“殿下,殿下?”
不待房中有所回應,他便笑道:“今日的晚膳,殿下還用嗎?”
片刻,門中傳出楚王一如平常的聲音:“酉初了?”
Advertisement
“是,還不到酉初一刻。”張岫笑答。
王府裏晚膳的時辰,夏秋在酉正,冬春在酉初三刻。
“告訴雲起堂,先用飯,不必——”楚王頓了頓,“不用了。”
“我這就去。”幾個呼吸後,他說。
侍們忙讓開門邊。張岫人快去拿殿下的裳,再去備水。
又過了約有半刻,楚王開門。
侍已將東西備齊候在一旁,見他出來站定,便低著頭服侍他洗去酒氣。
還有小侍用欽敬的目看著張岫,不知張公公是怎麽猜準的殿下的心。張岫瞪他,他低頭,心裏也不是沒有得意:
府裏是沒有過“哥兒姐兒滿月宴後,殿下是否要去看孩子和母親”的舊例,可規矩都是殿下定的。這原也不算什麽規矩。殿下想去,自然會去,殿下不想去,除非陛下有旨或娘娘勸導,不然,誰還能拿“規矩”著殿下去?這是楚王府,又不是那些夫人娘子的府宅,殿下是贅了來的。
而他們殿下的心呢,當是不願為了自己牽連旁人的——這不是姜側妃和江孺人誰更要的問題,而是江孺人這一年如此盛寵,殿下若連孩子滿月宴當天都不去看,誰知如靜雅堂又會怎麽想?從殿下的行事看,又顯然是在不風地護著雲起堂。
退一萬步,就算他竟猜錯了殿下的心,他也沒提過一個“江”字,只問了殿下還用不用晚膳。
他是隨服侍殿下的人,照顧殿下,本就是分的事。
隨殿下回到雲起堂,親手替殿下打起正房門簾,看殿下進去,又聽見江孺人高興的一聲,“殿下!”張岫笑呵呵又籠起了手,被芳蕊請著,也先到下房去取暖用飯了。
已過酉初三刻,堂屋裏卻還沒有擺飯。
掃一眼空的圓桌,楚王便問:“怎麽還沒吃飯?”又道:“不是說過許多次了,不必等我。”
Advertisement
“若在平日,我就不等了。”給他遞上手的棉巾,青雀笑道,“今日覺得殿下一定會來,就想著等一等——我方才還問嬤嬤,是不是殿下吃醉了。況且今天在鹿鳴堂高興,申時才散,我還不呢。”
“不?”楚王擡手,在上腹。
“是真不!”被他得有些,青雀想躲,便兩手抓住他的手腕,問,“現在擺飯嗎?殿下不?”
“擺飯吧。”
楚王握住的手,松開,同一起走向兒臥房:“‘先而食,食勿令飽’。不也吃些,以免傷胃。”①
“嗯。”青雀應著,看了看自己被松開的手。
又擡頭,看楚王似乎平靜無事的容。
他心……不算好。或許是很不好。
為什麽?
察覺到的視線,楚王回看,青雀只一笑,便說:“想著殿下或許會吃醉,我還廚上燉了姜魚湯和八珍醒酒湯、橘皮醒酒湯,不知殿下更哪樣。殿下又沒醉,只當嘗嘗看他們的手藝吧。”
“是沒醉。”楚王步伐慢下來,停在了兒臥房前,對青雀稍稍俯,“還有沒有酒氣?”
想著他收回去的手,猶豫著,青雀小小上前半步,輕輕聞了聞:“沒有……沒有了。”
退回去時,青雀眼前有一息恍惚。
這樣的對話,這樣的場景……好像封孺人那天,他送走定國公等人,回來看時一樣。
那時,他是怕和兒聞到酒氣不舒服。
現在,他還是怕兒不舒服。
那天,他還說,讓別怕,別多想;告訴,即便生産後不能隨心清潔,也……很。
那時,幾乎以為,楚王看到的只是——是自己,他的溫,也只是對。
當然,很快就回了神,知道那應不是對,只是對——像姜側妃的臉。
Advertisement
那麽現在,也的確不必去想太多。
只是松開手而已。
決定要沉驗的那一刻,就已經想好了一切可能,不是嗎?
青雀笑著,率先走了房門,又回頭對楚王笑:“殿下?”
著含笑的眉眼,楚王間微,片刻應:“……來了。”
察覺到楚王的煩惱或許非所能關懷,青雀便也竭力表現得如同平常一樣。這并不難。從前的所有時刻,幾乎都是這樣做的。忽略他的痛楚、頹喪、憔悴,還有面對時的晃神,只專注在自己上,想著自己的此刻和將來,想著兒的此刻和將來。
他應也不願讓知曉他的煩惱,所以,只在松開手時,些微洩了異樣。
但他又好像察覺了那一瞬的失落。
兒睡著,他也沒有出聲。待看過兒出來,他便一一問起了今日在鹿鳴館的筵席:吃了幾杯酒,行了什麽令,都去了哪裏賞景,哪一的景致最喜歡,有沒有什麽事讓為難。
吃飯時,他不再說話,卻親手給添了一次湯,又挪過一次碗。
青雀當然不可避免地高興起來,心裏脹脹的,有些發酸,又有一點覺得好笑。
堂堂楚王,自己還不知正為什麽心事不快,卻像給自己下任務一般,按部就班哄姬妾高興。
“我——”侍們撤去飯菜,青雀側向楚王靠近,“我琵琶練好了,彈給殿下聽?”
從花園回來後,楚王來之前,真的練了半個多時辰,手已不算太生。
的神在楚王眼中,從來毫無遮飾,明朗易懂。
譬如此刻,映著燭的雙眼裏,就寫滿了,“我也想讓殿下快樂”。
但他能不能就這樣得到快樂?
——為消除看頌寧帶來的痛楚,從青雀上得到快樂。
輕輕地,楚王笑出一聲。
看向東廂的方向,他避開了青雀的視線。
“明日吧。”他說,“明日,還想看你的弓箭。”
說完,他站起:“今日晚了,還有幾個條陳要看。”快速看了青雀一眼,他又道:“我就在東廂。你先睡,不必等我。”
青雀站起,目送他走出房門。
門板合攏,門簾也重歸垂順。一手扶住圓桌,青雀也輕聲笑了笑。
不知道姜側妃是否會彈琵琶,也并不知姜側妃是否還會箭。
那麽,就只需當作,楚王是在和,約定明天。
-
青雀在平常的時間睡,也和平常一樣,不知楚王何時回的臥房,也不知他是在淩晨的哪一刻離開。
但這一夜他回來,的確沒再察覺到他心不愉。
在安靜落雪的冬夜,按照約定,彈了《春江花月夜》給他,又彈了一曲《春白雪》。
他聽著,找出羯鼓給伴奏。
在低沉的鼓聲裏,看著他,看見了他對出清淺的笑意。
又過兩日,他終于趕在午後回來。
于是在花園還未消融的積雪中,站在游廊下,在他面前,對著五十步外的箭靶,先中了一個八環,又連續中了九個十環。
興地跳了一下。他走過來,環住,就好像是跳在了他懷裏。
張弓搭箭,隨手放箭,楚王的一箭穿了箭靶,一直飛出去,飛遠,飛遠,死死釘了百餘步遠的另一牆邊。
箭靶。箭羽輕搖。
握住楚王的手臂,青雀的心幾乎比箭靶的震跳得還要快。
喜歡。
怎麽能不喜歡。
隨後,就是楚王的生辰。
這日清晨,青雀早早睜眼,邊當然還是不見楚王。
楚王早說過他今年不辦生辰宴。
以為他或許還有正事,有空了才會回來,青雀沒想問他在哪,碧蕊卻歡喜地對說:“殿下就在東廂呢,還沒走。我看,是等著孺人送禮呢!”
“是嗎。”穿上鞋,青雀快步走到窗邊了——寒冬臘月,窗扇合得嚴,窗紙又不明,當然什麽也看不見——帶著幾分急迫說,“快快,快給我梳妝!”
侍們笑著,作果然比往日更麻利,不到一刻鐘,就替挽好了長發,理順了襟。
披上鬥篷,青雀風一樣飛到東廂門邊。
“殿下!”走進去,正撞在楚王面前,被他挽了手。便笑:“殿下果真沒看嗎?”
“你再不來,我就要看了。”淺笑著,楚王環住,一同走室。
請他在案旁稍等一等,青雀自己來到書架前,找出被藏得嚴的畫。
楚王看著笑。
還真是怕他看嗎?
將禮抱在懷裏,青雀走回來,腳步有些遲疑。
畫的時候,滿心覺得已送不出更好的東西,可真要把禮遞到他面前,同他一起看了,又怕他不喜歡。
但又回不去十日前。現在,不送也得送了。
回到書案旁,放下禮,抿了抿,在他的注視下,青雀親手展開畫卷。
畫中場景緩緩展現,楚王不低了低頭,更加凝神。
這是一幅……他的畫像。
說是畫像,人像旁卻還有同樣致的景。那是分隔雲起堂前後的月門,他站在門邊,旁還有春日的綠意蒼翠。在半面樹影、半邊夕中,他仰起頭,靜靜地注視著什麽。
畫中他形瘦削,面容消瘦乃至枯瘦,眉眼更顯冷,目也似靜如枯水毫無波,卻落了點點淺淡的、夕的彩。
這是——楚王很快想了起來——這是青雀府的第二天,他看到了正秋千。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農門醫妃:妖孽王爺纏上門
天師世家第八十八代嫡傳弟子阮綿綿因情而死,死後穿越到大秦朝的阮家村。睜開眼恨不得再死一次。親爹趕考杳無音訊,親娘裝包子自私自利,繼奶陰險狠毒害她性命,還有一窩子極品親戚虎視眈眈等著吃她的肉。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姐弟三個過得豬狗不如。屋漏偏逢連陰雨,前世手到擒來的法術時靈時不靈,還好法術不靈空間湊。阮綿綿拍案而起,趕走極品,調教親娘,教導姐弟,走向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可是誰來告訴為什麼她路越走越寬,肚子卻越走越大? !到底是哪個混蛋給她下了種?桃花朵朵開,一二三四五。謊話一個個,越來越離譜。俊美皇商溫柔地說:那一夜月黑風高,你我有了魚水之歡。妖孽皇子驕...
32.6萬字7.73 30934 -
連載1973 章

3歲小萌寶:神醫娘親,又跑啦!
“娘親,你兒子掉啦!”小奶包抱緊她的大腿,妖孽美男將她壁咚在墻上:“娘子,聽說你不滿意我的十八般武藝?想跑?”沈云舒扶著腰,“你來試試!”“那今晚娘子在上。”“滾!”她本是華夏鬼手神醫、傭兵界的活閻王,一朝穿越成不受寵的廢物二小姐。叔嬸不疼,兄妹刁難,對手算計,她手握異寶,醫術絕代,煉丹奇才,怕個毛!美男來..
177.8萬字8 17475 -
連載1305 章

和離后毒妃帶三寶顛覆你江山
虐渣+追妻+雙潔+萌寶新時代女博士穿成了草包丑女王妃。大婚當天即下堂,她一怒之下燒了王府。五年后,她華麗歸來,不僅貌美如花,身邊還多了三只可愛的小豆丁。從此,渣男渣女被王妃虐的體無完膚,渣王爺還被三個小家伙炸了王府。他見到第一個男娃時,怒道“盛念念,這是你和別人生的?”盛念念瞥他“你有意見?”夜無淵心梗,突然一個女娃娃頭探出頭來,奶兇奶兇的道“壞爹爹,不許欺負娘親,否則不跟你好了,哼!”另一個女娃娃也冒出頭來“不跟娘親認錯,就不理你了,哼哼。”夜無淵登時跪下了,“娘子,我錯了……
231.7萬字8.18 9007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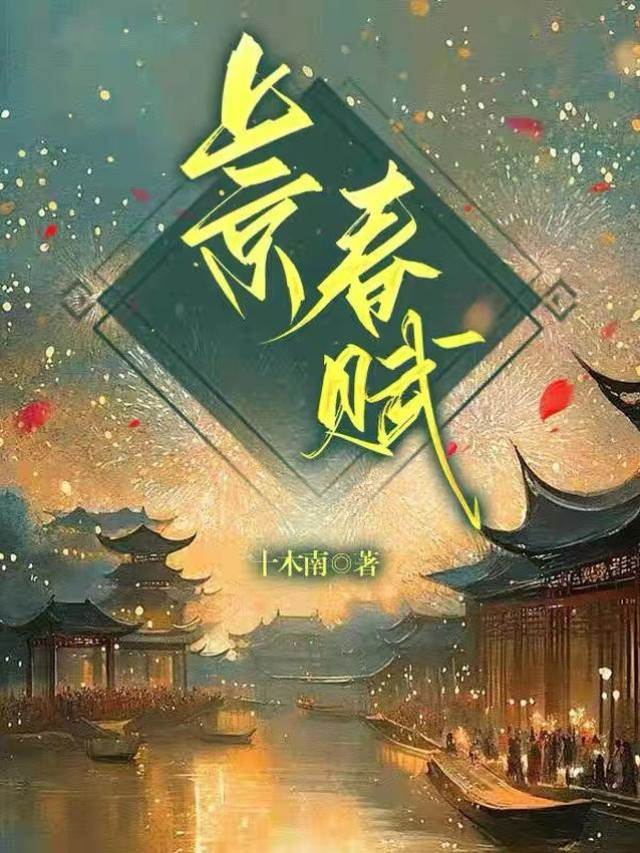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