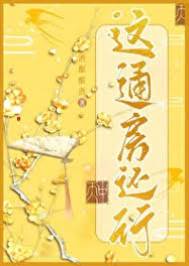《籠中青雀(重生)》 第120章 貴極人臣 封無可封。
第120章 貴極人臣 封無可封。
給太子賜婚霍珊時, 皇帝是想到了永興侯府實為軍功世家。可永興侯老夫人,是母後最後一位離世的兄弟姊妹,的這個孫, 婚事偏又格外坎坷, 讓人不由可憐嘆息。
既然太子主替他分憂,願意將最後一個良娣之位贈與霍家表妹,他也有心再提拔霍家一二,便應了這樁賜婚。
恰好,永興侯要丁憂三年。再起複, 也不必讓他再回兵部, 換一為,不在阿昱手下約束也好。
永興侯的三個兒子又一個比一個不。皇帝是氣惱他們混賬,卻也的確在某些考慮上更覺得輕松。
——誰知就連宋家也一并被東宮攏去了?
這才幾年!
“怪不得……”皇帝恍然冷笑,“怪不得, 朕還沒想起宋檀, 太子就同朕說起他已外放兩年。朕看也差不多了, 就把他調了回來, 原來是遂了他的心!原來,他們早背著朕埋伏起來!”
他看向驚慌的陳寶:“說!霍玥幾天一次東宮?一年要去東宮幾次?!”
“陛下……陛下!”陳寶早停了手中作, 臉上又是焦急,又是安,“霍恭人一個月只到東宮兩三次,都是去看霍良娣,太子妃有召才去拜見, 并非特地去見太子妃娘娘。上次去東宮……”
他想了想,小心道:“正是,九月初二日。”
九月初二日, 是江氏得賜“楚王次妃”的第二天。
前一天,陳寶去楚王府傳旨當日,東宮召集了臣屬議事,其中,沒有宋檀。
皇帝急怒的心稍有冷靜。
或許是霍玥這婦人自己的主意。他心想。宋檀還是一心忠于他的。
可也許只是東宮和宋家一起瞞他的手段!
正是因宋檀從不親去東宮,霍玥和東宮的切往來,才讓他忽視到如今!
Advertisement
心中有重重疑慮,皇帝又看向陳寶。
這奴婢,雖然跟了他幾十年,一向忠誠,方才說的那些話,也似只是寬他的心,可為什麽偏是他想讓宋家和江氏認親的時候,告訴了他這些?
“朕……”閉了閉眼睛,他沉聲,“知道了。”
陳寶緩緩把手向前:“那奴婢,接著給陛下肩?”
皇帝不出聲地頷首。
陳寶便又把雙手放在了陛下肩頭。
他覺得到,陛下的肩膀有一瞬僵了,但又很快放松,被他練地開。
……
宋檀到了。
不論是誰有心算計,是誰無意彀,又是誰的話語為真,誰在說謊瞞,皇帝都已暫時打消了讓江氏和宋家認親的想法。
人已召來,他便問了幾句家常:“你的孩子們還沒接回來?什麽時候去接?三姐兒都快兩周歲了吧。”
去年夏天,宋檀升任回京,幾個姬妾裏,有正懷胎的,也有已經生下了子,但孩子太小,不能一同上路的,他便都留在了江陵,待姬妾生育、子長大,都結壯了再送回來。
他的第二個兒——康國公府按排行論的“三姐兒”——是玉于景和二十七年十一月所生。
外人送的顧氏和徐氏,也分別于去年的六月和九月,給他生下了長子和次子。
淩霄又于今年三月生下了他的第三個兒子。
他現在是真正兒雙全,不再發愁子嗣了。
阿玥說得不錯:
就在他們親近東宮之後,他便接連得了三個兒子,還每一個都養活了。想必因東宮是國朝正嗣,福澤披到了他上。
提起自己的孩子,宋檀不免高興:“是,三姐兒正是十一月滿兩周歲。但大哥兒和二哥兒還小,二哥兒才要周歲,這就讓他們上路回來,臣還是不放心,便等明年開春,再一起接回來吧。”
Advertisement
“也是,還是小心些好。”皇帝笑道,“朕還記得你們小的時候,每一個都那麽弱,朕稍用用力,就覺得你們的胳膊都要折了。如今,也都長能為朕分憂的好男子了。”
陛下如此親近,宋檀更是歡喜,也不由慨,忙站起,要表白一二心跡:“陛下——”①
“你們都長大了!”皇帝擺手讓他坐,“從前都年輕,吵吵鬧鬧,你看他好像手段太過,他看你也總不順眼,但也都是過去的事了。”
他并不提楚王的名字,卻句句不離楚王:“現在,他是已經放下了,還求了你媳婦從前的伴讀做次妃。江氏倒很懂事。等他們大婚,把大姐兒接回去,你和你媳婦,也能常去看外甥了。”
他笑著,盯著宋檀的臉:“論起年紀,你還比他大了三歲,明年就到三十。三十而立啊!”
“……是。”宋檀遲疑地應了聲。
“你父親已年過花甲,近兩年,又不大好了。”皇帝品著他這份遲疑,仍是笑,“到你而立,朕便讓你先襲了康國公的爵位,也讓他安心頤養天年罷。”
“陛下!”驚喜和疑加,宋檀不免又站起,拜下,“臣——”
“但,就算做了國公,”他并不讓宋檀說出謝恩或推辭之語,“雖然江氏曾是你媳婦的伴讀,畢竟已是親王次妃,位同縣公,你們也該尊重,不可似從前一般輕視無禮。”
“陛下……”
“今後,江氏也算是大姐兒的母親。”漸漸地,皇帝放重語氣,“大姐兒的生母是你親妹妹,的養母,又曾同你們有段淵源,陪了你媳婦十幾年,你們,也應當可以親近?”
他認為自己說得足夠明白:
去親近楚王,親近自己的親外甥,別再靠近東宮!
Advertisement
可宋檀并不知曉前,只知陛下特地召他過來,先問了兩句家常,就一句又一句他再同楚王媾和,他尊重青雀這個他曾經的丫鬟!
陛下還特地施恩先讓他承爵,就是為了讓他不再和楚王作對?就是為了,讓他尊重楚王寵的姬妾?
陛下就對楚王如此疼寵,事事都要以他為先?!
“臣……遵旨。”松開牙關,宋檀叩首,“多謝陛下隆恩!”
皇帝當然聽得出來,他那沒能全然藏好的不服和不甘。
東宮,就這麽讓他留不舍?
“你……”皇帝膛起伏,語氣和藹,“知道了,就去吧。”
宋檀再叩首,恭聲告退。
皇帝喝一口茶,拿起一冊奏章。
他想到了宋、霍兩家曾經遍布軍中的舊部。
即便十五年前,康國公于東夏大敗,二十萬將士死傷殆盡,他畢竟還有許多軍中世!
他曾給過康國公多權柄,縱容這位表兄廣施恩德,籠絡了多軍中人心,當然是他自己最清楚不過!!
“混賬東西!”
皇帝沒能控制住怒氣,一把摔下了手中奏章。
-
至夜。
陳寶并非時時刻刻服侍在前。皇帝用過晚膳,他暫且離開也去用飯時,皇帝隨手召了一個午後不在,晚飯前才來當值的太監過來。
“九月初二日,霍恭人去看了霍良娣?”他似隨意問。
“好像……是有這回事!”那太監年輕些,只有四十來歲,也是在紫宸殿服侍多年的老人了。
答過這一句,他并不多說,只安靜等著陛下問下一句。
“一個月,去東宮幾次?”皇帝閉上眼睛。
“這……”太監仔細想了一想,“奴婢知道的,有時一兩次,有時三四次,上個月多些,共去了四次。再從前的,奴婢一時不能確定。”
皇帝從鼻孔裏發出一聲冷哼。
不管陳寶有沒有其他心思,霍氏常去東宮這事,總不是他憑空編造的。
對那太監擺手,皇帝讓他去。
陳寶畢竟從無錯。
罷了。他心道。用人不疑……用人不疑罷!
-
五日後。
重節後的第一個大朝會,聖人又加封楚王為正一品太尉。
太尉者,自秦漢至魏晉天下武之首也,統帥天下兵馬大權。②
在本朝,太尉雖無實職,只做加,但其為“三公”之尊,僅在太師、太傅、太保“三師”之下。
楚王之勳,早已在最高一階,正二品上柱國。其散,亦已在上月回京時,加至從一品“驃騎大將軍”。
至此,楚王已貴極人臣,再無可封。
-
當夜,太子輾轉未眠。
“父皇,是本沒給我留下後路。”慘笑著,他對趙良娣說,“封無可封,他已封無可封……”
“即便,我明日就登上大位,也再無辦法,給他施恩了。”他游在空曠的宮殿裏,“難道要把天下分他一半?”
“若不封!”他問著冰涼的空氣,“天下不會服我,他更不會服我!畢竟,我是毫無寸功的‘讀書太子’,他是功震天下、救民于水火的‘將星楚王’!他才是衆所歸!!”
趙良娣沉默地著太子,著一素羅單,赤足走在地上,仿佛覺不到寒冷的,的丈夫。
是死局了。
其實,自從楚王十七歲滅國東夏開始,東宮和楚王府,便已經是死局。
次日淩晨,星月尚明。
宮門未啓,太子便已梳洗完畢,換上一樸素袍。
趙良娣陪著他一夜沒睡,替他淨冠上的瓔珞。
“承恩公畢竟是殿下的親舅舅,從前也疼殿下至深。”又用帕給他抿了抿額角的虛汗,趙良娣笑著說,“殿下請寬心地去罷。”
“你等我。”太子握住的手,“我一定帶好消息給你。”
趙良娣微笑,輕輕靠向他肩頭。
是不會再給太子獻策了。太子有太多謀臣,而只是一個深閨婦人,一個妾。以的境,的份,說得越多,就錯的越多。要先在東宮裏保下自己。
但也還是希太子能贏。
和太子,共有五個孩子。是太子年請封的第一位良娣。太子登上大位,便不是貴妃,至也在一品妃位。
而若太子落敗,楚王上位,為先儲君的妻妾子,和孩子們……才是更難留下命。
猜你喜歡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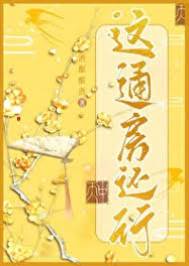
這通房還行
裴府上下皆傳: 主君的身體狀況很不樂觀,太夫人正在四處找尋合適的女子,送到主君屋裏給裴家留個後。 路過的小廚娘阿玖搖了搖頭,“聽起來好像給豬配種哦。” 剛入秋就身披厚氅、揣着暖手爐的主君:“……” 當晚,阿玖就被送到了主君的寢居。 阿玖是個鄉下來的小丫頭,一頓能吃三碗飯,嗓門還賊大。 考問她灶間香料估計能講得頭頭是道,可伺候養尊處優的主君,甚至當未來小主君的孃親,那就差些檔次了 ——裴府上下,從太夫人到伙夫都這樣想。 可阿玖非但沒被主君趕出來,反而一晚一晚地留下。 後來,小主君誕生了,主君的身子也漸漸好了起來。 太夫人:……也,也行吧。 【小劇場】 這一年冬天,裴延終於不用困在屋內喝那些苦湯藥。 他沉着臉跨上馬背,於簌簌飄雪中疾馳,攔在阿玖的牛車前。 眼神冷如霜刀,問出的話卻是可憐巴巴:“你不要孩子就算了,連我也不要?” 懷裏被顛吐了的小裴:? 阿玖咦了聲,從牛車探出頭來,“不是說留個後嗎,我完成任務可以回鄉下啦,表哥還等着……唔。” 小裴捂着眼睛跑開了。
22.7萬字8 9528 -
完結287 章

和渣夫同歸于盡后又雙雙重生了
【女主渣男雙重生+男主穿越+雙向救贖+扮豬吃虎】十七歲這年,沈嘉歲嫁于陸云錚為妻,沈陸兩家皆為將門,強強聯合。 成婚兩年后,陸云錚大敗敵國名揚四海,沈家卻因通敵叛國滿門抄斬。 沈嘉歲臨死前才得知,沈家通敵叛國罪證乃陸云錚親呈,且陸云錚想娶的人從來不是她,而是沈家養女,她視作親妹妹的顧惜枝。 滅門之仇,欺騙之恨,沈嘉歲臨死反撲,拉陸云錚同歸于盡。 再一睜眼,重回陸云錚上門提親那一日。 沈嘉歲匆忙趕到時,陸云錚正深情開口求娶顧惜枝。 原來,陸云錚也重生了...... ———— 沈家通敵叛國一事迷霧重重,牽涉甚廣。 為查清真相,沈嘉歲決然入局,這時,一人著緋紅官服站在了她的身旁。 沈嘉歲依稀記得,上一世咽氣之時,似有一片緋紅衣角闖進視野...... ———— 江潯:“江某平生所愿,唯山河遠闊,國泰民安。如今再添一愿,愿心上之人歲歲無虞,長安常樂。”
57萬字8.18 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