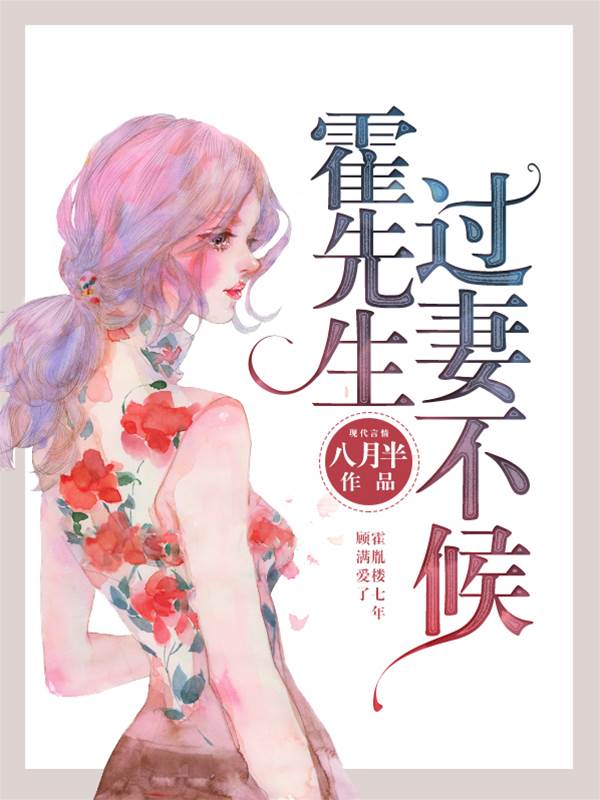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你另娶我他嫁,從此各不相干》 第三百五十七章 失蹤72小時了
護工迅速給注了鎮靜劑。
藥效發作前,秦箏最后嘶吼了一句:"你們等著……姜苒會死得比我慘一千倍一萬倍……"
救護車的門重重關上,刺耳的警笛聲漸漸遠去。
顧承言站在空的客廳里,腳下是碎玻璃和潑灑的紅酒,像極了一場慘烈戰爭的跡。
仁和醫院,神科病房
醫護人員剛做完檢查離開,病房里一片寂靜。
病床上的秦箏突然睜開眼睛,哪里還有半點剛才瘋癲的樣子。
敏捷地從病號服袋出一部微型手機,快速編輯了一條短信:【功躲過懷疑,一且按計劃進行,一定不要讓姜苒好過,先個半死再說。】
發送功后,刪掉記錄,將手機藏回原,角勾起一抹毒的笑。
三天后。
賀氏集團總裁辦公室,賀岑州盯著電腦屏幕,眼下是濃重的青黑。
他已經72小時沒合眼了,桌上的咖啡涼了又換,換了又涼。
Advertisement
"岑州,你好歹吃點東西,"陸蕭推門進來,手里端著餐盤:"再這樣下去,姜苒認還沒找到,你先垮了。"
賀岑州頭也不抬:"查得怎麼樣?"
"秦箏確實被送進了神病院。"陸蕭將平板遞給他:"技部追蹤到信號來自醫院部,但 位置無法確定。"
賀岑州猛地站起:"去仁和醫院。"
"等等!"陸蕭攔住他:"我剛從研究所回來,駱埔說欒黎現在的狀況本不可能參與綁架。"
"有人替做,"賀岑州抓起外套,"向月天的爪牙都一直沒有放棄。"
陸蕭猶豫了一下:"駱埔……好像對欒黎了真。"
賀岑州冷笑一聲:"帶我去見欒黎。"
醫學研究所。
欒黎躺在特制病床上,上連著各種監測儀。
比起從前那個彩照人的跳水冠軍,現在的完全瘦得了形,臉蒼白如紙。
Advertisement
"現在的狀況,連下床都困難,"駱埔站在一旁,語氣復雜:"不可能參與綁架。"
賀岑州走到病床前,居高臨下地看著欒黎:"姜苒在哪?"
欒黎緩緩睜開眼睛,眼神渙散:"姜......苒......"
"別裝了,"賀岑州冷聲道:"向月天的人是不是跟你聯系過?"
聽到這個名字,欒黎的明顯抖了一下:"我……不……知道……"
"賀總,"駱埔上前一步:"可以了,真的什麼都不知道,這半年來,的腦損傷導致記憶嚴重缺失,連自己是誰都經常忘記。"
賀岑州盯著欒黎看了許久,突然俯在耳邊低語:"如果你敢說謊,我會讓泥生不如死。"
欒黎的瞳孔驟然收,手指無意識地抓了床單。
駱埔見狀,嘆了口氣:"賀總,我承認我對欒黎有,但我不至于失去理智,現在的狀況,已經是最大的懲罰了。"
Advertisement
賀岑州直起,眼神冰冷:"希你說的是實話。"
離開研究所時,賀岑州神恍惚,差點被一輛疾馳而過的卡車撞上。
"賀岑州!"陸蕭一把拉住他:"你清醒清醒,你不能這樣下去了!姜苒還等著呢去救呢!你要是先倒下怎麼辦!"
賀岑州甩開他的手,聲音嘶啞:"三天了......可能已經......"
猜你喜歡
-
完結361 章

萌寶三隻:爹地請排隊
20歲,陸傾心被算計生子,虐心。25歲,陸傾心攜子歸來,讓別人虐心! *三隻萌寶*天佑:「我是藍孩子,完全可以勝任『爹地』一職。」天煜:「我……我喜歡醫生哥哥做爹地!」天瑜:「人家要桃花眼蜀黍做爹地……嚶嚶嚶……」正牌爹地喬BOSS,不是醫生,木有桃花眼,心塞咆哮:「三隻小崽子,你們放學別走,我們聊聊人生!」陸傾心:「大丫、二狗、三胖,回家吃飯!」三寶異口同聲:「媽咪,請務必喚我們大名!」
87.6萬字7.5 19819 -
完結479 章

夫人,總裁他罪不至死
「林小姐,你可曾愛過人?」「自然愛過。」「如何愛的?」「剛開始,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愛他。」「後來呢?」「後來啊,我恨不得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去死。」認識林羨的人都知道,她曾在感情裏栽過一個大跟頭,爬起來的樣子很狼狽,當時她一個人在原地站了很久,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後。因為,不管往前走,還是往後退,都是粉身碎骨,要命的疼……
101.2萬字8 15151 -
完結305 章

撒旦總裁追逃妻
五年前,她為養母委身于他。沒有完成契約便不辭而別,杳無音訊,順便帶走了他的一對雙胞胎。 五年後,她帶著愛與哀愁歸來,躲躲藏藏,與他形同陌路。一場意外的醉酒,讓他識得廬山真面目。 翻開舊時契約,他要求她繼續未完的義務。 她瀕死掙扎,所有的牽掛,不過是給他為所欲為的借口…… “爸爸!” “爸爸!” 兩張天使般的面孔出現在眼前,他愣了又愣,沒敢相認。 不能讓他搶走自己的雙胞胎兒女,她努力雪藏,抵死不認。 “一周才四天……太少了,不行!” “不少了呀!”方心佩掰著手指頭替他計算,“你想想看,一周總共才七天,扣掉了四天的時間,你只剩下三天給別人,恐怕還要因為分配不均,讓人家打破頭呢!” 看著她那副“賢惠”的模樣,程敬軒差點被氣得吐血。這是什麼話?自己的這個情人也算是極品,居然還替他考慮得這麼周到?
41.3萬字8.09 112976 -
完結374 章

太子殿下恕不約
一朝穿越,作為主任法醫師的她成了那個軟弱無知的小村姑人盡可欺?葉琳表示不慌,她最擅長以牙還牙,隨隨便便就能教那些個不長眼的做人。等她這鄉村生活越過越滋潤,突然有人告訴她,她是當朝相爺的女兒?好的,這座大山不靠白不靠,她就是認了這便宜爹又如何。回到京城,葉琳早已做好與各路神仙鬥爭的準備,卻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惹上了那個最不能惹的太子殿下。等等,這位殿下,您有點眼熟啊。
68.9萬字8 6939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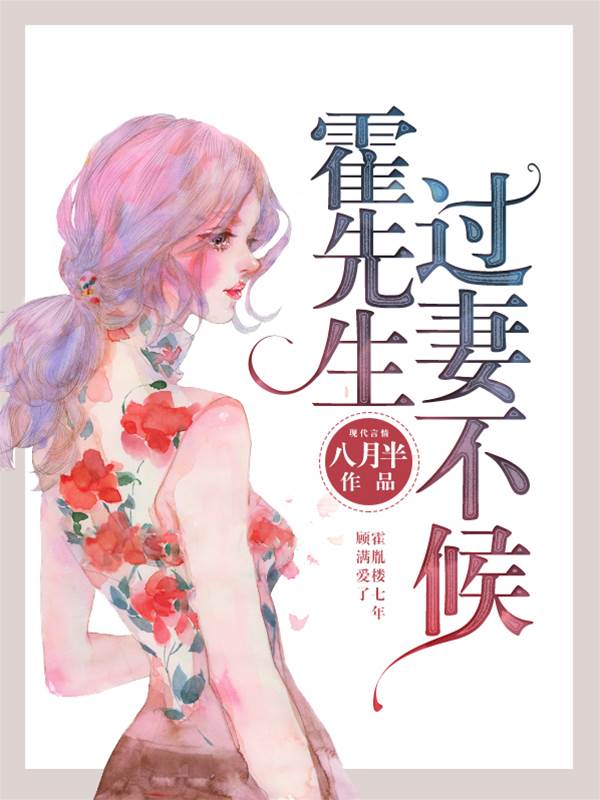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