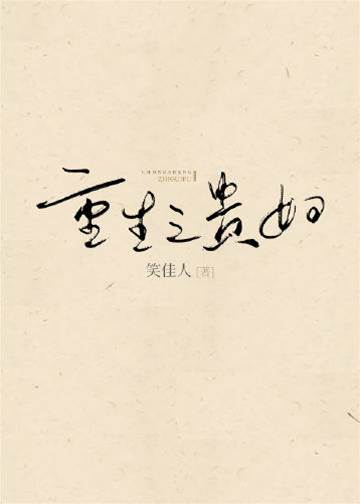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誘她上榻,爺的小婢女是禍水》 第1卷 第11章 南珠偷偷賺錢贖身
夜,惠嬤嬤忙完回房,瞧見南珠在刺繡。
走過去,從籃子里拿出一個看,只見那帕上鯉兒栩栩如生,甚至生,不得一番夸贊。
“南珠姑娘,你的手竟這樣巧,這錦鯉簡直像活的要跳出來一樣,怎麼繡的?”
南珠也十分欣賞自己手藝,只不過被夸了不得又要臉紅,和惠嬤嬤解釋:“只要在邊上多繡一層暗線,深淺過渡,瞧起來就像是活的。”
“實在厲害。”
南珠微笑著:“嬤嬤喜歡,我有空也給您繡個荷包。”
自己繡的這些要拿出去賣的,攢夠銀子贖,不過事關要,不敢輕易。
惠嬤嬤自是高興,仔仔細細觀察著帕子上的刺繡,再次夸道:“手藝這麼好,若是在外面開鋪子,生意一定紅火,不刺繡,你白日里熬的茶,我老婆子第一次喝,到現在還念著那味道。”
惠嬤嬤所說,正如南珠心中所想。
“待我日后出了府,確實有去外面做生意的打算,不至于再去賣苦力。”
只是,現在首要的,是趕攢夠銀子贖,這些年有些積蓄,如果在小姐出閣前多賣些繡品,也是能夠的。
“南珠姑娘有志氣。”惠嬤嬤瞧著南珠手如荑,面龐清秀,越瞧越喜歡:“你跟在爺邊,也能學到許多。”
再者,爺第一次容納子近,必然是喜歡的,惠嬤嬤不得他把南珠收了。
南珠滿腹心事,不知惠嬤嬤所想:“我只是暫時過來幫忙幾日罷了,設宴一事完了,還要回四小姐那邊。”
想起四小姐,南珠眼神暗了下去。
怕只怕銀子夠了,四小姐不肯放走。
惠嬤嬤對南珠的事也有所耳聞,只覺得實在可惜了南珠。
Advertisement
“南珠,你覺得爺怎麼樣?”
南珠冷不丁聽惠嬤嬤這樣問,心不揪了起來:“爺宅心仁厚,如菩薩般慈悲,是個好人。”
只是,酒品差了些,南珠心里這樣琢磨著,腦中又浮現那日爺的……
惠嬤嬤見臉紅,只當南珠心里也慕爺。
爺這般人,誰能不呢,京城里那些世家小姐破腦袋都想嫁給他。
惠嬤嬤道:“爺潔自好,邊從沒有過人,我瞧爺對你也是極好的,今日爺沒有傳晚膳,你瞧怎麼著,竟是把你熬的茶都喝了。”
南珠差點扎到手。
懷疑自己的耳朵:“爺喝了我熬的茶?他怎麼會有?”
惠嬤嬤納了悶:“不是你熬的嗎?”
南珠想說不是,話到邊,又咽了回去。
定是云初給爺的!
—
是夜。
沈燕白捂腹再次打開房門,云初一直守在外頭,連忙向前攙他,目擔憂:“爺都怪我忘了提醒你,茶里有羊,您喝不得。”
沈燕白喝羊會肚疼,今夜都跑了五六次凈房,眼下這況,估著今晚都別想歇了。
沈燕白面難耐:“送之前你沒想起來?”
“那會滿腦子都是想將南珠做的給您嘗嘗,沒想起這些。”
云初萬分疚。
難怪爺喝的時候,他總覺得有什麼重要的事忘記告訴他了。
沈燕白咬牙道:“飛鴿傳信,明日宴席延遲!”
“是。”
昨夜南珠知道云初將的茶端給沈燕白后,心中忐忑不安。
沈燕白畢竟是松云居的主人,給他邊的人做了吃的,卻沒給他做,不太妥當。
于是又一大早起來去廚房做早膳。
門口遇到云初,問:“爺用完早膳了嗎?”
Advertisement
沈燕白不準將昨晚事宣揚出去,云初忍住沒告訴南珠,心虛地搖搖頭:“爺沒胃口,在書房辦公。”
昨夜沈燕白幾乎一宿沒睡,早上胃口盡失,一早就去了書房。
長桌上有幾款布料,是明年開春主要售賣的料子。
南珠敲了門,得到允許后端著盤子進去。
“爺,您前日里醉酒傷胃,我給您熬了銀耳湯。”
沈燕白將桌上的布料卷作一旁,好整以暇打趣:“今日送來是不是遲了些?”
南珠咬著牙,見他戲謔模樣,紅著臉找了個蹩腳的理由:“昨天忙忘了。”
知是心虛,沈燕白沒拆穿,先嘗了一口,吃出不對勁來:“是什麼做的?”
南珠道:“是羊和銀耳,奴婢還放了紅棗。”
沈燕白眉心狠狠一跳,捂著咳了起來,模樣甚是慘烈。
南珠被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到了,趕給他拍背順氣:“爺是不是嗆到了?”
一顆心高高提起,南珠張到手心冒出冷汗。
糟了,爺要是吃出個什麼好歹來,十個也不夠賠,以后再也不給他做吃食了!
沈燕白瞧,俏眉鎖,目擔憂,不想竟如此關心他。
他心神漾,可惜胃里又翻江倒海,他握拳忍痛,告訴實:“我不能喝羊。”
“啊?”南珠沒想到竟是這樣:“爺昨晚不是還喝了茶?昨夜有哪里不適嗎?”
沈燕白:“只是腹痛。”
“現在痛嗎?”
南珠擔憂地看向他腹部,又急急瞧他面,不小心撞進那雙似笑非笑的眼眸,清亮又深邃。
沈燕白與那雙圓眼睛一對,嗅溫香,比任何藥都好使,心坎里熱乎乎的,只知人比花,哪有甚麼腹似刀絞。
Advertisement
南珠見他只看著自己,也不說話,真的十分害怕。
他是高高在上份尊貴的大老爺,只是一個生死不由己的小丫鬟,害他吃壞了,老夫人若是知道了把打死怎麼辦?
急的眼圈兒紅,就要哭似的:“爺這是怎麼了?”
不會吃傻了吧!
沈燕白輕咳一聲,掩飾尷尬:“沒什麼,只有點疼。”
“要不傳大夫來瞧瞧吧?”
說著,南珠掉出眼淚來。
沈燕白替拭去淚,下將摟進懷中的沖,聲道:“怎麼哭了?”
南珠淚眼婆娑:“爺子金貴,吃壞了,再落了病,我就死翹翹了。”
“我好端端的,你怎麼咒我?”沈燕白竟不知子掉起淚來會沒完沒了,從袖籠中拿出手帕,掉南珠臉上淚水,放輕了聲音半哄著:“怪我前日喝酒傷胃,這才嚴重些,你若不放心,扶我去榻歇歇。”
他拿出一本書,遞給:“你守在一旁給我念書罷。”
南珠吸著鼻子接過來翻看幾頁,心里想著怎麼讓爺換個陪法,卻聽沈燕白輕咳幾聲,提醒:“拿倒了。”
南珠鬧了個大臉紅,書重重放回去,只得實話實說:“爺為難人,我不認得字。”
沈燕白不為難:“我睡覺,你隨便做什麼。”
南珠欣然接,正好可以做些私活。
—
“南珠,南珠。”
這日,天還沒亮,南珠悄悄出了松云居,去了花園一個偏僻角門。
門旁邊的石頭后面,有個圓頭圓臉的小丫頭探出腦袋小聲喊。
蘭花和南珠一樣,是做活的小丫頭,因為不夠機靈,也經常被夫人院里的大丫鬟欺負。
南珠跑過去,和躲在石頭后面,將手中的籃子遞給:“這一批已經做好了。”
籃子里有各種繡品,云肩、手帕、腰帶等。
這一批加起來可以賺到五百文,蘭花負責賣和接活,南珠負責刺繡。
出手的繡品賣相極好,這些都是別人定制的,提前付過定金,待蘭花送出去后只管收剩下的錢,和南珠對半分。
大夫人隔三差五要吃德樓的點心,差蘭花出去買,每次排隊要排將近半個時辰。遇到要接活的日子,蘭花天不亮就出門。
們已經做了兩三年,荷包里賺了不銀子哩。
“這里面還有個斗篷,是松云居的燕爺賞賜我的,我洗干凈繡了新花樣,你拿去賣了,這斗篷料子金貴,定值不錢。”
“大爺對你可真好。”
蘭花把這些仔細東西收好,還悄告訴南珠一個好消息:“南珠,我馬上可以回家啦。”
南珠不由得震驚:“你哥哥來贖你來?”
蘭花點點頭,滿眼都是笑的樣子:“我娘說哥哥在揚州人看重,當上了藥鋪的掌柜,很快就會把我贖出去,讓我再耐心等一個月。”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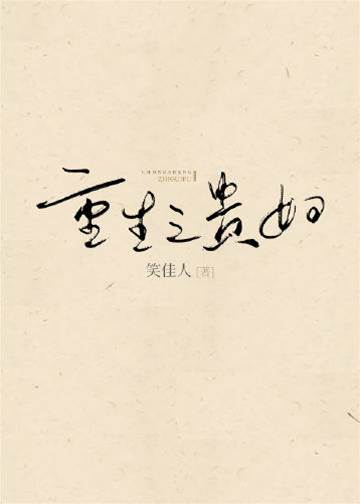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828 章

我是旺夫命
一朝穿越,鐘璃不幸變成了莫家村聞名內外的寡婦,家徒四壁一地雞毛也就罷了,婆婆惡毒小姑子狠心嫂子算計也能忍,可是誰要是敢欺負我男人,那絕對是忍無可忍!我男人是傻子?鐘璃怒起:這叫大智若愚!他除了長得好看一無是處?鐘璃冷笑:有本事你也那麼長。鐘…
170.9萬字8 233467 -
完結149 章

開封府美食探案錄
開封府來了位擅長食療的女大夫,煎炒烹炸蒸煮涮,跌打損傷病倒癱,飯到病除!眾人狂喜:“家人再也不用擔心我的身體!”但聞香識人,分辨痕跡……大夫您究竟還有多少驚喜是我們不知道的?新晉大夫馬冰表示:“一切為了生存。”而軍巡使謝鈺卻發現,隨著對方的…
45.8萬字8 13472 -
完結930 章

毒醫狂妃:誤惹腹黑九王爺
傳聞,相府嫡長女容貌盡毀,淪為廢材。 當眾人看見一襲黑色裙裳,面貌精緻、氣勢輕狂的女子出現時——這叫毀容?那她們這張臉,豈不是丑得不用要了?身為煉藥師,一次還晉陞好幾階,你管這叫廢材?那他們是什麼,廢人???某日,俊美如神邸的男人執起女子的手,墨眸掃向眾人,語氣清冷又寵溺:「本王的王妃秉性嬌弱,各位多擔著些」 眾人想起先前同時吊打幾個實力高深的老祖的女子——真是神特麼的秉性嬌弱!
153.2萬字8 334465 -
完結371 章

惑君
嫡姐嫁到衛國公府,一連三年無所出,鬱郁成疾。 庶出的阿縈低眉順眼,隨着幾位嫡出的姊妹入府爲嫡姐侍疾。 嫡姐溫柔可親,勸說阿縈給丈夫做妾,姊妹共侍一夫,並許以重利。 爲了弟弟前程,阿縈咬牙應了。 哪知夜裏飲下嫡姐賞的果子酒,卻倒在床上神志不清,渾身似火燒灼。 恍惚間瞧見高大俊朗的姐夫負手立於床榻邊,神色淡漠而譏諷地看着她,擡手揮落了帳子。 …… 當晚阿縈便做了個夢。 夢中嫡姐面善心毒,將親妹妹送上了丈夫的床榻——大周朝最年輕的權臣衛國公來借腹生子,在嫡姐的哄騙與脅迫下,阿縈答應幫她生下國公府世子來固寵。 不久之後她果真成功懷有身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嫡姐抱着懷中的男娃終於露出了猙獰的真面目。 可憐的阿縈孩子被奪,鬱鬱而終,衛國公卻很快又納美妾,不光鬥倒了嫡姐被扶正,還圖謀要將她的一雙寶貝兒女養廢…… 倏然自夢中驚醒,一切不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看着身邊沉睡着的成熟俊美的男人,阿縈面色慘白。 不甘心就這般不明不白地死去,待男人穿好衣衫漠然離去時,阿縈一咬牙,柔若無骨的小手勾住了男人的衣帶。 “姐夫……” 嗓音沙啞綿軟,梨花帶雨地小聲嗚咽,“你,你別走,阿縈怕。” 後來嫡姐飲鴆自盡,嫡母罪行昭彰天下,已成爲衛國公夫人的阿縈再也不必刻意討好誰,哄好了剛出生的兒子哄女兒。 形單影隻的丈夫立在軒窗下看着母慈子孝的三人,幽幽嘆道:“阿縈,今夜你還要趕我走嗎?”
61.6萬字8 10053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