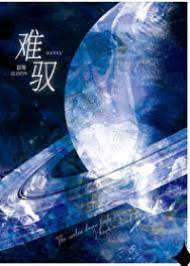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引長夏》 第82章 長夏
第82章 長夏
第八十二章
列車從北到南一路高速行駛, 窗外景從一無際的平原轉為青翠滴的江南寫意,停靠在南禮站時,已經接近傍晚時分。
踏出列車車門, 撲面而來的熱瞬間悶出一層汗, 桑渝皺了皺鼻子,“南禮今天不是有雨嗎?”
溫斯擇推著行李箱向前走, “晚上有雨。”
他看了眼漸沉的天,“快點回家吧。”
桑渝想到昨晚報給溫外婆的菜名, 了角跟上。
回到靈溪時, 樹枝搖擺,悶雷聲在天邊滾,天黑沉得不到邊際, 一副風雨來的架勢。
路上行人腳步匆匆, 桑渝溫斯擇也不例外。
都想在風雨顧前閃進家門。
桑渝溫斯擇還算幸運,雨滴攆著後腳跟,在他們跑進桑渝家單元門的下一秒砸落下來。
桑渝上念叨著好險,噔噔噔爬上三樓打開家門, 溫斯擇提著行李箱跟在後面。
今天剛打掃過的房間一塵不染,空氣中飄過清新的檸檬香味,室外雨勢湍急,拍打得玻璃窗啪啪作響,桑渝塞了把傘給溫斯擇。
雖然腸轆轆, 可現在一是汗, 準備洗個澡再過去。
兩個單元樓門距離不過幾米, 從這邊能見三樓窗口出的暖黃燈, 年形矯健步伐輕盈,手裏握著傘沒打開, 踏著雨水跑過去,樓道裏的聲控燈從一樓亮到三樓不過幾秒時間。
溫斯擇站在家門口勻了勻呼吸,手撥弄下發梢的雨水,掏出鑰匙開門。
客廳的燈開著,飯菜已經端上餐桌,只是不知道擺放了多久,看起來已經涼了。
外婆坐在沙發上,聽到開門聲擡起頭來。
“外婆。”溫斯擇含笑了一聲,站在門口換鞋。
卻沒有得到往日熱絡的回應和迎接。
Advertisement
臉上笑容稍凝,他停下作向裏看,外婆仍坐在那,戴著花鏡的臉上看不出喜怒,手上正翻過一頁上攤開的書。
靜靜看了他幾秒,外婆他:“小擇,你過來。”
溫斯擇垂頭看一眼腳上還沒換的鞋,結不自覺滾了滾,他將背包放到鞋櫃上,走到距離外婆兩米初站定。
“小擇,我問你,A大和B大聯系你了嗎?”
窗外風雨聲依舊,房間的空氣卻像是凝滯住了,抑沉悶,安靜到落針可聞。
心裏咯噔一聲,溫斯擇擡首對上外婆沉靜的目,緩過幾秒出聲:“聯系了。”
“那你的意思呢?想讀哪所?”
“我……”結不安地滾了滾,一滴汗順著耳後向下去,溫斯擇了,艱難出聲:“我還沒考慮好,想和——”
“還沒考慮好,”外婆打斷他,語氣很輕地重複一遍,低下頭去,“還沒考慮好。”
很輕的書頁翻聲響起,溫斯擇視線跟著挪過去,在看清外婆上的書籍時瞳孔驀地一。
“你考慮過嗎?!”
書籍和話音一起砸過來。
溫斯擇僵站在原地沒,厚重的書籍砸在他肩膀上,嘩啦啦地翻頁聲後,嘭的一聲掉在地板上。
被書角砸過的肩骨一陣尖銳的痛,垂在邊的手指輕著蜷起,握拳頭,溫斯擇低下頭。
“你外公是怎麽死的?!”
“你媽媽是怎麽死的?!”
“你難道都忘了嗎?!”
“你看看這個家裏,現在還剩下誰?!”
“誰家像我們一樣?!”
外婆蒼老的面容抖著,聲淚俱下地質問,一字一句砸得溫斯擇擡不起頭來,他咬住,眼眶發紅,說不出一句話。
“你知道我最怕什麽,你知道我最怕什麽,你知道我最怕什麽啊小擇。”
Advertisement
外婆捂了下心口,聲音抖著,越來越輕,“你要讓我,白發人再送黑發人嗎?”
“你當初答應我參加奧賽,是不是想拿獎牌換志願?”
溫斯擇驚懼地擡起頭,對上外婆沉痛的目和蒼白的爬滿皺紋的臉,心髒驀地一痛,膝蓋下彎,嘭一聲直直跪在地上。
*
桑渝洗完澡時雨勢減弱了些,手機上有一通容筱的未接來電,才想起回家後忘記報平安。
換好一幹淨服,桑渝將發攏了攏,一邊回撥容筱電話,一邊出了門。
雨不大,沒撐傘,手掌搭在額頭上小跑著到隔壁單元,上“嗯嗯”應著容筱的問題,一步兩個臺階地往樓上跑,到門外時掛斷電話。
房門開著一條細,像是特意給留的。
桑渝笑著推門進去,了一聲“外婆”,站在門口換上一雙白拖鞋。
溫斯擇的背包還丟在鞋櫃上,客廳的燈開著,裏面沒人應,只有廚房方向嗡嗡地微波爐轉聲響。
桑渝扶著鞋櫃邊的牆向裏探頭看,客廳沒人。
換好了鞋,拐進廚房,溫斯擇站在微波爐前,單手撐著旁邊臺子,眼睛直勾勾地看著前方,不知道在想些什麽,連進來都沒發現。
桑渝靠在門邊沒,靜靜看著他,等他回神。
廚房的窗戶開著,涼涼的夜風帶來舒適的溫度。
微波爐裏暖黃微散發著暈,排骨的香味順著隙飄出來。
桑渝聳了聳鼻子。
“叮”一聲,微波爐停了。
溫斯擇回神,拉開微波爐門,端出裏面的盤子。
“不燙嗎?”桑渝倏然出聲。
溫斯擇這才覺到燙似的,將盤子放在一旁,擡起眼看。
剛剛著盤子的指腹燙得通紅。
桑渝皺了下眉,走過去拉過他的手放在冷水管下沖。
Advertisement
夏天的冷水管水溫偏高,對燙傷并不能緩解,桑渝讓他先沖著,回打開冰箱,在裏面翻找冰袋。
外婆將東西收納得極其整齊,桑渝在角落裏翻出兩個閑置的冰袋,一回,溫斯擇正站在後,冷水管還在嘩嘩淌著水。
“怎麽跟過來了啊。”桑渝笑一聲,拿過一個盆子將冰袋放進去,牽著他往回走,盆裏接滿了水,通紅的指腹浸,擡起頭時和溫斯擇的視線撞上。
他視線發直,像是困久了,眼睛一眨不眨,琥珀眼眸上還蒙著一層水,要不是眼角幹幹淨淨,還以為他是哭過。
桑渝在他眼前打個響指,笑著問他:“困啦?”
“嗯,”溫斯擇收回視線,了浸泡在冷水中的手指,“不疼了。”
“怎麽會!”桑渝摁住他手臂,不然他拿出來,“我又不是沒被燙過,你老實泡著,至要15分鐘的。”
著他的手腕看他手指,好在只是紅腫,沒有起泡。
“外婆呢?”桑渝問。
“吃完藥先睡下了。”溫斯擇看著頭頂的發旋輕聲回答。
“怎麽了嗎?”桑渝擡起頭。
“沒事,”溫斯擇垂下眼睫,結滾了滾,音裏有一不易察覺的艱,“就是,太晚了。”
他看向滿肩的發,“又沒吹幹?”
“你不也是麽?”桑渝瞟向他著的發梢。
指針即將指向晚上九點,桑渝沒再追問外婆的問題,“那我們快一點吃好,你也早點休息。”
試了一下盤子溫度,端去餐桌,站在微波爐前又加熱其他幾道菜,小小地了一個懶腰,忽地想到容筱的電話,轉頭看向溫斯擇。
溫斯擇眼神發直,落點在上。
“我媽說小廣場過幾天要修整,梧桐樹那裏要修一個平臺,地面加高後鋪上一層木地板,溫斯擇,”桑渝低聲音,“我們得找個時間,把千紙鶴挖出來。”
千紙鶴……
溫斯擇心髒有一層刺麻麻地滾過一般,他眨了眨眼,目低下去,“好。”
出浸泡在水裏的手指,出一張紙巾拭幹淨,“吃過飯去吧。”
雨夜靜寂,小廣場上的梧桐樹冠茂盛如華蓋,細微雨過枝葉間隙,滴落在後背上,竟驚人的涼。
桑渝還記得當初埋下千紙鶴玻璃瓶的大概位置,和溫斯擇拿著工,慢慢地挖。
還記得當初埋下瓶子時也是這樣的雨夜,不同的是,那晚而森冷,他們懷著告別的心,哭著將它一點點埋起,不知以後有沒有再見它的可能。
不像今天,即使落著雨,夏日夜晚也是熱的,它也比他們早預計地出現。
桑渝撐開傘,擋住不時“襲”的雨滴,“挖出來後我們藏在哪裏呢?要不還是放在我床下吧?”
溫斯擇作一頓,複又繼續挖掘,“我自己收好吧。”
“那你注意藏好。溫斯擇,你打算什麽時候和外婆提——”
忽地,溫斯擇手裏的工杵到一個堅件,他停下作,手扶了扶,一段明玻璃瓶出來。
桑渝顧不得再問,將周圍的土塊松,過了好久,兩人終于將玻璃瓶挖出。
桑渝拿出準備好的紙巾將瓶清理幹淨。
沉埋在地下十年,玻璃瓶口的金屬蓋已然生鏽,裏面的千紙鶴展著翅膀,仍栩栩如生。
兩人將這裏填好,撐傘往回走。
坐了一天車,渾上下的骨頭都是疲累的,再加上晚上做賊似的折騰了這麽久,桑渝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在樓下告別溫斯擇,噔噔噔地爬上去。
溫斯擇撐傘站在樓下,手裏拎著一瓶千紙鶴,目追著樓道裏的聲控燈從一樓到三樓。
不多時,三樓一扇窗後亮起燈,桑渝推開窗,半趴在窗臺上,揮手和他道別。
溫斯擇勾起角笑,示意桑渝回去,等那扇窗戶關上,窗簾去亮,角笑容落下來。
燙傷*的指腹住生鏽的瓶蓋,從指尖一路疼到心髒。
他收起傘,垂下肩,在蒙蒙細雨中走向垃圾桶,站定許久後,將玻璃瓶扔了進去,轉離開。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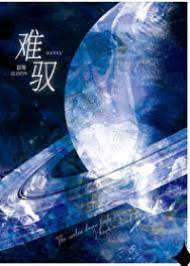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