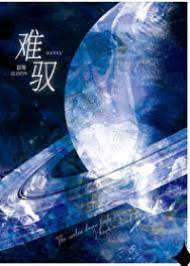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封心鎖愛后,我追的高嶺花失控了》 第1卷 第57章 你們就饒過你們文媽吧
聽見這話,王芳拽著謝家雄的手腕是更加用力了。
謝家雄著自己手腕的力道,他把覆蓋在臉上的紙巾扯了下來。
第一眼,看見的就是角落里的岑寂。
岑寂安靜的坐在桌前,帶著冬日的冷,高的鼻梁架著金框的眼鏡,模糊了他眼底的緒。
他瓣的很淡,和煦的似能過他冷白的皮,把他曬化了。
謝家雄心里咯噔一下,這才反應過來自己說了什麼。
他咬了咬瓣,連忙端起桌面上的高腳杯,從位置上站了起來:“別說以前的事了,其實我現在也沒那麼哭了。”
“文媽,只要知道你現在仍舊這麼優秀、這麼好,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高一的時候都沒人跟我做朋友,他們覺得我娘娘腔,覺得我很奇葩。我績也不好,一直很自卑。”
“直到我高二遇見了你,你說我就是我,向沒有任何異于常人的地方,任何的向都是正常的。你教我英語,說我很值得朋友。”
謝家雄想到從前的事,含笑的眼睛里帶著些許意:
“你帶給了班級每一個人溫暖,后來大家在群里一起為你反黑,一起幫你找妹妹,跟七班炫耀姑姑送來的夜宵……”
“大家為了同一件事共同努力,大家也都跟你一樣,不把我當異類,我才知道了什麼友誼的難能可貴。”
Advertisement
“這杯酒我敬你。”
文昭看見謝家雄又哭又笑的樣子,眼眶也的,有點模糊。
其實過了高中之后,無論是讀了大學的本科還是研究生,就再也遇不到這樣純粹的和這樣純真的人了。
高中時期的青蔥和天真,再也回不去了。
文昭今天是經期的第二天,其實小腹還有些酸痛,但是心里也莫名的想要喝酒。
不經意的捂了捂自己的后腰,就去拿過桌邊的酒杯,和謝家雄杯:“家雄,能夠在高中遇見你,我也覺很幸運。”
明的玻璃杯在日下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響。
杯中的酒紅搖晃,文昭抿了一口。
王芳聽見這話,也想起了從前的事,突然有些嘆:
“謝家雄確實一直惦記你,原本咱們和六班有個小群,文媽后援會,后來就被謝家雄改媽媽去哪兒了。”
“我上了大學之后,才發現再也沒有像五班一樣的班魂了。”
“我也很想要敬你一杯。”
其他同學也紛紛起哄的道:“是了,沒有你五班就沒了團魂,我也要排隊跟你喝一杯。”
“文媽你之前一聲不吭就走了,這酒必須喝了!就算是敬五班!”
文昭眼眶的,心里其實有些疚,于是重新在高腳杯里倒滿了葡萄酒。
雙手著酒杯,然后眼前的疊的酒杯相。
Advertisement
“是因為有了大家,五班才有團魂,因為大家的幫助,才讓我次次化險為夷。”
“四年前我走得太倉促,是我的錯,我向大家賠罪。”
文昭的話音剛落,就想要仰頭把酒喝掉。
可也就是此刻,眼前突然出了一只骨節分明的手。
文昭一愣,看見的就是冷黑的腕表,在眼前晃,閃著金屬的澤。
那是岑寂的手。
男人微涼的指腹過文昭的皮,又是接過了手里的酒杯。
葡萄酒在杯中搖晃,掀起小小的波瀾,險些要灑落了出去。
岑寂頎長的子過熙攘的人群,擋在了文昭的前。
他含笑著向同學們開口,溫文爾雅,上的襯衫潔白:
“四年前的事不是文昭的錯,昭昭后來告訴了我,是我沒說。”
“我的錯,讓大家擔心了,我替喝。”
眾人一愣。
就見岑寂持著的酒杯,與同學們輕輕杯,隨即仰頭,喝掉了杯里的葡萄酒。
酒紅的浸他的瓣,吞咽時結上下滾。
他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岑寂用得是文昭喝過的酒杯。
意識到這點之后,所有人幾乎都要沸騰起來。
王芳的眼睛在瞬間亮了,急急的拿過桌上的酒瓶,又繼續往岑寂的酒杯里倒酒。
“岑寂,這杯是我敬你們兩個人的。”
岑寂淡淡的笑著,任由王芳把酒倒滿。
Advertisement
文昭這才回過神來,急忙攥住了岑寂的手臂,對著他搖頭:
“岑寂,沒必要。”
岑寂淺淡的琥珀眼眸低垂,他將子往文昭的邊傾,然后低聲在文昭的耳畔道:
“你今天不能喝。”
低啞的聲音里帶著幾分淡淡的酒氣。
文昭一頓,突然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仰頭著眼前的岑寂。
而岑寂只是把擋在后,他將一手背在后,的抓住了的手腕。
就像是永遠不想要松開一樣。
“你說婚禮之后我們不再聯系,現在婚禮進行中……”
“所以還能理我,對不對?”
他在文昭的耳邊說完這話,又是支起子,仰頭將王芳倒得酒飲盡。
眼尾顯出了淺薄的紅。
柳之敏看見這幕,微微一呆,咬牙關,隨即也倒滿了岑寂的酒杯:
“岑寂,這杯我專門敬你一個人的。”
“至于文媽的,我等和褚禮的婚禮再敬。”
岑寂來者不拒的飲下,他莞爾,眼眸霧蒙蒙的:
“今天我喝了,你們就饒過你們文媽吧,無論在誰的婚禮上。”
看著傳言中滴酒不沾的岑寂,今天是這樣好說話,酒桌上的氛圍一下子濃烈了起來。
兩位新人過來敬酒,別桌的人也過來敬酒。
岑寂始終攥著文昭的手。
人群攘,觥籌錯,文昭站在岑寂的后。
看著他襯衫在下潔白,背部的廓在襯衫下起伏,脊骨拔。
恍惚之間,像是回到了前世兩個人登記結婚的那天。
同樣是請了這些同學,喝了酒。
岑寂同樣是擋在自己的前,節骨分明的大掌背到后,的抓住了的手。
婚禮持續到夜幕降臨。
五班的同學紛紛加了文昭的微信,又是把拉進了群里。
他們天南海北的聊著自己的近況,約定要開一個同學會。
等夜深了,賓客陸陸續續的散場,文昭才突然聽見宋程宜有些疑的聲音:
“昭昭,岑寂去哪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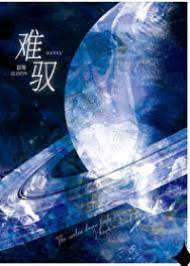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