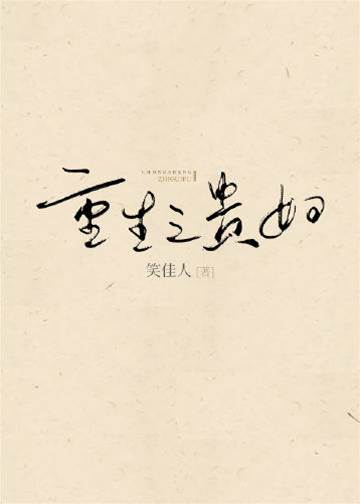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為奴三年后,整個侯府跪求我原諒》 第691章 穆尚雪的祈求
夜如墨,沉甸甸地在穆府的飛檐斗拱之上,仿佛要將一切生機吞噬。
庭院里,只有風聲在空寂的回廊間嗚咽,更添幾分死寂。
喬念獨自坐在搖曳的孤燈下,指尖無意識地挲著一枚冰涼的銀針。
那冰冷的卻無法平息紛的思緒。
蕭衡的蝕骨纏,被在靜思閣的穆夢雪、以及明日月圓之夜的地之行,都如同一團團麻,絞得心神不寧。
忽然,影七那沙啞低沉的聲音如同鬼魅般在角落響起:“谷主,院外有異。看形,應是穆尚雪。”
穆尚雪?
他來做什麼?
喬念眸驟然一凜,指尖的銀針瞬間攥,警惕與厭惡織的緒瞬間升騰。
這個前幾日還對親妹妹冷漠以對的人,深夜鬼祟至此,絕不會有什麼好事!
倏然起,推開房門。
清冷的月如寒霜般傾瀉而下,將庭院映照得一片慘白,骨的涼意撲面而來。
銳利的目如同鷹隼般掃過庭院的影角落,果然捕捉到一個試圖匿的模糊影。
那人影似乎也察覺到了冰冷審視的目,形猛地一僵,隨即竟帶著一種破釜沉舟般的決絕,從藏之走了出來。
月清晰地勾勒出那人的廓——果然是穆尚雪!
一冰冷的厭惡瞬間從喬念心底涌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想到前幾日為了被囚的穆夢雪去尋他時,他那副事不關己、甚至帶著不耐煩的冷漠臉,喬念連半分虛偽的客套都欠奉。
Advertisement
直脊背站在廊下影中,影被月拉得修長而孤絕,聲音帶著拒人千里的寒意:“穆大公子?深夜鬼祟至此,有何貴干?”每一個字都像是淬了冰。
穆尚雪的臉在慘白的月下更顯蒼白憔悴,仿佛被干了生氣。
他劇烈地翕了幾下,結滾,似乎有千言萬語堵在口,卻最終一個字也沒能吐出。下一刻,他雙膝一,“噗通”一聲,竟直地重重跪在了冰冷堅的青石板上!
膝蓋撞擊石板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
喬念瞳孔微,下意識地后退一步,低了聲音厲聲喝問:“你這是做什麼?!”
“喬姑娘!”穆尚雪的聲音帶著瀕死般的絕抖和濃重的哽咽,他深深低下頭,額頭幾乎要到冰冷的地面,姿態卑微到了塵埃里,“求你!求你去看看夢雪!救救!家主……家主他真的對了殺心!是真的要殺啊!”
喬姑娘……
穆尚雪對的稱呼,終于不再是那聲虛偽做作的‘念念’了。
喬念心中冷笑,“你之前不是還毫不在意,認為在靜思閣‘靜思’正好嗎?現在又是在演什麼兄妹深的戲碼?”語氣是毫不掩飾的譏諷。
穆尚雪的臉在月下難看到了極點,看向喬念的眼眸中甚至已經不控制地涌上了幾分潤的水,那是混雜著恐懼、悔恨和走投無路的痛苦,“我……我以為在靜思閣至是安全的!我……我沒想到家主他,他……”
Advertisement
他不是沒見過穆康盛的冷無,甚至自己的親生兒,也曾被穆康盛親手抱去了那地。
可他心底總存著一僥幸,以為夢雪是不一樣的!
夢雪并非懵懂無知的嬰兒,已經十六歲了!
在這穆家整整十六年,乖巧伶俐,喚了穆康盛十六年的叔公!
作為穆家這一輩唯一的兒,穆康盛平日里對夢雪的寵溺與偏袒,他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曾天真地以為,那點稀薄的脈親,至能讓夢雪在靜思閣安然無恙。
可今日穆康盛的那番話,徹底擊碎了他那點自欺欺人的幻想,讓他看清了家主為了所謂的“穆家利益”可以冷酷到何種地步!
思及此,穆尚雪猛地抬起頭,眼中是困般走投無路的瘋狂哀求。他抖著手,如同捧著救命稻草般,從懷中掏出一枚小巧卻異常沉重的黃銅鑰匙,不由分說地,塞進喬念冰涼的手心:“這是靜思閣的鑰匙!求你了!喬姑娘!現在只有你能救了!只有你了!”
他的聲音嘶啞破碎,帶著濃重的哭腔。
那鑰匙冰冷的如同燒紅的烙鐵,燙得喬念指尖猛地一,一寒意順著指尖直竄上心頭。
眉心低擰,審視著穆尚雪狼狽絕的臉,疑問道:“靜思閣外定有看守,我又不曾習武,如何能進得去?穆大公子,還是另請高明吧!”
Advertisement
是在試探。
果不其然,穆尚雪口劇烈起伏著,像是溺水的人在做最后的掙扎:“你雖進不去,可藏在你后的人……定能帶你進去!”他的目仿佛穿了喬念,看向后虛無的黑暗。
藏在后的人,指的便是影七。
喬念的心猛地一沉,面上卻不聲,同樣低了聲音,帶著冷冽的質詢:“你如何知道的?”
“當日你突然出現在棠京后,七叔公就被家主急傳去問話。得知我們穆家對你的向當真毫無察覺,半點消息都未曾傳回時,家主便已經猜測,你或許……已經了新一任的藥王谷谷主。”
穆尚雪語速極快,帶著一種揭的急切,“而那日花燈會上,穆家有人親眼見到一名手詭異的面人在保護你,所以家主就認定了,你如今就是藥王谷的谷主!”
原來如此……喬念心中一片冰涼。
穆家在棠京,果然是手眼通天,無孔不。
連自認為匿得極好的行蹤,都會為被懷疑和推斷的線索點。
眼見著喬念沉默不語,眼神變幻,穆尚雪心中的恐慌幾乎要將他撕裂,他急聲道:“喬姑娘!喬谷主!之前若有得罪的地方,都是我穆尚雪的錯!你恨我、怨我,便是現在要了我的命來抵償,我也絕無二話!只求你,看在我這點不值錢的悔意上,救救夢雪!……是無辜的啊!”
說罷,穆尚雪竟對著喬念,在冰冷的青石板上,重重磕下一個響頭。
猜你喜歡
-
完結208 章
重生之農家釀酒女
現代調酒師簡雙喪生火海又活了,成了悽苦農家女簡又又一枚. 一間破屋,家徒四壁,一窮二白,這不怕. 種田養殖一把抓,釀酒廚藝頂呱呱,自力更生賺銀兩 培養哥哥成狀元,威名赫赫震四方. 曾經的嫂嫂一哭二鬧三上吊,撒潑後悔要復和,陷害栽贓毀名聲,讓你仕途盡毀;霸氣新嫂嫂一叉腰——打. 酒莊酒樓遍天下,不知從哪個犄角旮旯裡冒出來的七大姑八大姨齊上陣,奇葩親戚數不清,老虎不發威,當她是軟柿子? 大燕丞相,陷害忠良,無惡不作,冷血無情,殺人如麻,人見人繞之,鬼見鬼繞道;只是這賴在她家白吃白喝無恥腹黑動不動就拿花她銀子威脅她的小氣男人,是怎麼個意思? ************** 某相風騷一撩頭髮,小眉一挑:"又又,該去京城發展發展了." 某女頭也不擡:"再議!" 再接再厲:"該認祖歸宗了." 某女剜他一眼:"跟你有半毛錢關係?" 某相面色一狠,抽出一疊銀票甩的嘩嘩響:"再囉嗦爺把你的家當都燒了." 某女一蹦三丈高:"靠,容璟之你個王八蛋,敢動我銀子我把你家祖墳都挖了." 某相一臉賤笑:"恩恩恩,歡迎來挖,我家祖墳在京城…"
66.4萬字8 73556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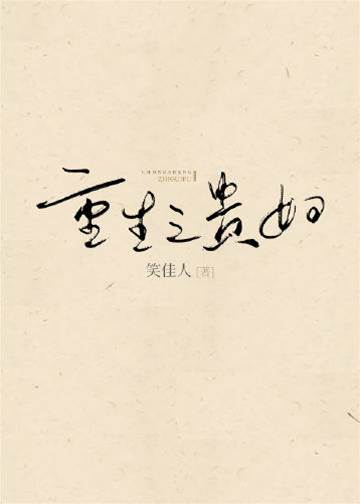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7269 -
完結59 章
念遙遙
白切黑和親公主X深情鐵血草原單于,遙遙”指“遙遠的故鄉”。“遙遙”也是女兒的小名,瑉君起這個名字也是寄托自己想要回家的念想。同時也算是一種宿命般的名字吧,女兒小名是遙遙,最后也嫁去了遙遠的西域,算是變相的“和親”月氏的大雪終于停了,我仿佛看見天山腳下湍湍溪流,茂盛的樹木與金燦燦的油菜花。我騎著馬去看我剛種下的小芽,一對鐵騎打攪了我的早晨,我沖到他們面前,指著最有氣勢的一個人破口大罵。他卻不惱,逆著陽光,將我籠罩在他的身影里,低下頭來,笑問道:“漢人?哪兒來的?”
9.2萬字8 11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