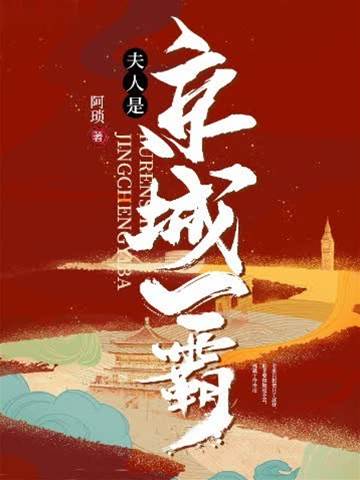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將軍嘴上說不熟》 第135頁
是日,禮部報呈的“嘉”謚號被朱批抹去,李琞懸腕良久,終于落下“昭懿”二字。他的七公主扶,是灼灼烈日,既這人世給不了圓滿,便讓帶著耀眼的華,去另一個世界吧。
公主府那場大火無人再提,七公主扶病逝,謚號昭懿。
大理寺中,司直馮會輕叩門扉,將文書呈于案頭:“嚴大人,將作監已開始修繕公主府了,那……封死的道,想來很快便會被發現并記錄上報。”
嚴瑢執筆未停,淡淡道:“昔日齊王府中的道快要通到海河去,今上登基也只加了道注腳。王公貴族府上有些機關暗道,實算不得稀奇,發現并上報,也是將作監的職責。”
馮會瞳孔微。他自然記得探查失火書房時,角落里的地磚有異,是新封死的道。大理寺的卷宗如實記了,只是嚴大人給陛下的節略中并未提及。
“下多了。”馮會躬退出,莫名想起昨日被嚴瑢燒掉的那封信箋,似有西北軍的漆封。
又幾日后,一條公主府鬧鬼的消息,開始私下在將作監流傳,乃至于天剛黑,便無人再敢做活。消息晦地傳宮中,太后在小佛堂下了懿旨:不用修繕了,擱置吧。
喧囂了數日的七公主府終得安寧,被火燒過的院墻已翻新,只是其中已不再有繁花滿枝。
-
南境通往衢州的道上,梅溯瞇眼向隊伍中那架鎏金鑲寶的華貴馬車,車里的貴人此番回京,極有可能重登儲位,梅安叮囑一路上不可怠慢他。
可這位大齊的前太子,卻比在文山時還要沉默。
自從出府啟程,李啠便安靜得出奇,倒是他那個護衛天祿格外事多,不是嚷著要茶要點心,便是嫌車馬顛簸。梅溯被煩得狠了,便咬牙低罵:“屁事恁多!不知道的,還當車里坐了個娘!”
Advertisement
一陣風掀起馬車窗簾,出半張冷肅側臉。道上的塵土撲進車廂,混著些霉氣,竟有些像天牢中味道。
車碾過碎石,顛得案上茶盞叮當響。李啠手扶穩,作依舊帶著東宮時養的儀態。他這雙手,批過賑災的折子,執過祭天的玉圭,最后卻在一紙謀逆罪狀上……按下了朱印。
他收回手,閉了眼。
袖中荷包忽地滾落,玉錦
緞已有些泛黃,但看得出做工細,只繡的那株并蓮已有些黯淡。
那是最后一次見袁月仙時奉給他的。彼時兩人都以為好事將近,笑著問:“這花樣,殿下可還喜歡?”
而今,蓮枯了,人沒了。
他忽而低笑出聲,多諷刺啊,那個自小養,連蝶翅都不忍的金枝玉葉,竟用蠱毒廢了李晟,嚴彧又借掀翻了賊船。這荷包,倒了唯一干凈的件。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如今連這點甜,都了穿腸毒藥。
車隊碾上一條荒廢的老鹽道,兩側是峭壁茂林,殘存的鹽晶在烈日下泛著慘白的,像一層未化的薄雪。馬蹄踏過,簌簌作響。
梅溯抬手遮住刺目的反,瞇眼向遠。風化的巖柱如鬼魅般矗立,投下詭異的影。他的戰馬不安地噴著鼻息,鐵蹄刨得鹽粒飛濺。
“哥,這地方邪!”梅信低嗓音,拇指已頂開刀鐔。
梅溯沒應聲,只緩緩抬起右手,整支隊伍如弓弦般驟然繃。
天祿不聲地勒馬橫移,將李啠的車駕護在里側。護衛們悄然收攏隊形,鋼刀出鞘。
“啊啊——”巖里忽地飛出只驚的禿鷲,凄厲的聲劃破天際,幾乎同時,“嗖嗖”的箭矢破空而來!
眾人提刀格擋,卻被突如其來地銅鏡反刺痛了雙眼,箭矢如雨,幾個衛兵悶哼著倒下,戰馬嘶鳴著揚起前蹄。
Advertisement
"嗖嗖"數聲,半空中炸開數十個麻布袋,鹽如雪般彌散,嗆得人睜不開眼。有些人被迷了眼,痛苦地哀嚎。
梅溯刀鋒劃出一道銀弧,將迎面而來的鹽袋鏢劈了兩半,尖銳的鹽晶劃破了他的臉。
“他娘的鹽梟把戲!”梅溯啐了一口,當年剿私鹽時這招他見多了,“梅信,巖柱上!”
梅信猿猴般躥上巖柱,弓弦響,懸掛的鹽包轟然墜落。煙塵中沖出二十多個揮舞鹽鋤的漢子,為首的漢子怒吼著沖上來:“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梅家軍已全部陷在與鹽梟的近戰中,卻將李啠及他的護衛安全地護在后。
李啠掀簾去看,瞧見襲擊者中有個藍衫年輕人,鐵鏈鹽鋤使得磕磕絆絆,想沖似還有些猶豫。
“留那個藍布衫活口。”他吩咐車外的天祿。
天祿死死盯著局勢變化。梅溯揮刀橫沖直撞,看似莽撞,實則每一步都打細算,長刀劈砍在巖柱上,震得碎石鹽粒四下翻飛,阻斷了側翼襲擊,看得他暗嘆不已。
一個滿臉鹽灰的襲擊者從側面撲來,梅溯看似來不及回防,卻在最后一刻側避過,反手一刀柄擊中對方后頸。那人綿綿地倒下時,梅溯已經抓住了他手的短刀。
“臺州西倉的貨。”梅溯掂了掂繳獲的短刀,刀柄上標痕雖已刮花仍可辨認。反手一揮,又一個襲擊者捂著嚨倒下,“夠利!”
戰斗很快呈現一邊倒的局面,這些鹽梟雖然兇狠,可畢竟不是正規軍的對手,在丟下十幾尸后,余下的人開始潰逃。
“別追了!”梅溯的令剛下,便見天祿飛而出,幾個騰轉,揪住了藍布衫的脖領!
“!”梅溯忍不住罵道,“此時倒顯著你了!”
Advertisement
“鎖了!”
天祿將藍布衫丟給手下護衛,轉看向著氣的梅溯,他臉上鹽和汗水混在一起,被他一抹,幾道白灰灰的痕跡涂了滿臉。
天祿剛要笑話他幾句,卻見他臂上袖被劃了道口子,已染黑料。
天祿從車尾拿出金瘡藥和裹簾,遞向梅溯:“要不要幫忙?”
梅溯似才發現臂上有傷,冷哼一聲道:“用不著!”
天祿輕笑一聲,走向藍布衫。俘虜的雙手已被反綁在后,面上全是恐懼。
李啠端坐車上,正在問話:“你什麼?”
年輕人閉不言。
梅溯上前一步,暴地扯開他的袖,出手腕——那里沒有任何標記。
“新伙的?”梅溯的氣勢要比李啠狠得多,藍布衫終于哆哆嗦嗦嗯了一聲。
梅溯把繳獲的匕首往他頸間一抵,只稍稍用力,便冒了珠。藍布衫眼里盛滿了恐懼,大氣也不敢,磕磕地開始求饒:“大、大人饒命!”
梅溯嗤笑一聲:“老子在臺州沒打怕你們?老巢都沒了,還敢來報復!”
藍布衫結結:“鹽道沒了營生,海上也沒了活路,當家的這才帶我們鋌而走險……”
“誰告訴你來這條道上劫老子的,說!”言罷刀尖又近幾分。
“這……小的不知,小的只是聽命行事!”
梅溯如鷹般的眸子視著他,刀下人已瑟瑟發抖。
梅溯看了眼李啠,之后一刀挑斷了藍布衫縛手的繩子,又往他口不輕不重地一踹:“回去告訴你們當家的,洗干凈了脖子,等老子辦完事回來,再去賞他一刀!滾吧!”
那藍布衫略一猶豫,爬起來跌跌撞撞跑遠了。
梅信清點人馬,一刻鐘后重新上路。夜幕降臨前,隊伍終于離開了老鹽道。
李啠回那條泛著詭異白的道路,鹽晶在暮中依然反著微弱的芒,像無數雙窺視的眼睛。
“不是單純的復仇……”他對車外的天祿低語。
天祿著眼前這個飽經滄桑的主子,沉聲道:“屬下接的是嚴將軍死令,只要我還活著,必不會讓殿下……讓您有生命危險!至于其它,將軍自會替您肅清,您可安心!”
第122章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遠峰巒疊嶂也朦朧起來,眼已現南境氣象。
夕過花窗,在梅爻上落下輕淺的影子。這是在大齊轄域的最后一晚,待明日破曉,南境的旌旗便會出現在道盡頭,闊別半年的兄長會接回家。
本該歡喜。
可越是臨近,心里某也被拉扯得越。一路上看著草木染上故土,愈發沉默。偶爾挑簾去,目總不自覺越過層層護衛和旌旗,落到那道玄甲背影上,仿佛只要那人仍在隊首執韁,心里空落的某才得片刻安寧。
自打梅煦的親衛加儀隊,嚴彧倒真“恪守”起了禮的本分。南境武士們將王的尊貴威儀,護得滴水不。
指尖輕輕過那枚小小的骨哨,最終將它抵在邊。
沒有哨聲響起,只有一抹溫熱的氣息拂過骨面,如同一個未敢宣之于口的吻,又似這半年來在心底、無傾吐的繾綣。
側燭影忽地一晃,還未來得及反應,一道暗影已籠罩而下。骨哨從指間落,卻被來人穩穩接住。
沒有冰冷的甲胄,嚴彧一素袍,襟間縈繞著悉的龍涎香。他修長的手指著那枚骨哨,目幽深地著,忽然將它緩緩推繃的抹中。微涼的骨質著下,激起一陣細微的戰栗。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yanqing/07_b/bjZKj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833 章

科舉逆襲:最強女首輔
程卿穿越了。開局死了爹,一個柔弱娘,三個美貌姐姐,而她是程家鼎立門戶的獨子……程卿低頭看自己微微發育的胸,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程家群狼環伺,換了芯子的程卿給自己定下兩個小目標:第一,繼續女扮男裝,努力科舉入仕。第二,保住自己的性別秘密,要位列人臣,也要壽終正寢!本文又名:《師兄看我眼神怪怪的》、《鹽商闊少要包我》、《將軍邀我抵足夜談》、《那個王爺總與我作對》、《陛下您有斷袖之癖?》
156.5萬字8 22136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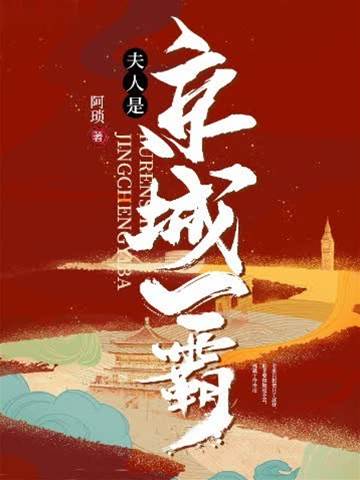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連載264 章

半妖農女有空間
千蓮本是仙界的一株千幻金蓮,因為誤入太上老君的煉丹爐,身死道消成為大秦朝的一個小村姑。 本以為以後只是個普通的村姑了,哪知道竟然隨身帶著一方小天地,這方天地中有一池靈泉,泉水中正是她上輩子的真身——千幻金蓮,而且,千蓮還發現自己依舊能吸收草木精華和天地靈氣。 買田買地買莊子,千蓮生活不要太愜意。 哪知道卻碰到個執著於捉妖的傢伙。 蕭北騁:你到底是人是妖? 千蓮暗忖:說她是人吧,可她能吸收天地靈氣、皓月流漿,可若說她是妖呢,她又沒有妖丹,幻化不了本體,難不成,她……是人妖?
44.6萬字8 17025 -
完結743 章

侯門醫女:我勸將軍要善良
被逼嫁給一個兇殘暴戾、離經叛道、罄竹難書的男人怎麼辦?顧希音表示:“弄死他,做寡婦。”徐令則嗬嗬冷笑:“你試試!”顧希音:“啊?怎麼是你!”此文又名(我的男人到底是誰)、(聽說夫人想殺我)以及(顧崽崽尋爹記)
127.2萬字8 52202 -
完結800 章

凰臨天下
九界之中,實力為尊。她是神尊境的絕世強者,卻不料在大婚之日,被所嫁之人和堂妹聯手背叛,淪落為下界被家族遺棄的傻子二小姐。涅槃重生,再臨巔峰的過程中,一朝和天賦卓絕,暗藏神秘身份的帝國太子相遇。“據說太子殿下脾氣不好,敢冒犯他的人下場都淒慘無比。”數次甩了太子巴掌的她,默默摸了摸鼻子。“據說太子殿下極度厭惡女人,周身連隻母蚊子都不允許靠近。”那這個從第一次見麵,就對她死纏爛打的人是誰?“據說太子殿下有嚴重的潔癖,衣袍上連一粒灰塵都不能出現。”她大戰過後,一身血汙,他卻毫不猶豫擁她入懷,吻上了她的唇。
136.1萬字8 266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