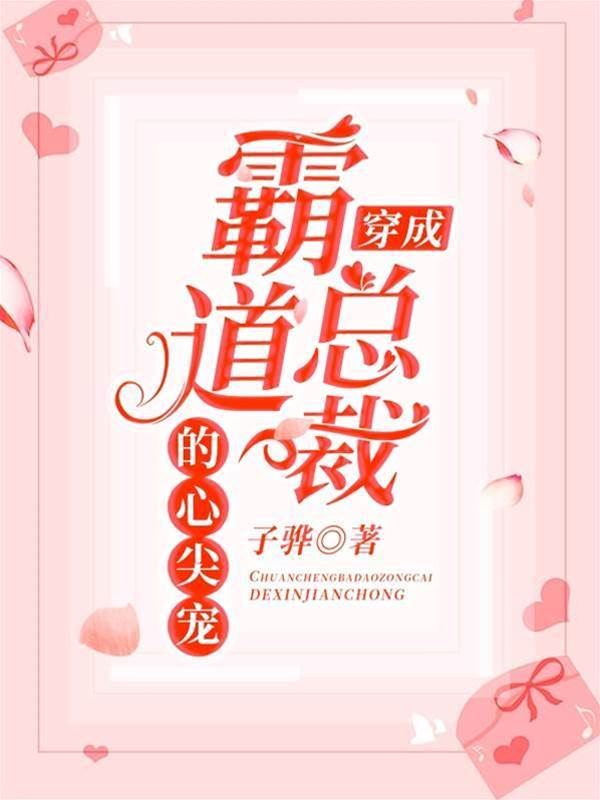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和離當晚我失憶了》 第21頁
道:“再過半個月是你們父親的生祭,再加上咱們府上又有添丁之喜,我想著到時去城外的寶華寺住上十天半個月,一來是為祈福,二來也好祈求咱們府上添子添福。大娘子可記住了?”
紓妍見特地點了自己的名字,下意識問:“我也要去?”
云縣主聞言,簡直要氣暈過去。
趙氏都已經懷了三個,子還未婚,除了這個嫡長媳,難道還有旁人不?
可紓妍并不想去。
自認為與裴珩已經和離,只待自己好了,即刻就要離開帝都,他想要添子添福,同有何關系。
正拒絕,裴珩已經開口,“如此也好。”
紓妍瞪時瞪大眼睛。
好什麼好,他怎就替自己答應了!
裴珩像是沒有察覺的視線,起向云縣主告退:“兒子還有事,就先回去。”
趙氏本想到他提都未提自己夫君升遷一事就就要走,有些急了,給裴瑄使了個眼。
裴瑄一臉為難地轉過臉去。
趙氏方才故意當著眾人的面宣布自己有孕一事,本就想著借懷孕一事夫君向這大伯哥討個更好的職位,卻沒想到他不肯,急得站起來,正開口,就聽大伯哥對著自己的兩個弟弟道:“去聽雨堂茶室等我。”
趙氏立刻轉憂為喜。
裴瑄垂頭喪氣地應了聲“是”。
裴鈺則一臉的生無可,正尋借口離開,只見大哥哥冷冷斜睨自己一眼,一,又坐了回去。
裴珩收回視線,看向自己的小妻子,神溫和:“回去罷。”
早就想走的紓妍立刻站起來,禮節地向云縣主請安告退,隨他出門去。
兩人剛出正院大門,紓妍迫不及待地問責:“我幾時說要去寺廟?”
Advertisement
他道:“我送你回去,邊走邊說。”
紓妍見外頭守著的有人,只好按捺下來,與他沿著來時的小徑朝著瀾院走去。
如今五月,到了晚上天氣不算太熱,迎面吹來的夜風里著晚香玉濃郁的花香。
這香氣令紓妍迷醉,沒有急著追問寺廟一事,問:“我一事實在不明,想請大人解。”
同樣難得閑適的裴珩答:“何事?”
極天真的聲音里著困,“二娘子是如何將娃娃揣到自己腹中的?”
裴珩停駐腳步,低頭對上一雙盛滿月的烏黑眼瞳。
第19章
裴珩與小妻子婚時,彼時正逢沈家舉家被流放后不久。
在帝都孤苦無依,邊只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婢。
裴珩著眼前一臉天真的小妻子,后知后覺地明白過來,也許從來無人教導過如何侍奉自己的夫君。
仿佛生來就是給他做妻子的,是以圓房的那天夜里,他將眼神里流出的局促不安與懵懂茫然當作。
事后,著下浸的雪白帕,哭得微腫的眼眸里流出不安:“人,我要死了嗎?”
他如何回應的?
他一時想不起來了。
彼時裴珩剛升任閣首輔不到兩年,朝堂之上有不人對他的位置虎視眈眈,稍不留神就會被人扯下來,家族中又要挑選培養優秀的子弟,用以鞏固裴氏一族在朝中的基地位,本分不出心思理會新婚妻子的想法。
后來的每一回,他都將這件事當作傳宗接代的任務。而從來都是曲意迎合,無半句抱怨。
那個夜晚,在想些什麼?
這些年又在想什麼?
一向不在這些小事上費心的男人一時失了神,直到又聽見小妻子問:“是因為拜子觀音的緣故嗎?”
Advertisement
裴珩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于是哄,“是這個緣故。”
又追問:“那我們婚這麼多年沒有,是因為我同大人沒有拜生子觀音的緣故?”
“大抵是我們每個月只拜兩回,次數有些,”裴珩結滾了一滾,“你想要小娃娃?”
“若是生得漂亮,有一個也無妨,我最怕悶了,”紓妍彎著眼睫笑,“待我以后了婚再去同我的新夫君拜送子觀音。”
裴珩蹙眉,“你要婚?”
“自然要婚,”紓妍反問:“難道大人不會婚?”
他不置可否:“你喜歡怎樣的郎君,我可幫你留意。”
紓妍聞言,由衷道:“我從前一直覺得大人虛偽至極,卻沒想到大人為人竟這樣好。不過大人倒也不必/我的心,我不喜歡帝都的郎君。”
說得坦誠,渾然沒有注意當到“虛偽至極”四個字時,旁的男人利眸微瞇,自顧自在那兒說著自己的擇婿標準,“最好能夠贅我家,我——”
“既如此何不趁此機會去寺廟住上一段日子,”
他打斷,“寶華寺是千年古剎,既然藥石一時無用,不如試上一試,興許早些恢復記憶。”
紓妍倒沒想到這茬,遲疑,“有用?”
裴珩正道:“心之所至,心誠則靈。”
紓妍一時猶豫不決,問道:“大人方才替我答應此事,可是怕云縣主因我不肯去寺廟而多生事端?”
他沉默片刻,道:“父親一直想要同你們家結親,你若去了,他在天之靈,一定會很高興。”
紓妍萬萬沒想到是這個緣故。
年紀還小,對于父輩們的并不了解,只知自己的父親倒是提起他來贊不絕口,原來他的父親也喜歡。
Advertisement
正猶豫要不要去,他又道:“到時你不愿意去,我自會尋個合適的理由,你不必擔心這些。”
“嗯”了一聲,“若是我實在閑得慌,盡量替大人走這一趟。”
萬一真有用也說不定。
此刻已經夜,月亮懸掛枝頭,隨著人的方位向前緩緩移。
紓妍一時起了玩心,追著月亮跳來跳去。
眼看著就要追到花叢里,他制止,“夜里黑,不許胡鬧。”
“我才沒有胡鬧!”揚起一張白的面頰,笑,“我在追月亮。難道大人年時不曾追過月亮?”
裴珩沒有作聲。
他總是如此,早已習以為常的紓妍也不指他能回答自己的話,一邊追逐著月,一邊豎著耳朵聆聽草叢里的靜。誰知他忽然道:“我年時,見過的月大多是在書案上。”
聽了,一臉可惜,“那大人還真是可憐,這樣的月豈可辜負。”
裴珩不以為意。
又聽驚喜道:“大人聽,這兒定是藏著一只壽星頭!”說著就要去草叢里捉,裴珩一把將拉回來。
“怎這樣頑皮,”一貫持重的男人頗為頭疼,“不許再往里鉆。”
撇撇,“這不許那不許,管得真寬。”
他道:“里頭有蛇。”
有些半信半疑。
跟在后的書墨適時跳出來,“那里真有蛇,前些日子還咬傷了一個修剪園林的花匠。”
紓妍這才作罷。
從正院到瀾院,約有一刻鐘的距離,一路上總問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比如,送子觀音為何不把小娃娃揣到男子腹中。
再比如,每個月要拜幾回送子觀音才會更快地揣上娃娃。
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傻話。
可裴珩非但不厭煩,反而前所未有覺得放松。
盡管他一路閑庭漫步,也很快便到了門口。
紓妍向他道謝,“多謝大人送我回來。”言罷要走,裴珩住。
他問:“為何不愿管家?”
紓妍愣了一下,隨即笑道:“這兒不是我的家。”說完,頭也不回地了院子。
直到院門關上,裴珩方收回視線,順著來時的路折返。行至方才追逐月的地方,一時停駐腳步,仰頭看向天。
書墨也隨著他看去,只見天上除了那圓月,沒有任何東西。
仰得脖子都累了,突然聽到一向最討厭旁人玩喪志的公子吩咐,“去把方才那只壽星頭捉來。”
書墨:“……”
這怎麼找?
*
裴珩回到聽雨堂時,兩個弟弟已經在茶室等了兩刻鐘之久。
他剛踏門檻,他二人忙站起來,畢恭畢敬地喚了一聲“大哥哥”。
他行到上首坐下,冷眼打量著自己的兩個弟弟。
裴瑄與裴玨見自家大哥哥面一臉嚴肅,張得直冒汗,低著頭大氣不敢出。
自從父親去世后,十一歲的大哥哥便肩負起父親的責任,這些年來為了這個家殫竭慮,兩人對他又敬又怕。
裴珩抿了一口茶,“今日的事是你的主意?”
裴瑄一聽便知是問自己,低下頭,“倩兒說得也沒錯,我想著若是要能往上升一升也是好的,只是我……”
他說到這兒,實在難堪,未再往下說。
若是別人有當縣主的母親,當首輔的大哥哥,指不定早就高升,唯獨這麼多年他都原地踏步,實在因自己無能的緣故。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yanqing/27_b/bjZmv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328 章

鬼王撩帳:人家好怕怕
意外身亡,魂穿異世,這都不算什麼。可是,偽善繼母,心機庶妹,剛一過來就遭遇毀容退婚,她招誰惹誰了?作為醫學世家的唯一傳人,竟然也會落入這步田地。說她囂張跋扈,那就跋扈給你看。你們都想做好人,那麼惡人就由她來當。繼母,死開!庶妹,滾邊!至於那傳說中喜好男風的鬼王……瑪德,到底是誰亂傳瞎話?這哪裡是喜好男風,興趣明顯是女好麼!某鬼王:“王妃錯了,本王的喜好無關男女,隻是喜好你……”
54萬字8 30742 -
完結81 章

天生撩人
梅幼舒生得嫵媚動人,在旁人眼中:心術不正+狐貍精+禍水+勾勾搭搭=不要碧蓮! 然而事實上,梅幼舒膽子極小,只想努力做個守禮清白的庶女,希望可以被嫡母分派一個好人家去過活一世。有一日君楚瑾(偷)看到她白嫩嫩的腳,最終認定了這位美豔動人的小姑娘果然如傳聞中那般品性不堪,並且冷臉上門將她納為了妾室。 梅幼舒驚恐狀(聲若蚊吟):「求求你……我不要你負責。」 君楚瑾內心os:欲迎還拒?果然是個高段位的小妖精。梅幼舒:QAQ 婚後每天都被夫君當做黑心x做作x惡毒白蓮花疼愛,梅幼舒表示:我TM是真的聖母白蓮花啊! 精短版本:小嬌花默默過著婚前被一群人欺負,婚後被一個人欺負日子,只是不知不覺那些曾經欺負過她的人,都漸漸地匍匐在她腳旁被迫要仰視著她,然而幾乎所有人都在心底等待著一句話的應驗—— 以色侍君王,色衰而愛弛! 瑟瑟發抖小兔嘰vs衣冠楚楚大惡狼 其他作品:無
25.8萬字8.25 26644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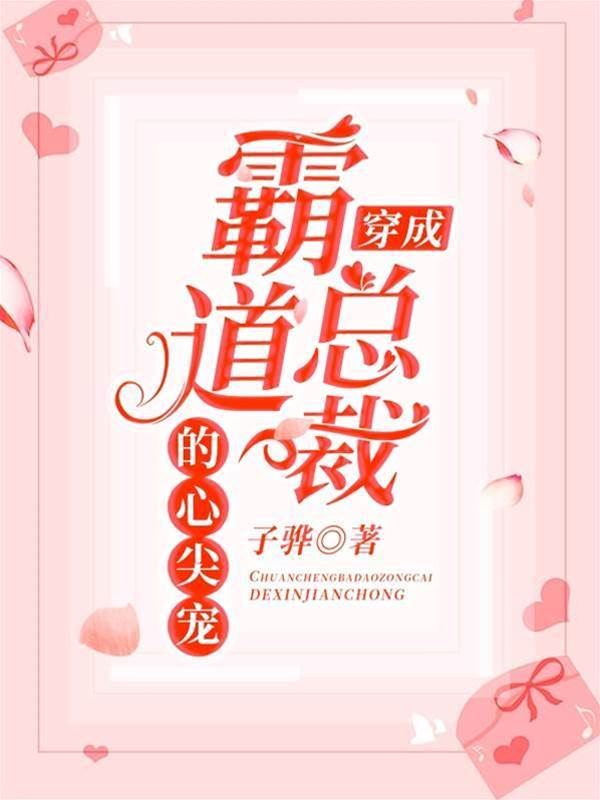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81 -
完結112 章

太子妃嬌寵日常
姑母是皇後,父親是當朝權臣,哥哥是手握重兵的大將軍,一副妥妥的炮灰標配,他們還一心想把自己送上太子的床! 一朝穿成胸大無腦的內定太子妃,柳吟隻覺得壓力很大。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太子殿下極其厭惡柳家嫡女,避如蛇蠍,直到一次宮宴,眾人卻看到如神袛般的太子殿下給那柳家嫡女提裙擺!!! —— 月黑風高夜,男人攬著嬌小的人兒眸光一暗,“你給孤下藥?” 柳吟一臉羞紅:“我不是!我沒
31.9萬字8 32371 -
完結218 章

愛你甘願為妃
一碗落胎藥,她看著他平靜飲下,卻不曾想,他親手殺死了他們的孩子,依然不肯放過她,他說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33萬字8.18 10132 -
完結191 章

新婚夜,瘋批太子奪我入宮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瘋狗男主】十六歲前,姜容音是嫡公主,受萬人敬仰,貴不可攀。十六歲后,姜容音是姜昀的掌中嬌雀,逃脫不了。世人稱贊太子殿下清風霽月,君子如珩
34.6萬字8 3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