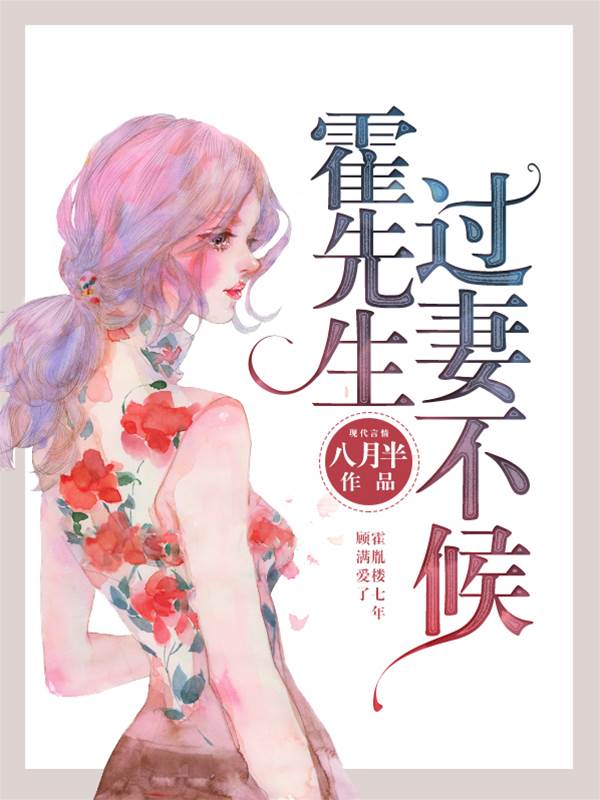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舊愛來襲:總裁的貼身愛人》 第179章 愛情的回光返照
其實,云起一直想去看一下葉沐,早在當初云開獄的時候,就想去了。只不過之前一直有葉父葉母在,還有葉初晴在,還有解不開的仇怨夾在他們兩家之間,并不方便面,也知道葉家的人都不喜歡,不想惹出無謂的事端來,便一直沒有來。
現在葉初晴都是泥菩薩過江了,自然,那種自私自利的格,也顧不上這個弟弟。
云起在葉之煦的安排下,很順利的見到了葉沐。
在經歷了這麼多事之后,大家都已經被折騰的很累很累了,看到葉沐那樣安靜的‘睡著’,云起忽然覺得很羨慕他。如果像他這樣什麼都不知道,靜靜的睡自己的覺,對于世間的一切紛紛擾擾都不聞不問,是不是也是一種幸福?
“關于他的病,醫生是怎麼說的?還有希醒來嗎?”沈時墨問道。
“這種病,怎麼能說得準?就看能不能創造奇跡了!”葉之煦看著躺在床上的弟弟,無奈的嘆口氣。
“你們兩個先出去一下吧,我想單獨和葉沐說說話!”云起說。
“那好吧!我在外面等你!”沈時墨先出去了。
隨后,葉之煦也出去了,并且給關上了門。
病房里一下子變得靜悄悄的。
云起拿出自己的手機來,“沐,我給你放首歌聽,好嗎?”
選擇了一首純鋼琴曲,是很輕很安靜的旋律。
的聲音也是輕輕的,“你應該不知道吧,這首曲子是我專門為你而作的。當初我為了復仇,投到音樂里,但是每當我投到音樂的領域去的時候,我又總是能忘記仇恨。有一次你大哥對我提起你,僅僅只有那一次,讓我想起來原來這所城市還有一個還在昏迷不醒的你,于是晚上,我作出了這首曲子。我不否認,我恨你的姐姐,恨到了骨子里。但是當我彈這首曲子的時候,我是真心的希你能夠醒過來。”
Advertisement
說著,時間仿佛回到了他們初識的那段時間,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很任,但是很的年——
“在那過去的幾年里,我時常想起我們的相遇相識。我時常想,如果當時我沒有進去你的病房,你沒有認識我,我也沒有招惹你,會不會發生后來一連串無法挽回的事?”
“一切禍好像都是因你而起,但又好像不是,我不知道誰能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你在手前吃東西,云開獄,我不得不介時墨和你姐姐的婚姻。而你姐姐,為了讓我和時墨永遠不能在一起,害死了我的媽媽,我的兒,我的外公。在我對生活對生命都徹底絕的時候,你大哥帶我離開了這個城市,想盡辦法使我振作,想盡辦法讓我活下去……你說,這樣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到底是不是前世命定的孽緣?”
“有時候我多想像你這樣睡過去,一睡不醒,這樣我就不必活得這麼累,這麼痛苦。可是葉沐,這樣一直睡著,你不累嗎?明天你就要回到你的父母邊去了,如果你一直醒不過來,大概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再相見了。如果你想見我,你就努力一下,早點醒過來,好嗎?”
“……”
很長很長的時間過去,房間里只能聽到的聲音,還有音樂流的聲音。
一直在陪他說話,說到嗓子都啞了,他還是那樣安安靜靜的睡著。甚至,連他的呼吸聲,都聽不到。
最后走出病房時,天已經黑了。
和沈時墨告別了葉之煦,坐上了車。
沈時墨沒有立即開車,只是用一種沉默的目久久凝視。
“你怎麼了?”不解的問。
“我在想你說的那句話。”
“哪句話?”更奇怪了。
Advertisement
“那句對葉沐說的,那首曲子是專門為他而作的。”
“你聽我講話?”
“我哪有聽?那家醫院里的隔音設備不好,我是堂堂正正的聽!”
他說的理直氣壯的。
忽然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笑了出來,“好吧,就算你堂堂正正的聽好了,有問題嗎?在我流浪的那兩年里,我常常想起我的家人,很想很想他們的時候,我就會為作一首曲子。像云開,阿梓,桑榆,阿揚,我都為他們作了曲子。”
“連阿揚都有?”他咬牙低問。
“阿揚他不止一次的救過我啊!”
不嗔不怒,輕輕的一句話就把他的氣勢了下去。
的確,除了那個罪魁禍首小爺以外,每一個人都為做了很多事,比這個自認為最的男人做的都多,他有什麼資格要求呢?
這一刻,他說不上來心里什麼滋味,低低的問了一句:“你是不是,這輩子都不會為我彈琴了?”
“我的演奏會有很多啊,我可以送你前排的場券。”
“你明知道——”
“嗯?”
他沒有說下去。
輕描淡寫的語氣,畔始終帶著一抹淡淡的微笑,是很溫,卻有一種別人看不到的哀傷。
他知道,不是聽不懂他的話,他只是,越來越無法猜到底在想什麼?自從回來以后,對他充滿恨意,句句帶刺,他多希能好好跟他說句話,現在,他終于如愿以償了,卻是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了心里,只用笑容來面對他,他每時每刻都在擔心,是不是隨時會離開他?
在一些人將死之時,常常會出現一種回返照,他們現在之間這種難得的平靜和溫,會不會是他們的回返照?
他咬了牙齒,什麼也沒再說,猛地發車子像箭一般沖了出去。
Advertisement
下意識的抓住了扶手,卻沒有害怕,更沒有大喊大。
他開車的速度也很好,雖然夠快,卻也很穩,不至于會磕到到。
也一語不發,眼睛始終著窗外深沉的暮。
狹小的空間里,這種令人不安的安靜,令他不由自主的放慢了速度。
直到車子駛進一段沒有路燈照耀的漆黑路程,他突然把車子停了下來。
不解的看看他:“怎麼了?”
“前面在修路,我們還是繞路走吧!”他說。
“你怎麼知道?”
“前段時間,我常常來這里。”
又是一陣沉默。
他正準備調轉車頭,卻說話了:“在這里停一停吧!”
這里離云歸山不遠,蒼茫的暮中,幾乎可以看到那蜿蜒的山路。
然而,的肚子很不爭氣,還是早上吃了點東西,中午到現在一直都沒什麼胃口,現在終于了出來。
他也聽到了,嘆了口氣:“你了,我們走吧!”
“我可以不可以吃一個漢堡,加一杯可樂?”的要求很低。
“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里吃?”
“這里?”他看看附近,別說麥當勞,連燈都很看到。
“對!”點點頭,指著旁邊的一條路,“過去這條路,有一排比較破舊的房子,再過去那排房子,有一條寬敞的馬路,那邊有一家麥當勞,我想吃漢堡。”
原來,經常來這邊的不止他一個。
“好,那我們過去吧!”說著,就要發車子。
“有一段路過不去車。”
的語氣淡然,沒什麼緒。
他默默地看著,凝視許久。
誤解了他的意思,微微笑道:“為難你了是不是?其實也沒那麼,我們走吧,簡潔這時候應該做好披薩了,的手藝很好。”
他卻聽得心里更難,什麼為難他了?如果這點小事就能為難他,那他要不就是一個沒用的男人,要不就是一個不在乎的男人。
不論之前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他都不計較了,只點點頭:“那你在車里等我,這里不安全,我下車之后上鎖,不管看見什麼人什麼事,都不要下車。”
他去給買漢堡。
沒有看見,他下車以后,久久凝視著他的背影,眼中多了一抹意。其實,不是在故意為難他,只是想起很多年前,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常常跑好幾條街去給買喜歡吃的漢堡和薯條,想重溫一下那種覺,那種即使自己不斷無理耍賴,還會被人呵護的覺。
真的,那種覺,已經很久很久不曾屬于了!
窗外不時的走過一些三四十歲的男人,奇怪的朝車子里看來,看到只有一個人的時候,眼變得有些不懷好意。
不過門窗都被沈時墨鎖好了,也沒什麼好怕的,而且知道,沈時墨很快就會回來。
果然,不到半個小時,就看到了沈時墨的影。
他提著麥當勞的專用環保袋向這邊走來。
車旁那些奇怪的人也都走了。
他打開車門進去,一邊把東西給,一邊問:“沒有害怕吧?”
“有什麼好怕的?”
之前也常常一個人過來,也常常到一些對不懷好意的人,的確沒有什麼好怕的,生死,早都置之度外了。
打開沈時墨帶回來的袋子,里面有漢堡,有可樂,有薯條;所有吃的,都應有盡有。
拿出一個漢堡來給他,“給你吃!”
以前在認識以前,他從來不吃這些,這東西在他眼里都是垃圾食品,但是看到吃的那麼香,那麼開心,這些垃圾食品好像都變了味佳肴。
“怎麼樣?好吃吧?”一邊吃著,一邊笑著問他。
猜你喜歡
-
完結361 章

萌寶三隻:爹地請排隊
20歲,陸傾心被算計生子,虐心。25歲,陸傾心攜子歸來,讓別人虐心! *三隻萌寶*天佑:「我是藍孩子,完全可以勝任『爹地』一職。」天煜:「我……我喜歡醫生哥哥做爹地!」天瑜:「人家要桃花眼蜀黍做爹地……嚶嚶嚶……」正牌爹地喬BOSS,不是醫生,木有桃花眼,心塞咆哮:「三隻小崽子,你們放學別走,我們聊聊人生!」陸傾心:「大丫、二狗、三胖,回家吃飯!」三寶異口同聲:「媽咪,請務必喚我們大名!」
87.6萬字7.5 19819 -
完結479 章

夫人,總裁他罪不至死
「林小姐,你可曾愛過人?」「自然愛過。」「如何愛的?」「剛開始,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愛他。」「後來呢?」「後來啊,我恨不得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去死。」認識林羨的人都知道,她曾在感情裏栽過一個大跟頭,爬起來的樣子很狼狽,當時她一個人在原地站了很久,不敢往前,也不敢往後。因為,不管往前走,還是往後退,都是粉身碎骨,要命的疼……
101.2萬字8 15151 -
完結305 章

撒旦總裁追逃妻
五年前,她為養母委身于他。沒有完成契約便不辭而別,杳無音訊,順便帶走了他的一對雙胞胎。 五年後,她帶著愛與哀愁歸來,躲躲藏藏,與他形同陌路。一場意外的醉酒,讓他識得廬山真面目。 翻開舊時契約,他要求她繼續未完的義務。 她瀕死掙扎,所有的牽掛,不過是給他為所欲為的借口…… “爸爸!” “爸爸!” 兩張天使般的面孔出現在眼前,他愣了又愣,沒敢相認。 不能讓他搶走自己的雙胞胎兒女,她努力雪藏,抵死不認。 “一周才四天……太少了,不行!” “不少了呀!”方心佩掰著手指頭替他計算,“你想想看,一周總共才七天,扣掉了四天的時間,你只剩下三天給別人,恐怕還要因為分配不均,讓人家打破頭呢!” 看著她那副“賢惠”的模樣,程敬軒差點被氣得吐血。這是什麼話?自己的這個情人也算是極品,居然還替他考慮得這麼周到?
41.3萬字8.09 112976 -
完結374 章

太子殿下恕不約
一朝穿越,作為主任法醫師的她成了那個軟弱無知的小村姑人盡可欺?葉琳表示不慌,她最擅長以牙還牙,隨隨便便就能教那些個不長眼的做人。等她這鄉村生活越過越滋潤,突然有人告訴她,她是當朝相爺的女兒?好的,這座大山不靠白不靠,她就是認了這便宜爹又如何。回到京城,葉琳早已做好與各路神仙鬥爭的準備,卻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惹上了那個最不能惹的太子殿下。等等,這位殿下,您有點眼熟啊。
68.9萬字8 6939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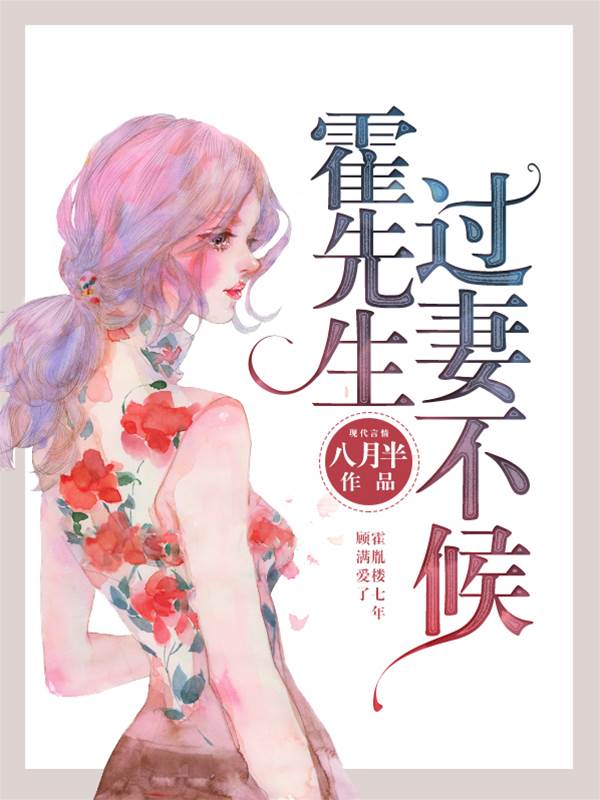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