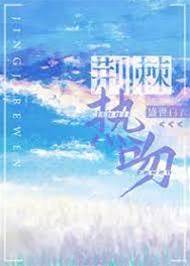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頂級新婚》 她曾俯首稱臣的國王 已向她……
曾俯首稱臣的國王 已向……
留學期間, 賀徵朝經常三天兩頭就去探,即使不常住,至多待三天, 對溫知禾而言,也跟在國鄉下拍電影那會兒無異。
23歲這年大概是人生高時刻, 寫的博文被出版社看中, 合作出了本書,被博客節目邀請做嘉賓,被曾經的影迷認出, 與幾個孩獨立制作的畫短片也圍了國際相當有含金量的獎項。
在這之前,溫知禾從未想過自己會出書、做博客、制作畫,分明在十六歲那年, 還是一個無法選擇自己喜的專業, 買不起相機的孩。
某場博客提及年,溫知禾做著回憶錄,幾乎要忘記過去的模樣。坦言說那時膽小不說話沒朋友,主持人還打趣看不太出來。
下了播,溫知禾就在公寓門口收到賀徵朝送來的玫瑰。他來或不來,總會送花, 樓底下的花店都是為而開, 毫不誇張。
24歲過了大半, 溫知禾結束學業回國了。即便國充斥著迫的年齡焦慮, 所的人生時段, 也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
溫知禾刻意瞞回程,策劃了一場驚喜,結果剛登上機艙,就在寥寥無人的座位上看見他。
“你怎麽……”溫知禾一時無言, 走到他跟前輕輕揪了下領帶,故作氣鼓鼓地倒打一耙:“下圈套讓我上你的賊船啊,我還想主回去找你給你一個驚喜。”
賀徵朝低頭輕哂,那雙深邃的眼總是多到讓人面熱:“我和你道歉,不該向你瞞。”
他說是這麽說,四下無人時,已經以掌覆上的,或或給予扇打的痛。
這裏不是他們的公務機,沒法做得太過分,還有攝像頭高高掛壁。他親吻著的,點到為止地環抱,平靜又沉著地了餐,溫知禾卻有種決堤而淹漫的。
Advertisement
乘務員離開,溫知禾出于報複,深深地抓準了他命脈,只是將它催化便不采擷,哼著曲去洗手間淨手。
推門剛要出來,一堵牆便巋然擋去去路。
男人的目極深:“膽子大了不。”
不是沒有在仄的隔間做過壞事,只要關上門,捂住,這個男人可以放到不知恥。
溫知禾沒因為撥的後果吃虧,所以懂得適當地低頭,溫溫吞吞說:“……我以為你會喜歡。”
簡直是得了便宜還賣乖。賀徵朝哼笑一聲,并未多說什麽,從領口取了方巾,替仔細拭每一只手指。
他做這事向來順手,慢條斯理,像保養珍貴的玉:“到家了再教訓你。”
溫知禾嗖地回手,哦了聲。
不等到家,下飛機到車上,的雙手已被牢牢拷住無法彈。半個鐘頭的車程本完不了,是親吻,他們就沒完沒了。
抵達家門口,司機停擺好車,面地留給二位私人空間,賀徵朝驀然捋起的擺親吻那裏,隨後嵌合得正正好,讓搖晃得只覺天翻地覆。
三十歲的男人惹不起,尤其是快奔四的男人……溫知禾大腦缺氧,雙張合著,已經察覺不到自己在說什麽話。
不知,正漩渦中心的淩。賀徵朝送去沉重的沖擊,在耳畔悶悶輕哂:“四舍五你倒是會舍。”
溫知禾倒吸口氣,看到那方泛白的綿,近乎要暈厥。歹從心起,反正都已經被教訓,說些嗆人的話又怎樣:“那你也會舍,這麽快就舍出來了。”
說時是以半跪的,居高臨下的姿態睥睨,只是嚨蒸著燙人的熱,聲線氣若游,沒什麽底氣。
賀徵朝能看見邊漣漪的紅,那是他烙印的痕跡。他手去剜,一寸寸,一次次,又按住的脖頸加深這個烙印,迫使低頭去看那裏,嗓音溫中著涼薄:“你自己看看,這是你的還是我的?”
Advertisement
誰能分得清。溫知禾惱怒,話還沒說出口,又迎來一次沖擊,直中靈魂要害,那麽酸麻,的頭皮爬滿啃食的螞蟻,渾也是匝匝的酡紅。
幾下來已是天黑,溫知禾被他由車上抱到起居室,知得不得不舉起白旗認命投降。
他倒也仁慈,不,是懂得適度。看已經紅得不像話,做了善後就沒再多要。
太過疲憊的後果是睡個爽,溫知禾悶頭沉寂了十個小時,醒來的時候還迷迷瞪瞪,以為自己沒回國,下意識按線想傭人。
傭人是沒來,來了昨晚的閻羅王。
溫知禾對自己歸國的象化了,也不是很想起,索繼續睡。
賀徵朝只能面無表地倒掉自己做好的飯,投工作中。批閱完傳來的文件,他沒有拿桌上任何一本書,而是從某博客APP裏,點開了采訪溫知禾的那幾期。
最新一期是上個月錄制的,上中下籠統三期,他翻來覆去聽了遍,無需看shownotes,都知第幾分鐘第幾秒會到下一條問答。
不是沒有見過面、打過視頻,越過屏幕做更親的事,但一個人總會不由自主去探尋那些細枝末節的角落,書上有關的筆記,會不惜損害去撕扯下來收藏,偶然在街角幻聽的名字,會下意識扭頭看去。
學生時代沒做過的蠢事,他在一個人上做了千遍萬遍,分明他已是上了年紀。
不過,聽聽博客也并非沒有新發現。溫知禾生父曾奇妙地在賀家做過專車司機——他們有過相當近的距離。
博客在持續播放,賀徵朝闔眼傾聽,聽講述憾的年宮,聽戲謔自制的麥芽糖發自己過敏,聽學生時代傾慕過的男同學……聽了不知幾遍,依舊有著十足的新鮮。
Advertisement
因為太過專注,沒發覺書房的門被悄然推開,直到播放鍵被人暫停,溫香玉懷,賀徵朝才睜開眼。
真兜不住上的熱和香,但并非無意撥,是純粹習慣坐在他膝上。
“大老遠我就聽見你放這個……你是老年人呀,放這麽大聲。”溫知禾搖著嘟囔,其實是胡謅,隨口打趣的。
賀徵朝托著的,大言不慚:“你不在的時候習慣了,這間房總要有你的聲音。”
突然的糖炮彈,零幀起手。溫知禾一噎,本就口幹舌燥,現在臉都燙起來了。
歸國第一周,溫知禾不了應酬一些人世故。
的工作室掛在恒川那裏一直沒變,人員走走散散,核心的幾位仍還在,何況畫短片曾經過悉的好友指導過,謝宴必須排在首位;其次是親友間的寒暄,幾場家宴……
溫知禾忙得像陀螺,頭回發覺自己的圈子竟如此龐大,原先是打算回來推進新項目,好讓自己沒那麽閑,事實證明的確閑不住。
相比起,特意推了商務應酬、將工作式地做完的賀徵朝就顯得格外像個空巢老人。
那次撞見他翻來覆去聽博客,溫知禾就約覺到。笑不太出來,也不會那麽稚,尤其得知他在回國前做過一次手——這還是賀寶嘉無意間的。
溫知禾想氣又氣不過,眼淚率先掉出來,問他是不是車禍後癥,那些檢報告不會是他糊弄人的吧。
“不是,沒有,你別想太多。”賀徵朝攏著的臂膀,溫聲解釋。
溫知禾抹了抹淚,緒低悶:“你這話說得像渣男。”
“什麽?”他顯然不在一個頻道上。
溫知禾輕哼,重複:“渣男,騙子。”
賀徵朝笑了下,沒有辯解這莫須有的罪名,很配合地擔下,卻又沒說要原諒,而是順著的臂彎下抱住,低聲嘆:“我很高興。”
溫知禾知道他在高興什麽,這個男人總是油鹽不進。皺了皺鼻子,煩悶地拍了下他:“我哭了你就高興?”
“分況。”
“什麽意思?”
他還未答,又言:“你也沒哭。”
“……”
沉默須臾,溫知禾攥了攥拳頭:“你真是……”
賀徵朝接了的拳頭,垂首看,是商量的口吻:“給我一段假期,陪陪我。”
拳頭化作張開的五指相扣,溫知禾像在一只龐大的、的、又依賴極重的、屬于的.犬,的心因為這段話,那雙始終溫和沉靜的眼塌得不像話。
曾俯首稱臣的國王,已向低下頭,送奉往後餘生的權杖與皇冠。
溫知禾抿了抿,忽地想起:“那,那我們再去旅游吧?之前說過的……也算我第二次的畢業旅游?”
賀徵朝略略思忖,應了聲:“你的筆記本還在屜裏,第二格。”
溫知禾去找,果然在他所說的地方找到曾經的筆記。這裏不止只有筆記本,還包括的報道、采訪,被人為打印剪裁出來的,麻麻全都是,堪稱潘多拉魔盒,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放在最上面的,一張被拼接的合照。右下角有標注。
是十歲的與十二歲的他。
他們人生最關鍵的轉折點,那縱橫在他們之間,沒有集的天塹,被他稚地用膠棒粘在一起。
如此深刻而牢固。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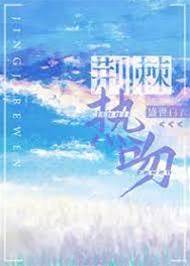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522 章

沫沫生情霍少寵妻如命
沐家見不得人的私生女,嫁給了霍家不能人道的殘廢二少爺。一時之間,滿世界都在看他們的笑話!然而,夜深人靜之時,某女扶著自己快要斷掉的腰,咬牙切齒!“霍錦廷,你不能人道的鬼話,到底是特麼誰傳出去的?!”————————整個桐城無人不曉,雲沫是霍錦廷的心頭寶。然而許久以後雲沫才知道,一切的柔情蜜意,都不過是一場陰謀和算計!
56萬字8 50687 -
完結102 章

是禍躲不過
林荍從小在霍家長大,為了在霍家生存下去,只能討好和她年紀相差不大霍家二少爺。 霍圾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做什麼都是第一,斯斯文文從不打架,不發脾氣,不抽煙,不喝酒,沒有任何不良嗜好,溫柔體貼,沒有缺點…… 可只有林荍知道她討好的是一條溫柔毒蛇。 林荍:“你到底想怎麼樣?” 霍圾摘下眼鏡,斯文輕笑,“姐姐不愛我,為什麼對我笑?” 一句話簡介:腹黑年下的占有欲
29.7萬字8 39025 -
完結452 章

偷生豪門繼承人,被大佬溫柔誘哄
【萌寶 馬甲 雙重身份】那一夜,她走投無路,闖入司家植物人房間,把人吃幹抹淨逃之夭夭。五年後,她攜寶歸來,第一時間就是和孩他爹的雙胞胎弟弟劃清界限,不想他卻丟過來一份醫學報告,“談談吧。”“談什麼?”男人將她堵在牆角,“撫養權,戀愛,你自己選。”這還不算完,她的四個小祖宗一下子給自己找出來兩個爹!沈歌謠蒙了,她睡得到底是誰?男人直接把她按住:“既然不記得了,我幫你好好回憶回憶!”
50.2萬字8 37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