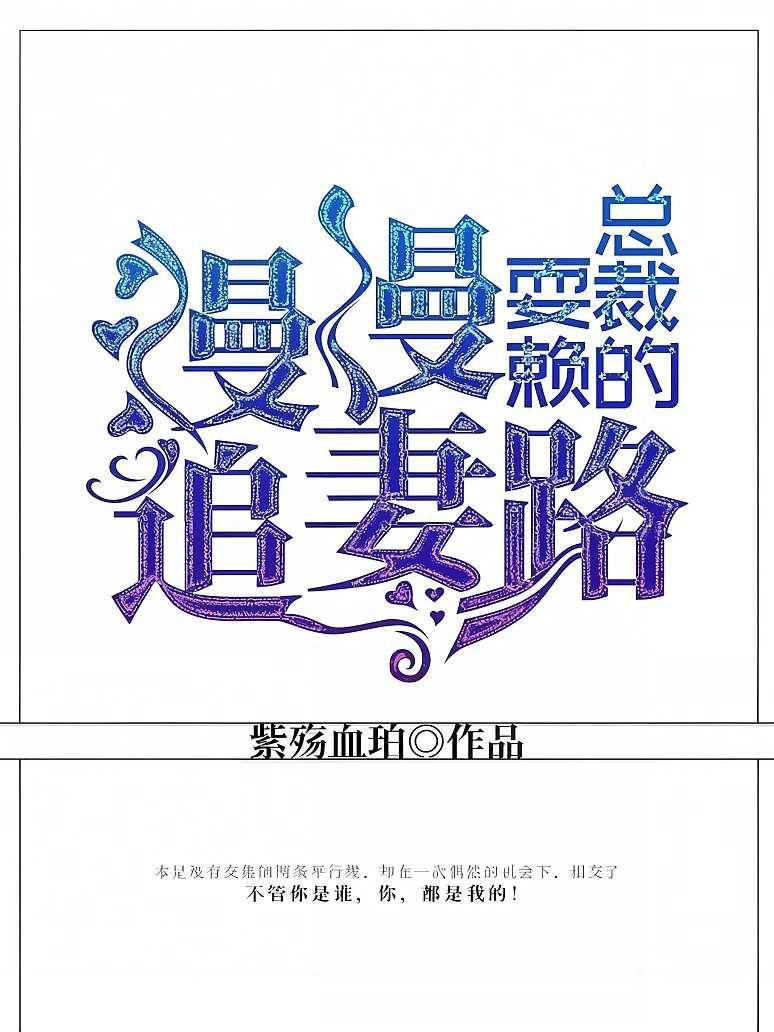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誤招惹總裁上司后,她懷上三胞胎!》 第124章 愛上了“獵物”
這般曖昧的姿勢說出這般威脅人的話…
很容易讓人想歪。
阮了干涸的,“我…我。”
他頓住,驀地發笑,“跟你有什麼關系?”
小聲,“我這麼知道傅先生說的懲罰,不是上的懲罰。”
傅廷洲盯著面紅耳赤的臉,笑出聲,腔在掌心震,“你不說,我還真沒想起來,是有段時間沒你了。”
“不行…”一,傅廷洲埋頸側,又細又的短發扎得的,他炙熱的鼻沿著頸部脈絡往下。
阮癱在他懷里,大口氣,偏偏覺來得比以往還要強烈。
窺到的模樣,傅廷洲將纏在自己腰上,“一段時間沒小阮,真是越發敏了。”
別過臉,手背抵在眉眼,不看他,“…這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他一寸寸吻,“那說明小阮也著我。”
“門沒關。”
阮耳朵紅到不行。
他忍耐到極點,聲音沙啞,“不會有人進來。”
傅廷洲在書房纏了好久,全程放任自己,像被他點燃了心底暗不想直面的。
人一旦打破忌,初嘗果的滋味,那便只能放任無法主張的,在世俗眼里,是罪惡起源,所不能直面的是真實的自己,甚至已經被他俘虜的。
Advertisement
倘若沒有,就只是本能,可破了忌,清楚地知道自己除了本能,心早已經接并且上了原本的“獵”。
或許趙海棠說得沒錯,沒有經驗的人,很容易折在一個場浪子的手里。
關鍵他不是一般的場浪子。
他的偏心,太讓人沉溺。
過了不知道多久,阮衫不整躺在傅廷洲懷里,他上的汗水浸,讓跟他一般狼狽。
傅廷洲手指穿過濃的發間,攏向后,一不,閉上眼。
他低聲笑,“投資找到了嗎?”
聲音沙啞,“你要投資啊?”
“當初不是你說的嗎?”
阮撐起,看他,“我那時候開玩笑的。”
他淡淡嗯,“我不都當真了。”
“隨便你好了。”坐起,將服拉攏好。
說隨便他,顯然也并非拒絕的意思。
傅廷洲笑而不語。
…
一段時間后,傅家沒再派人找過,公司裝修進展也已經到了收尾,現在就只差公司名字了。
阮原本想的TY,但團伙也不止一個人,索就改“TEAM”,也恰好是團隊工作室。
裴敬將帶到屬于的辦公室,“阮小姐,您看,這辦公室您滿意嗎?”
辦公室線非常充足,很是敞亮,關鍵景致也好,能俯瞰半個商業區中心。
阮走到窗前,“這辦公室確實不錯,很合我意。”
Advertisement
“您喜歡就好。”
“哦對了,以后不用我阮小姐,咱們都是自己人了,就無須太客氣了。”
裴敬憨厚地笑了起來,“那我們以后喊你姐,可以嗎?”
也笑,“行吧。”
一周后,TEAM工作室正式立,工作人員將手的新設備都搬了進來,陸辛琪這會兒咋咋呼呼地從外頭進來,“咱們竟然收到了花籃誒,一排的花籃!全都是三角大廈部其他公司在慶祝我們工作室的立!”
阮隨著裴敬他們來到走廊,外頭幾乎擺滿了一排花籃,紅條上都寫有某某公司慶賀開業之類。
裴敬也匪夷所思,“咱們來了這麼久,似乎也沒跟樓下其他公司有打過照面吧?”
阮約猜想到是誰的手筆了,這不,數名保鏢推著南宸走出電梯,南宸看了看邊上一排的花籃,淡笑,“新公司立,倒有不收獲呢。”
阮上前迎接他,“這得是南先生的功勞吧?若非他們知道南先生照顧我的公司,怕也是無人問津。”
公司部的企業,哪個不是給南宸面子的?南家家大業大,連三角大樓都只是南家在商業區的一棟寫字樓,能被南宸這般照顧的新公司,于他們而言主示好并不虧。
南宸抬頭看,“我只是照拂了下你的新公司,可沒有用這層關系。”
Advertisement
阮輕笑,主推他進工作室,“別人都認為我的靠山是南先生,這下真洗不清了。”
他眉眼流濃深笑意,“在京城有靠山是常見之事,混商界,獨一人寸步難行,何況還是人,既然他們都認為我是你靠山,那就讓他們認為吧,在你公司能在京城穩扎腳跟之前的確需要一個照拂。”
他所說的話并不無道理,沒有背景的男人在職場打拼都履步維艱,更別說一個沒有背景的人,何況是于權利中心的京城。
想要往上爬,靠野心也不夠,很多事業型靠實力能爬到的位置頂多是管理層,可終究還是老板下屬,照樣是給人打工。
不愿屈于人,自己開公司,實力跟財力居后,人脈背景才是優先。
而也知道,的一帆風順多半都是南宸給“護航”,比起把別人當跳板卻又對外聲稱自己靠實力的人,更不介意別人認為靠南宸。
就在這時,林一帶著保鏢出現,保鏢手里的花籃比其他公司花籃都要大一倍,還需要兩人扛,紅條標注:傅氏總裁傅廷洲賀上。
阮咋舌,怎麼莫名聞到了一場“較勁”的味道?
林一走來,站在他們面前,微微頷首,“阮小姐,南。”
南宸看著他,“傅總怎麼沒親自過來?”
他回答,“傅總在樓下,他說不方便打擾。”
阮眉頭皺了下,傅廷洲說不方便打擾是什麼意思?他會不方便打擾?還會覺得臉皮薄?
這狗男人又在搞什麼名堂?
南宸看出臉上的糾結,緩緩啟齒,“你想去就去吧,這里有其他人照顧,不用擔心。”
阮到抱歉的,畢竟他才是自己的“大金主”,拋下“金主”照顧不周還去找別人,怎麼都是不禮貌的行為。
而南宸偏偏沒介意。
但南宸對越好,就覺得欠他的越多,唯一的補償也只能在今后的利潤上了。
阮來到樓下,那輛狂拽炫酷的越野就泊在正大門的噴泉池前,后車窗緩緩降下,那張俊妖孽的面孔在影里越發清晰。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白蓮花她不干了
1、 紀棠被北城宋家選中,嫁給了繼承人宋嶼墨,成為人人羨慕的豪門貴婦。 作為作為位居名媛榜之首的紀棠時刻保持著溫柔得體,但凡公開場合,她都三句不離秀恩愛,結果夫妻同框次數為零,被號稱是最稱職的花瓶太太。 喪偶式形婚三年,宋嶼墨從未正眼看過自己這位妻子。 空有一張美麗的臉,性格乏味無趣。 直到網傳兩人婚姻關系破裂那日,紀棠早就將已經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放塑料老公面前,哭著等他簽字分財產。 ——“老公……嚶嚶嚶人家離開你就不能活了!” 2、 后來,圈內姐妹忍不住紛紛追問她跟宋家這位艷冠全城的公子離婚感受? 紀棠撩著剛燙好的深棕色大波浪長發,輕輕一笑: 【跟他這種無欲無求的工具人離婚要什麼感受?】 【要不是宋家老爺子要求我結婚三年才能分家產,誰要用盡渾身解數扮演白蓮花哄他玩?】 【幸好能成功離婚,再不提離,老娘就要忍不住綠了他!】 笑話!拿著離婚分到的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整天住豪宅開豪車,被娛樂圈小鮮肉追著獻殷勤,過著醉生夢死的小富婆生活,不香嗎? 誰知剛轉身就看見站在人群外的男人,穿著純黑色西裝的氣度清貴又驕矜,似笑非笑地望著她。 “紀棠”宋嶼墨金絲眼鏡下的眸子斂起,視線盯著這個美艷又明媚的女人,優雅地撕了手上那份巨額離婚協議書,聲音清冷而纏綿:“不是離開我,就不能活了嗎?” “那就好好活。” 紀棠:“…………?” 不,我想死!!! · 演技派白蓮花x偏執狂腹黑霸總。 先婚后愛,狗血俗套故事,男主追妻火葬場的雙倍排面已經在安排了
36.4萬字8.18 29200 -
完結1297 章
替嫁甜婚:爹地,媽咪太撩了
一場陷害,她與陌生男人荒唐一夜,她落荒而逃而他緊追不舍;為給外婆治病,她被迫頂替繼妹嫁入豪門霍家,婚后卻被發現懷孕!霍御琛——她的新婚丈夫,亦是霍家繼承人,手段殘忍冷血無情。對她趕盡殺絕,最終害了肚中孩子。六年后,她攜二寶歸來,技能全開,狠狠虐了曾欺負她的人。前夫卻忽然跪地求饒:“老婆我們復婚吧,當年睡了你的人是我,我要負責!”她不屑拒絕,
137.7萬字8 71757 -
連載336 章

女兒火化時,渣總在為白月光放煙花
女兒腎衰竭,手術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過生日爸爸能陪她去一次游樂場,她想跟爸爸單獨相處。我跪在傅西城的面前,求他滿足女兒的心愿,他答應了。 可生日當天,女兒在寒風中等他,等到吐血暈厥,他都遲遲沒有出現。 女兒病情加重,搶救失敗。 臨死前,她流著淚問我,“媽媽,爸爸為什麼喜歡程阿姨的女兒卻不喜歡我?是我還不夠乖嗎?” 女兒帶著遺憾離開了! 從她小手滑落的手機里正播放著一條視頻,視頻里,她的爸爸包下最大的游樂場,正陪著他跟白月光的女兒慶祝生日。
67.7萬字8 17878 -
完結707 章

離婚后,厲少追妻路漫漫
五年前,她放棄尊嚴淪為家庭主婦,卻在孕期被小三插足逼宮被迫離婚。 五年后,她帶著兩只萌寶強勢回歸,手撕渣男賤女搶回屬于她的家產。
127.9萬字8 4154 -
完結258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離家出走了
【倔犟驕傲的前鋼琴公主VS偏執占有欲極強的房地產霸總】 20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捧在心尖上的女友,是最羨煞旁人的“商界天才”和“鋼琴公主”。 25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隨意玩弄的玩具。 沈硯初恨她,恨到骨子里。 因為她哥哥一場綁架策劃害死了他的妹妹。 18歲的沈聽晚不堪受辱從頂樓一躍而下,生命永遠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華。 而她跟沈硯初的愛情,也停留在了那一天。 再見。 已是五年后。 沈硯初對她的恨絲毫未減。 他將她拽回那座她痛恨厭倦的城市,將她困在身邊各種折磨。 日復一日的相處,她以為時間會淡忘一切,她跟沈硯初又像是回到曾經最相愛的時候。 直到情人節那晚——— 她被人綁架,男人卻是不屑得嗤之以鼻,“她還不配我拿沈家的錢去救她,撕票吧。” 重拾的愛意被他澆了個透心涼。 或許是報應吧,她跟沈硯初的第二個孩子死在了綁架這天,鮮血染紅了她精心布置的求婚現場。 那一刻,她的夢徹底醒了。 失去了生的希望,當冰冷利刃劃破黎笙的喉嚨,鮮血飛濺那刻,沈知硯才幡然醒悟—— “三條命,沈硯初,我不欠你的了。”
46.5萬字8 184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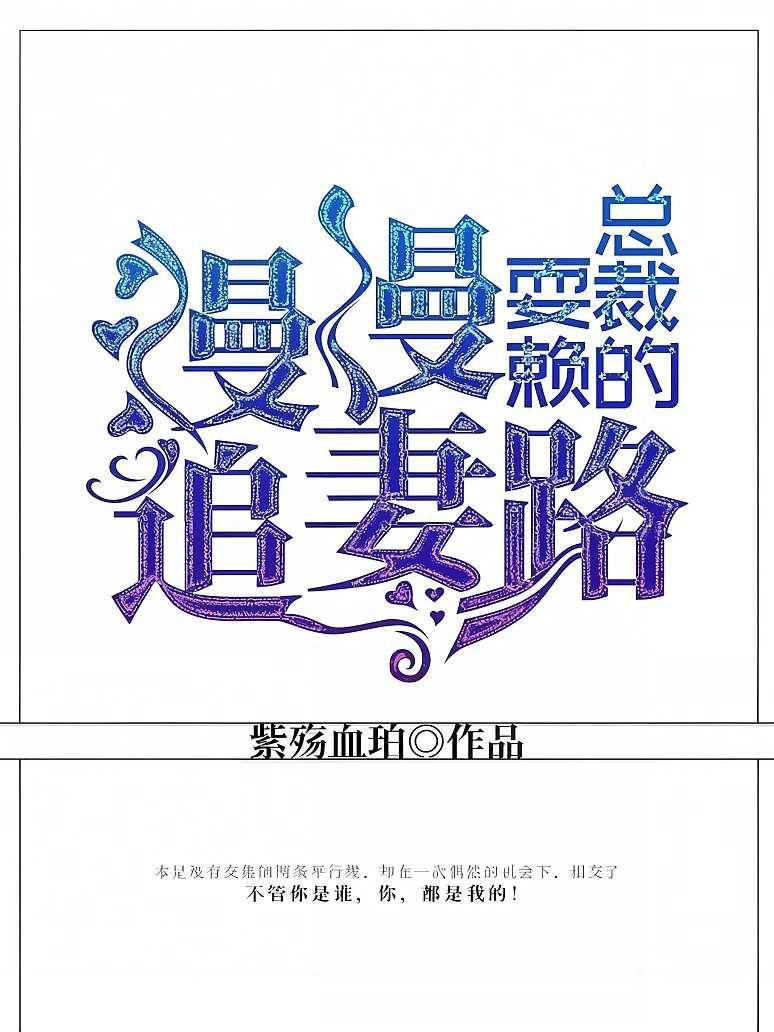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