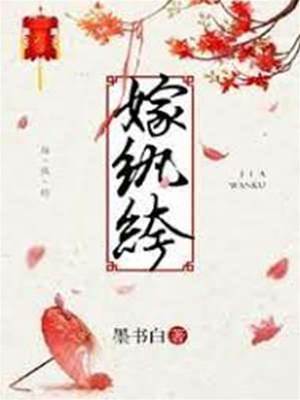《藏鸞》 第1卷 第88章 心如死灰
初春的阳过窗棂,洒在杨既明的袍上,暖意融融,却驱不散他周的沉寂。
他的毒已被阿团尽数拔除,伤势也好了大半,但这几日,他却始终未曾踏出院门一步。每日除了阿团来诊脉,便只有送饭的下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窗外,一株早开的桃花探出枝丫,白的花瓣随风轻颤。杨既明静静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
“知宴兄,怎么不进来?”
门外,沈知宴的影微微一滞,随即推门而。他站在影界,神平静,却一言不发。
屋内一时静默,唯有春风穿堂而过,带起细微的尘埃。
良久,杨既明低声问道:“知楠……还好吗?”
沈知宴眸微动,眼底闪过一丝复杂。
(他果然……还是问了。)
作为挚友,他一直知道杨既明对妹妹的心意。杨既明温润如玉,才华横溢,若妹妹嫁给他,必定会被捧在手心,珍之重之。
可偏偏——
(楠儿心里装的是萧珩。)
(即便那人伤至深,仍固执地不肯回头。)
沈知宴闭了闭眼,压下心中翻涌的绪,淡淡道:“无碍。”
杨既明轻轻“嗯”了一声,指尖无意识地挲着茶盏边缘,低声道:“那就好。”
又是一阵沉默。
沈知宴看着他消瘦的侧脸,忽然想起年时,三人一同在书院读书的景。那时的杨既明意气风发,谈笑间皆是锦绣文章,何曾像如今这般……沉寂如死水。
(若没有萧玠的算计……)
(若没有那场差阳错……)
(他们之间,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
可这世上,从无“如果”。
沈知宴最终只是深深看了杨既明一眼,转离去。临出门前,他脚步微顿,低声道:
“既明,好自为之。”
Advertisement
门扉轻合,将满室春隔绝在外。
杨既明着紧闭的房门,角扯出一抹苦笑。
(他终究……连一句责备都没有。)
(可这样的宽容,比任何惩罚都更让人痛彻心扉。)
窗外,一片桃花被风吹落,轻轻飘进窗内,落在他的掌心。
(就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时……)
(终究,零落泥。)
新绿的柳枝轻拂窗棂。萧珩坐在书房内,手中的公文迟迟未翻一页。
自那夜误伤沈知楠后,他再未见过。
沈知宴将护得极紧,每次他去探,总被拦在院外。理由千篇一律——“楠儿需要静养。”
(静养……)
(还是……不愿见他?)
窗外阳正好,可萧珩却觉得心头泛冷。他无意识地拉开桌案屉,一支未完工的青鸟玉簪静静躺在其中。簪首的青鸟只雕琢了一半,羽翼未丰,却已显灵动之姿。
他怔了怔,鬼使神差地手拿起。
(这是……他刻的?)
玉簪温润的触莫名悉,脑海中忽然闪过零碎的画面——晨中,赧的看着他为带上玉簪.......
心口骤然一疼,萧珩下意识按住口,眉头紧蹙。
(为何一想到……)
(这里就会如此难?)
他沉默片刻,终是将玉簪轻轻放回屉,起走向门外。
庭院里,春正好。
花园里,沈知楠坐在石桌旁,目落在远那片灼灼盛放的桃花上,神沉静,却着一丝倦意。
脚步声自远响起,不疾不徐,却在离几步之遥时蓦然停住。
沈知楠回眸,正对上杨既明复杂的目。
两人静默相视,谁都没有先开口。
良久,沈知楠轻叹一声,指了指旁的石凳:“坐。”
杨既明形微震,似是不敢相信还愿与他同席。他缓步上前,在侧坐下,侧首着清瘦的侧脸,低声道:“体如何了?”
Advertisement
沈知楠的目依旧落在远的桃花上,角微扬:“已无恙了。”
杨既明看着苍白的脸和眼下淡淡的青影,心中苦涩——
(真的无恙了吗?)
(若真的无恙,为何眉间的愁绪仍未散去?)
春风拂过,几片花瓣打着旋儿落下。杨既明垂眸,轻声道:“明日……我要回京了。”
沈知楠转过头来,对他轻轻一笑:“既明大哥保重。”
这一声久违的“既明大哥”,让杨既明心头一震。他着浅淡的笑,头滚动,最终也扯出一个微笑:“好。”
两人不再言语,只并肩坐着,静静看着远的桃花纷飞。
那些未出口的歉意,那些曾的执念,那些错付的深……
都在这一刻,随着春风消散。
(有些遗憾,不必言说。)
(有些释然,心照不宣。)
桃花落尽,余香犹在。
远的桃花树下,沈知楠与杨既明并肩而坐,微风拂过,扬起鬓边的碎发。角带着浅淡的笑意,目和,而杨既明亦是神温润,两人之间仿佛有一种无声的默契。
萧珩站在回廊下,死死盯着这一幕,心口那悉的绞痛再次翻涌而上,疼得他指尖发颤,不自觉地攥紧了前的襟。
(为什么……)
(看着和别人在一起,会这么难?)
他踉跄着后退半步,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琰之?”
江寻不知何时站在了他后,顺着他的视线去,眉梢微挑。
萧珩没有回头,仍死死盯着远,声音沙哑:“那是谁?”
江寻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是在问杨既明,眼底闪过一丝狡黠。
(这是……开始在意了?)
他故意拖长了语调,慢悠悠道:“他啊——杨既明,杨阁老的嫡孙,和你媳妇是青梅竹马。”
Advertisement
“青梅竹马”四个字被他咬得极重,说完,他还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萧珩的表。
果然,萧珩的脸瞬间沉,眸中翻涌起暗。
江寻眼睛一亮,心中暗喜,继续火上浇油:“听说当初沈丞相是有意把嫂夫人许给他的,只是陛下抢先下了赐婚的圣旨。”
话音未落,萧珩周的气息骤然冷冽,指节得咯咯作响。
江寻见状,差点笑出声来——
(失忆了又怎样?)
(骨子里的醋劲儿可一点没!)
他故作叹息地摇头:“唉,可惜啊可惜,若非圣旨,说不定现在……”
“闭。” 萧珩冷冷打断,目仍锁在远那两道影上,口剧烈起伏。
江寻见好就收,拍了拍他的肩,语重心长道:“琰之啊,有些事……错过了,可就真的错过了。”
说完,他转离开,角却忍不住上扬。
(这下……)
(某人该坐不住了吧?)
而萧珩仍站在原地,看着桃花树下沈知楠浅笑的模样,心口的疼意与莫名的烦躁织,让他几乎不过气。
(青梅竹马?)
(险些……嫁给他?)
萧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看着沈知楠与杨既明并肩而坐的背影,看着他们低声谈时边浅淡的笑意,看着他们起离开时,杨既明下意识虚扶在后的手……
(青梅竹马……)
(险些嫁给他……)
江寻的话如毒刺般扎在心头,让他呼吸都变得艰涩。
日影渐斜,暮四合。
花园里的人早已散去,唯有风卷着残花掠过空的石桌。萧珩仍站在原地,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孤零零地投在青石板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终于动了动僵的体,迈步时,膝盖传来针刺般的麻意。
心口的疼意未消,反而愈演愈烈,像有一把钝刀在里来回搅动。他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路过一座凉亭,余瞥见石桌上遗落的酒壶。
萧珩顿了顿,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抓起酒壶仰头灌下。
酒冰凉,过咙时却烧起一片灼热。可这远远不够——
“拿酒来。” 他哑声吩咐。
小厮很快抱来两大坛烈酒,战战兢兢地退下。萧珩拍开泥封,直接提起酒坛往中倾倒。
辛辣的滋味如烈火滚过五脏六腑,烧得他眼眶发烫。
(这样……就好。)
(醉了,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醉了,心就不会这么疼了。)
他喝得又急又凶,酒顺着下颌落,浸湿了襟。坛中酒尽,他抬手抹去边的残酒,却发现眼前竟浮现出沈知楠的脸——
替他包扎伤口时微蹙的眉,站在廊下等他归来的影,被他误伤时苍白的脸……
“砰!”
酒坛砸在地上,碎片四溅。
萧珩踉跄着站起,眼前一阵阵发黑。可醉意越深,的模样却越发清晰。
(为什么……)
(连醉酒都避不开?)
夜风骤起,吹散了他未出口的诘问。
月下,那道高大的影摇摇晃晃,最终重重跌坐在石阶上,低头捂住了脸。
沈知楠接到江寻的传话时,指尖微微发颤。
“琰之在凉亭喝醉了,无人敢近。”
抿了抿,终究还是匆匆赶了过去。
夜已深,凉亭的石阶上,萧珩独自坐着,形半隐在影里,周酒气浓烈。
轻轻走近,手扶住他的手臂:“王爷,回去吧。”
萧珩茫然抬头,醉眼朦胧中,的面容近在咫尺。
(又来了……)
(这该死的幻觉。)
他自嘲地扯了扯角,却仍顺从地被扶起,踉跄着往房间走去。
一路上,沈知楠沉默不语,只稳稳地托着他的手臂。夜风拂过,带起发间淡淡的幽香,萧珩恍惚间觉得,这气息悉得令人心颤。
回到房中,替他脱去鞋袜,又拧了湿帕子净他脸上的酒渍。动作轻。
萧珩半阖着眼,看着近在咫尺的眉眼,忽然觉得间干。
(既是幻觉……)
(那便放肆一回吧。)
他猛地攥住的手腕,一个翻将压在榻上。沈知楠尚未反应过来,便被狠狠堵住——
这个吻又急又凶,带着浓烈的酒气和说不清的,仿佛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
沈知楠睁大眼睛,脑中一片空白。
(为什么……)
(明明那般厌恶……)
(为何还要如此?)
萧珩的掌心滚烫,顺着的腰线游移,所过之皆带起一阵战栗。他吻得愈发深,仿佛要将拆吃腹。
(反正是梦……)
(反正醒来,一切都会消失……)
他没有看见,下的人儿眼角落的泪。
沈知楠偏过头,眼神空地着床帐上摇曳的影。
不再挣扎,也不再看他,仿佛一失去灵魂的躯壳,任由萧珩肆意索取。
可萧珩却不肯放过,明明是他的梦,为何依旧不肯看自己。
“看着我。” 他扣住的下,强迫转过脸来。
他的眸中翻涌着疯狂的占有,动作愈发凶狠,像是要将彻底碾碎。
沈知楠被迫迎上他的目,瓣咬得渗出丝,却仍不肯发出一丝声音。
(既然他厌恶……)
(既然他以前待的种种都是假的……)
(为何还要这样辱?)
萧珩盯着倔强的模样,心底那莫名的怒火烧得更旺。
“说话!” 他嗓音嘶哑得不像话。
沈知楠终于承不住,破碎的呜咽从边溢出,眼泪无声落。
可萧珩却像着了魔一般,俯拭去眼角的泪,动作却丝毫不停。
(既然在梦里……)
(那便彻底占有。)
(让再也逃不掉。)
窗外,月被乌云遮蔽,屋内只剩错的息与压抑的哭泣。
而沈知楠,终究在他一次又一次的侵占中,彻底闭上了眼。
(心死了……)
(便不会再痛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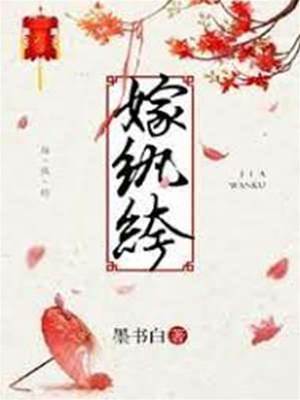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933 章

領袖蘭宮
入宮了,她的願望很簡單:安安靜靜當個小宮女,等25歲放出去。 可是!那位萬歲爺又是什麼意思?初見就為她 吮傷口;再見立馬留牌子。接下來藉著看皇后,卻只盯著她看…… 她說不要皇寵,他卻非把她每天都叫到養心殿; 她說不要位分,他卻由嬪、到妃、皇貴妃,一路將她送上后宮之巔,還讓她的兒子繼承了皇位! 她后宮獨寵,只能求饒~
449.3萬字8 89937 -
完結1135 章
逆天神妃
她是華夏的頂尖鬼醫,一朝穿越,成了個被人欺辱至死的癡傻孤女。從此,一路得異寶,收小弟,修煉逆天神訣,契約上古神獸,毒醫身份肆意走天下。軟弱可欺?抱歉,欺負她的人還冇生出來!卻不知開局就遇上一無賴帝尊,被他牽住一輩子。 “尊上!”影衛急急忙忙跑來稟報。躺床上裝柔弱的某人,“夫人呢?”“在外麵打起來了!夫人說您受傷了,讓我們先走!她斷後!”“斷後?她那是斷我的後!”利落翻身衝了出去。
141.4萬字8 473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