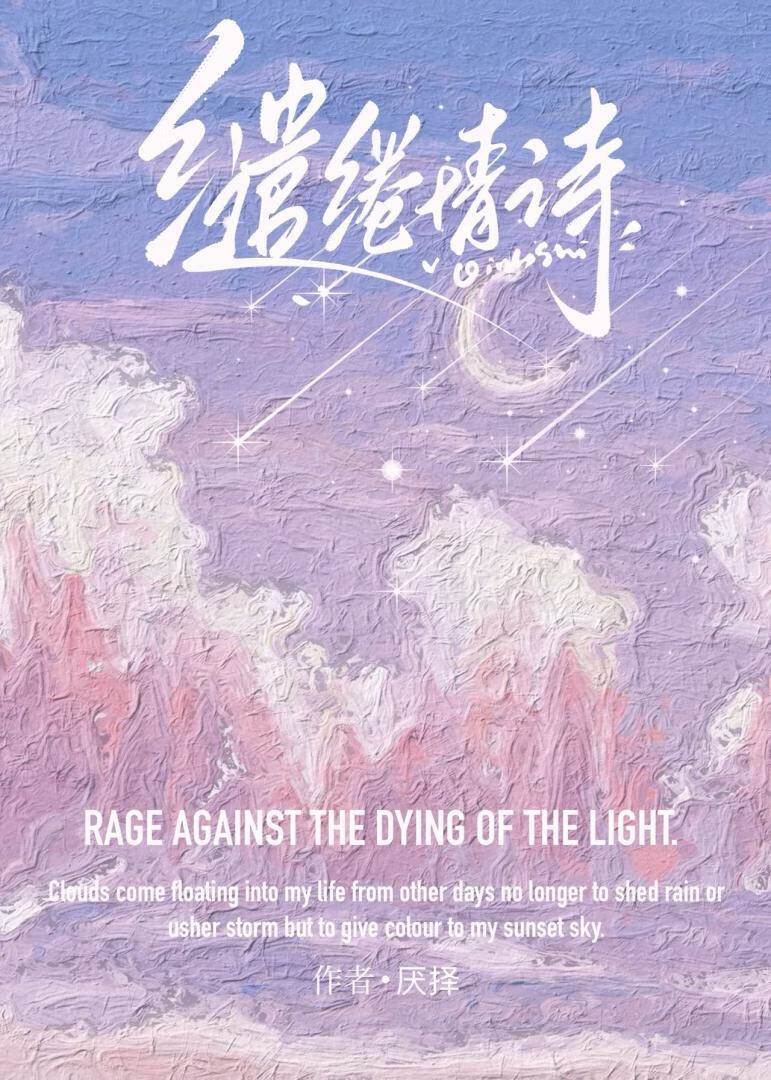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撩完離婚!豪門大佬紅眼失控》 第1卷 第101章 滿腦子廢料
沉悶的覺,一直延續到和清歡分別,坐進黑轎車的副駕駛。
不帶司機,傅聿自己開車來,專心致志地留意著路況,而盛瀟兒始終扭頭看著車窗外。
久別重逢,不該這般死寂。
盛瀟兒的定力不及傅聿的好,靜了一會兒,坐不住了,把頭轉回來,了,正準備隨便找點話題,傅聿卻率先開口打破沉默。
“澆澆,你沒戴戒指。”
盛瀟兒怔了怔。
把戒指取下來時,就已經事先備好答案,條件反就回答:“嗯,我怕弄丟。”
說話的同時大腦也在飛速運轉,慢半拍地捕捉到傅聿口吻里的不悅,約藏了幾分指責的意味,盛瀟兒接著又一怔。
“你的意思是,因為我不戴戒指,沒有亮明已婚份,所以才遭到別人搭訕?”
“是這個意思嗎?”
“明明是別人的錯,你反過來怪我?”
盛瀟兒瞠圓了雙眸,難以置信地接連反問。
男人是不是都這樣,只要在外面有了小三,原配便就連站著呼吸也是錯的。
傅聿眉心微皺,問:“你在生氣?”
他無法理解。
為什麼瞞回國的是,有家不歸的是,摘掉戒指的是,而現在,居然是在一臉委屈地向他發脾氣?
他承認,看到沒戴戒指,腔的不爽悶了高。
Advertisement
他陳述事實而已,和連珠炮的質問有何干系?
盛瀟兒用力抿,心底翻涌的滋味說不清道不明,猛地把頭甩開。
“沒有,我沒生氣。”說,“我在發癲。”
“……”
氣真的越來越大。
毫無起因的發作,傅聿沒和其他人相過,頭一個就是,經驗欠缺,找不出由。
看到氣鼓鼓的側臉,難免又覺得無奈:“是不是不講道理是人的共?”
“……你談過幾個啊,還總結出共來了。”
喬非也這麼對他?
盛瀟兒的想象中,自己是以嘲諷的語氣來說出這句話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等真正說出口,嘲諷是有了,更多的,卻是沮喪與酸溜溜。
正是這一也不住的酸溜溜,莫名取悅了傅聿。
臆抒出一口輕嘆。
罷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懟,的路數他至今也看不明白,除了哄著著,別無他法。
至于怎麼哄——
在紅燈路口,傅聿單手握住方向盤,另一手拿起手機,撥通吳書的號碼。
手機連著藍牙公放,吳書的聲音通過車音響,清晰無比地傳出。
“傅總。”
“我們現在對恒思科技的投資額是多?”
吳書報出一個并不算小額的數字,說:“準確的數額,我得問戰略投資部拿,待會兒發到您的手機上?”
Advertisement
“不用了。”傅聿的指節敲著方向盤,兩下過后,“下一季度,直接全部砍掉。”
吳書默了半秒。
“好的,我去傳達。”
撤掉投資恒思不一定會馬上就倒,但行為發起者是復山,這在業毋庸置疑是最強烈的信號,恒思活不久了。
“對外宣發口徑,是否需要統一?”吳書請示道。
傅聿略加沉思,音調不變:“就說,他們既然想請傅太太吃宵夜,這筆資金就當作買單。”
吳書:“?”
雖然在回答吳書,傅聿的黑眸始終在一瞬不瞬地盯著盛瀟兒。
盛瀟兒緩慢地轉過頭來,不咸不淡地瞟他一眼:“……你好昏庸。”
聽見盛瀟兒的聲音,吳書再遲鈍也明白了,當然不可能按傅聿的原話發布,一頓,維持公事公辦的口吻:“我明天請公關部擬出新聞初稿,先給您過目。”
“行。”
“傅總,如果您沒有其他吩咐的話……”
“嗯,掛吧。”
吳書如同刑滿釋放,連忙急匆匆地掛了電話。
“滿意了?”傅聿看著盛瀟兒。
盛瀟兒言又止,說真的,不太滿意。
“你砍掉的投資,本來就是你的錢,怎麼算也不能算作姓余的買單啊。”
“有理,那怎麼辦?”
“……誰知道你怎麼辦,反正宵夜我是一口也沒吃到。”盛瀟兒的臉又轉向了窗外,聲音悶悶的。
Advertisement
綠燈亮起,轎車繼續平穩行駛。
“現在帶你去吃?”
“不去。”
傅聿突然覺得,有人去非洲一趟,回來變得特別難哄。
“澆澆,別生氣了。”
“都說了我沒生……”
“明早八點,我要飛深圳出差一周。”傅聿打斷道。
分離了這麼長時間,兩人好不容易見面,團聚不到十個小時,就要再度分隔兩地,確定要拿后腦勺一直和他置氣?
盛瀟兒不吭聲了。
今非昔比。
才不會再輕易被他縱緒。
他要去哪兒是他的事,不舍啊惆悵啊那些緒,統統都不會再有。
“你明早都要出差了,今晚還逮我回家干嘛,一個晚上能干什麼?還不如就留我在歡歡那兒繼續住著……”
的行李也都還在清歡家里。
盛瀟兒不滿地細聲抱怨,說著說著,倏地一道靈從心頭劃過。
猛地轉頭看向傅聿。
他仍在專心開車,察覺的視線,分神向投來一記掃視,快速一掠,足以讓盛瀟兒覷見黑眸深充滿的灼亮。
他還好整以暇地重復的話:“一個晚上能干什麼?嗯?澆澆?”
他……煩死了!
盛瀟兒回座椅里,雙手攥著安全帶,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警戒姿態。
“下流,骯臟,滿腦子廢料,誰管你啊,我生理期。”
傅聿發現自己指不定有傾向,他簡單一句話而已,也能招引出如此不客氣的怒罵。
問題在于,他居然覺得這副樣子,可得。
目直視著前方路況,掩飾掉眸中的一抹莞爾,傅聿話音微揚:“奇怪,我怎麼記得你生理期剛過?”
盛瀟兒的例假每個月都很準,不怪傅聿記得清,因為每當前后的幾日,有人總是肆無忌憚,仗著安全,百無忌,特別破例允許他……
盛瀟兒的臉紅得都快了。
他什麼人啊,不是很忙嗎!怎麼連這種事都記這麼清楚!
“是你生理期還是我生理期?是你大姨媽還是我大姨媽?你和它還是我和它?我說它來了就是來了!天王老子來了它也是來了!”
心是虛的,但語氣必須強。
傅聿淡淡掃盛瀟兒一眼:“好,知道了。”
手了的頭發。
“回去給你煮紅糖水。”
猜你喜歡
-
完結391 章
閻王愛上女天師
白梓奚只是隨師父的一個任務,所以去了一個大學。奈何大學太恐怖,宿舍的情殺案,遊泳池裡的毛發,圖書館的黑影……白梓奚表示,這些都不怕。就是覺得身邊的這個學長最可怕。 開始,白梓奚負責捉鬼,學長負責看戲,偶爾幫幫忙;然後,白梓奚還是負責捉鬼,學長開始掐桃花;最後,白梓奚依舊捉鬼,然而某人怒摔板凳,大吼:哪裡來的那麼多爛桃花,連鬼也要來?白梓奚扶腰大笑:誰讓你看戲,不幫忙?
33.8萬字5 34513 -
完結1074 章

我渣了死對頭的哥哥
司西和明七是花城最有名的兩個名媛。兩人是死對頭。司西搶了明七三個男朋友。明七也不甘示弱,趁著酒意,嗶——了司西的哥哥,司南。妹妹欠下的情債,當然應該由哥哥來還。後來,司南忽悠明七:“嫁給我,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子,作為嫂嫂,你管教小姑子,天經地義。讓她叫你嫂子,她不聽話,你打她罵她,名正言順。”明七:“……”好像有道理。司西:“……”她懷疑,自己可能不是哥哥的親妹妹。
90.2萬字8 35281 -
完結462 章

傅爺的王牌傲妻
寧洲城慕家丟失十五年的小女兒找回來了,小千金被接回來的時灰頭土臉,聽說長得還挺醜。 溫黎剛被帶回慕家,就接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告。 慕夫人:記住你的身份,永遠不要想和你姐姐爭什麼,你也爭不過。 慕大少爺:我就只有暖希這麼一個妹妹。 慕家小少爺:土包子,出去說你是我姐都覺得丟人極了。 城內所有的雜誌報紙都在嘲諷,慕家孩子個個優秀,這找回來的女兒可是真是難以形容。 溫黎收拾行李搬出慕家兩個月之後,世界科技大賽在寧洲城舉辦,凌晨四點鐘,她住的街道上滿滿噹噹皆是前來求見的豪車車主。 曾經諷刺的人一片嘩然,誰TM的說這姑娘是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哪個窮鄉僻壤能供出這麼一座大佛來。 兩個月的時間,新聞爆出一張照片,南家養子和慕家找回來的女兒半摟半抱,舉止親暱。 眾人譏諷,這找回來的野丫頭想要飛上枝頭變鳳凰,卻勾搭錯了人。 誰不知道那南家養子可是個沒什麼本事的拖油瓶。 南家晚宴,不計其數的鎂光燈下,南家家主親自上前打開車門,車上下來的人側臉精緻,唇色瀲灩,舉手投足間迷了所有女人的眼。 身著華服的姑娘被他半擁下車,伸出的指尖細白。 “走吧拖油瓶……” 【女主身份複雜,男主隱藏極深,既然是棋逢對手的相遇,怎能不碰出山河破碎的動靜】
176萬字8.46 260012 -
連載120 章

限時閃婚:傅少追妻不要臉
閃婚一個月后的某一晚,他將她封鎖在懷里。她哭:“你這個混蛋!騙子!說好婚后不同房的……”他笑:“我反悔了,你來咬我啊?”從此,他食髓知味,夜夜笙歌……傅言梟,你有錢有權又有顏,可你怎麼就這麼無恥!…
20.6萬字8 11589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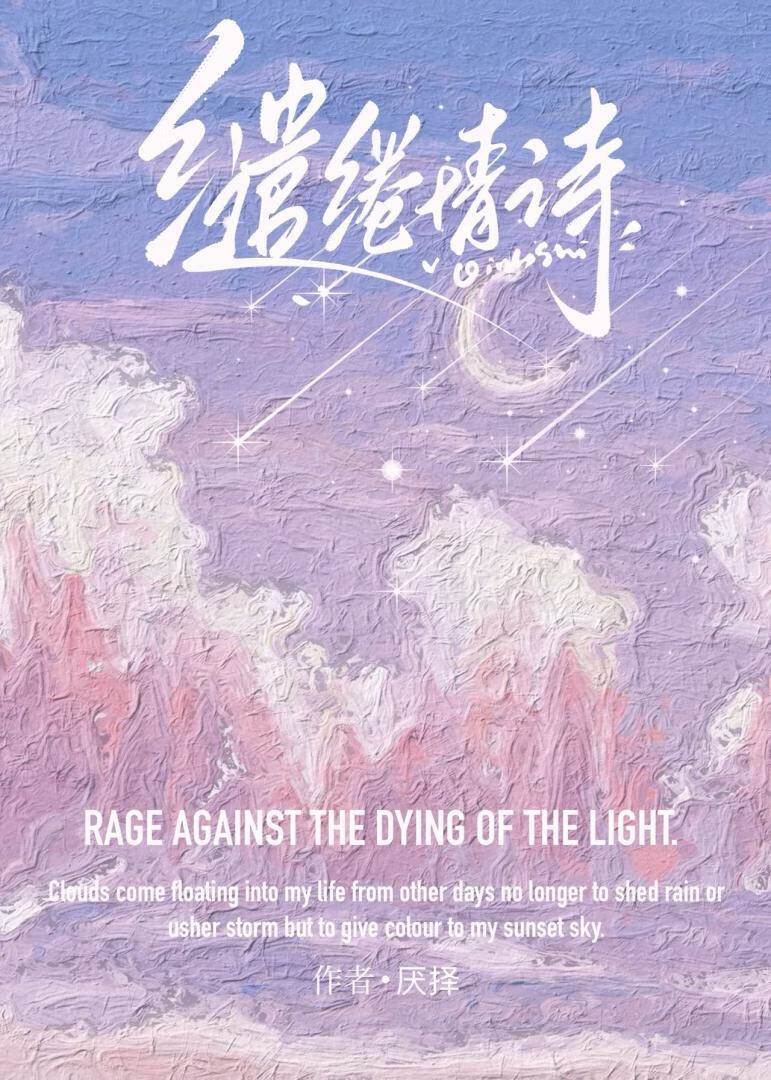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