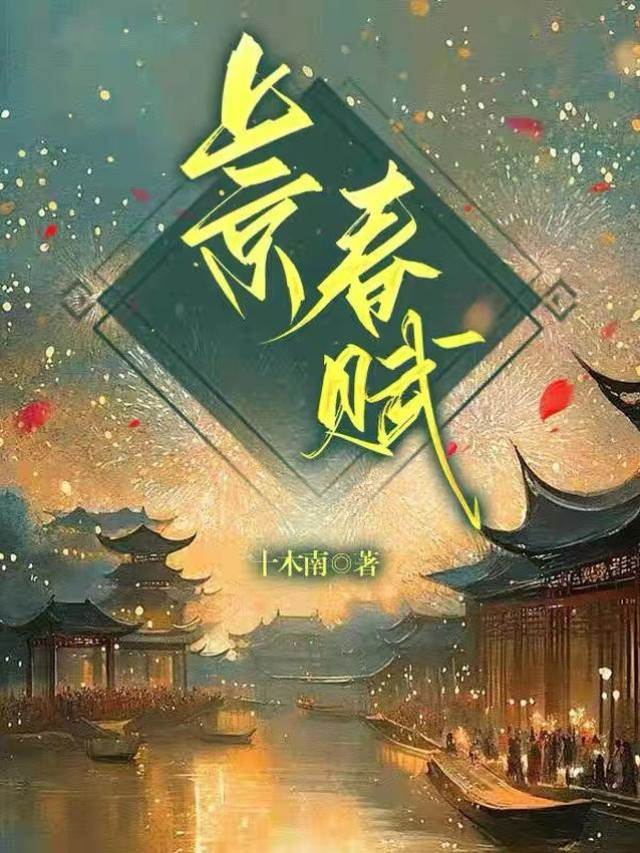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惹皇叔》 第152頁
下方大臣只當皇帝換了個人執筆錄事,并沒有在意。
一員大臣接過陳則的話,繼續稟奏:“臣到工部未久,諸般事務皆生疏,蒙陛下圣恩,不敢怠慢,丹水水文與渭水相近,臣治渭水多年,略有心得,臣才與陳大人商議,愿赴齊州當地,一則探查水,二則核算錢款細項……”
這大臣的聲音聽得耳,傅棠梨抬眼了一下,發現又是個人。
原咸縣令何友松,這人不但治水有才干,更兼錚錚鐵骨,當初被林貴妃百般拷打,是沒供出太子妃與淮王之事,趙上鈞頗嘉許,擢其連升三級,現于工部任侍郎之職。
傅棠梨見及何友松,不期然又想起在永壽鎮的那些事兒,臉上一熱,急忙低頭。
又有新任的工部尚書上前,補充何友松未竟之。
趙上鈞正襟危坐,滿面肅容,卻在下面地過手來,住了傅棠梨的腳踝,用指腹挲著。
趕把腳回來,答答地瞪了他一眼。
他好似回眸了一眼,目相,溫而繾綣,的臉又開始發熱,急急垂眸。
可恨這人卻做若無其事狀,轉眼又在大臣面前做出一派威嚴的儀態。
偏他煩人,既有正事要辦,何必地把進宮來,怪不好意思的。
傅棠梨心里嘀嘀咕咕的,拿筆隨意勾了兩下。
不是起居郎,記不下皇帝的言行舉止,這會兒百無聊賴,又眼看了看趙上鈞。
這個角度,恰好瞧見他的側面,廓雋永分明,似刀鋒雕琢而,睫長得特別惹眼,濃郁如同羽一般,當他垂眸的時候,會在眼底落下幽深的影子,人分辨不出他的喜怒。
啐,焉知這會兒不是假正經。
Advertisement
傅棠梨思量片刻,咬著笑了起來,筆尖蘸了墨,在紙上開始涂涂抹抹,一會兒一會兒抬頭看他一眼,笑一下,再涂涂抹抹。
太過于專注了,以至于大臣們退下去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再一抬頭,趙上鈞已經靠了過來,那張俊的面容直接杵在的面前。
“寫什麼?”
傅棠梨有些心虛,抓著那紙張,下意識地想把它一團:“沒什麼,別看。”
趙上鈞手臂長而有力,一手按住,一手取過了那紙。
在畫他。
顯然傅二娘子學過丹青,寥寥數筆,自神韻,但見畫中人劍眉斜飛,朗目如星,鼻梁高,雖則面容沒有十分像,但那筆鋒之下,畫中人神態冷峻,氣勢如劍,似要破紙而出,除了趙上鈞,還會有誰呢。
但趙上鈞卻不太滿意,他慢慢地近,住,咬的耳朵:“嗯,你瞧著,我有這麼兇嗎?”
耳朵發燙,傅棠梨眼波流轉,瞥他一眼:“還說呢,喏,可不是現在就在兇我。”
殿門已經掩上,案幾邊,赤金的饕餮張開大口,吐出龍涎,如同山間的嵐霧,約不可捉,那是一種奢靡而曼妙的香氣,在華燈的影子中浮,擾人心思。
“我想你,一天不見就想得不行,怎麼會兇你呢,不要總來詆毀我。”趙上鈞湊過去,輕輕地吻。
他的重量在上,承不住,向后仰倒,兩個人一起跌坐在地,趙上鈞的手不知道何時了過來,只一拉,解開了的帶。
領口散開,危峰堆雪,了一下,呼之出。
“啊!”傅棠梨驚呼了一聲,下意識地捂住口,側、彎腰,想要遮掩住這一片春。
趙上鈞順勢一按,從背后住了,手指一勾,羅衫褪下,出后背大片雪白的凝脂,以及,一截小蠻腰,盈盈不堪一握。
Advertisement
華的宮殿,雪松木地板上鋪著的寶相花錦紋織金毯,帶著一層細膩的、絨般的,在上面,好似上的孔都舒張開了,有些麻麻的。
傅棠梨抖了一下,雖然四下無人,但還是不敢大聲,嚶嚶似蚊吶:“做什麼呢,討人嫌得很,放開我。”
趙上鈞好整以暇,一只手制住,另一只手拿起一支筆來,皇帝的案頭放著批閱奏折的朱墨,如丹砂,他蘸了這墨,在傅棠梨的肩胛骨落下一筆。
很。
傅棠梨咬住,忍不住笑了一下,又又惱:“別鬧我。”
“噓,別。”趙上鈞的筆鋒開始在背上游走,聲道,“我也畫一樣東西,梨花猜猜看,畫的是什麼,若猜得出來,我就放了你,若猜不出來。”他微妙地停頓了一下,輕輕地笑了起來,“我今晚就要好好罰你一頓。”
他要罰什麼,不用說也知道。
“不許你涂畫的,我要惱你了。”傅棠梨掙扎著想要逃,但無非也就像是一只小的鳥雀,撲騰著,撲不出趙上鈞的手心,反而像是挑逗一般,脂膩,蹭來蹭去,烏云般的秀發散開一地,宛如流水。
如雪,朱墨嫣紅,似雪中落下梅無數。
趙上鈞的呼吸沉了下來,他又蘸了一抹墨,筆鋒勾勒,時輕時重、時緩時急,漸漸往下走,到了腰窩,還在往下,到尾椎,打了個圈圈。
傅棠梨激烈地了一下,幾乎要彈跳起來:“!”
“嗯?那我幫你撓撓。”趙上鈞低低地、這麼說著,俯下去,了。
“嗚……”傅棠梨難耐地仰起了脖子,“道長,不行、不要了。”
“道長”,這樣兩個字,從口中吐出,似乎是一種求饒的意味,但得一塌糊涂,大抵更是。
Advertisement
趙上鈞的筆鋒繼續向下一,的筆尖進去。
傅棠梨渾發抖,不知道是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原因,著,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地著他:“道、道長……”
天氣微涼,但他的手掌火熱,在那里,一陣陣發燙,背上冒出了薄薄的一層汗,黏黏膩膩。
筆尖的羊毫轉來轉去,不用蘸墨,已經很了。
“知道我畫了什麼嗎?”趙上鈞幾乎在的背上,耳語一般問,他的氣息是雪后的白梅、山林中的烏木,一點微苦,而此時,焚燒起來,如同野炙熱的呼吸,噴在的脖頸,栗。
傅棠梨不自地哆嗦,帶著哭腔,哀求他:“我笨,猜不出來,不玩了,你走開。”
趙上鈞仿佛嘆息了一聲:“是和合符啊,調和,如魚水,如漆投膠,梨花,你覺得我這符箓畫得如何?有效否?要不要……再修改一二?”
第75章 道長,從頭到尾,我只有……
“很好、很好,有效,夠了。”傅棠梨忙不迭地應承,挪著子,想要爬走。
但筆尖還卡在那里,了一下,杵得難,悶哼了一聲,蜷起了,眼角綴著淚珠子,回眸瞪了趙上鈞一眼,燭火搖曳,的眼眸迷離,似橋下驚鴻,春波照影。
令人沉醉。
“既然如此,那就讓我試試效果如何。”趙上鈞終于扔下筆,又將翻了一個面,俯下去。
庭燎的燭陡然暗了一下,復又大放明,像是被人推搡著,劇烈搖,撞得珍珠簾子四下散,錚琮作響,碎珠飛濺。
趙上鈞固有帝王隆威,似大樹參天立于山崖,樹蒼勁虬結,挾驍悍之勢,屢屢征伐,無人能敵。
凝脂堆雪都被他碾軋泥濘,一陣陣濺起、一陣陣。
最近越發氣起來,不就哭,哭得鼻尖通紅,搭搭的,聲音都被攪得支離破碎:“難,地上,你忒魯……”
趙上鈞不答話,直接抄起的腰,就著那種姿勢,將從地上抱了起來,大步向后殿走去,隨著他急促的腳步,燭火的影子依舊搖擺不停,劇烈而激。
傅棠梨倏然張開,卻發不出一點聲音,只能拼命地著氣,好似馬上就要暈厥過去,汗水一陣陣地冒出來,渾都了,滴滴答答地落在他手心里,而后沿著他的手臂流淌下去,到都是黏膩的。
的味道,是糖,甜得要命,一口一口吃掉,一點兒都不剩。
珍珠簾子兀然被扯斷,窸窸窣窣灑了滿地,跳躍著,打著旋兒。
兩個人一起重重地跌在榻上,陷其中,十指錯,地住,毫無間隙。
庭燎高照,纖毫畢現。
……
胡天胡地的一通鬧騰,磨人得很,把傅棠梨折騰得死去活來,苦不堪言。
也不知道折騰了多久,實在太累了,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會兒,待到醒來時,趙上鈞已經不在邊了。
狻猊燃香,燭影搖紅,芙蓉帳中羅衾猶暖,空氣中猶有腥膻氣息浮,人。
宮人上前,躬致意:“北庭大都護張大人求見,圣上去了宣政殿,囑咐勿擾娘子,請娘子好好歇著,圣上過會兒就回來陪伴娘子。”
傅棠梨打了個呵欠,迷迷糊糊地半睜著眼:“這會兒幾時了?”
“戌時過半。”
傅棠梨一激靈,困意全無,趕起:“這麼晚?”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37 章

朕的愛妃只想吃瓜
入宮三年,永寧殿美人燕姝未曾見過圣顏。滿宮嬪妃想盡辦法爭寵,唯有她沉浸在吃瓜系統中,無暇他顧。——【臨武侯的世子不是自己的嘖嘖。】【老古板禮部尚書竟與兒媳扒灰!!!】【艾瑪長公主老實巴交的駙馬竟然養了好幾房外室。】每天各路狗血八卦,誰還記得…
54.3萬字8.5 60625 -
完結211 章
將門醫妃
蕙質蘭心,滿腹才華的將門庶女,嫁給滿腹權謀算計,不受寵的三皇子。 她護他,他防她。 她愛他,他負她。 當他幡然醒悟時,她卻為他徘徊生死之間,病入膏肓。 “活下去,我允你一事,否則,大將軍府和相府將血流成河!” 沉穩腹黑,算無遺策的三皇子,從未說過,他的心,早已為慕子衿著迷。 恨入骨髓、寵如心魔,且無葯可醫。
112.6萬字8 10767 -
完結104 章

梟虎
【溫柔賢德王妃x鐵骨錚錚梟雄】【體型差】【溫馨婚後】人盡皆知,冀王趙虓驍勇無匹,是大靖邊疆第一道銅牆鐵壁,素有“梟虎”之名。他謔號“獨眼兒”,左眸處一道猙獰傷疤,面容兇悍,體格魁梧,更傳言性情暴虐殘酷,曾命人砍下戰俘頭顱烹煮後送給敵將,令其驚駭大罵他“屠閻羅”。寧悠是膽戰心驚地嫁過去的,一輩子恭謹小心,只怕一步不慎便引他暴怒。可多年以後回頭再看,他哪有如此?分明是嘴硬脾氣直,疼愛媳婦卻不自知,更不懂憐香惜玉的粗漢子一個罷了。重來一世,她的願望原本簡單。活得自在些,好好兒地守著這個盡管少有柔情、卻愛她勝過自己的男人,好好兒地將日子過得有聲有色、兒孫滿堂。可百煉鋼還未化為繞指柔,一場巨變卻悄然而至。佞臣矯詔,篡逆削藩,性命攸關之時,趙虓為護她和幼子,被逼舉兵。她唯有慨然陪他踏上征途……【小劇場】趙虓做藩王時和寧悠吵架:-這藩國裏誰做主?何時輪到你對我指手畫腳?反了天了!(色厲內荏)趙虓登基後和寧悠吵架:-我怎就非得聽你的?我堂堂一國之君就不能依著自己的想法來?(虛張聲勢)-好了好了,我錯了,我改還不行?(擰巴扭捏)-我認錯態度怎麽不好了?(心虛嘴硬)-好嬌嬌,不氣了,是我不對……(低頭服軟)衆內監:??陛下竟然懼內王淮: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內容標簽:強強 宮廷侯爵 情有獨鐘 重生 正劇 HE
25.4萬字8 2280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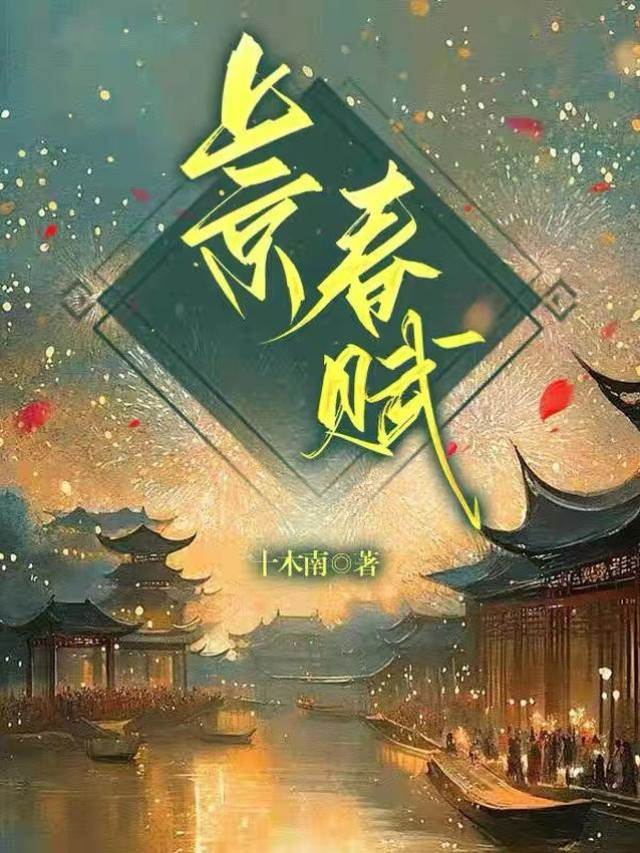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