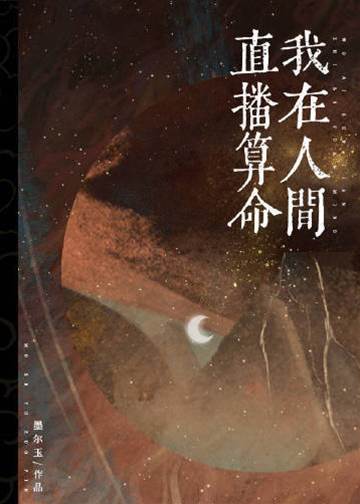《相敬如賓第三年》 第82頁
他長久的沉默,眼底流的憎惡無法遮掩。
喬寶蓓心底駭然,像見一片碧藍澄明的海。這片海深沉遼闊,卻也清澈見底,是如何年復一年地對他昭然若揭的行為視若無睹?甚至自我催眠他沒有太過煩擾,沒有過多的惡意。要不是喬星盛把檢驗報告,傷痕,錄音披給,竟還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和他共度一生。
在這一刻之前,喬寶蓓從來沒覺得他如此可憎恐怖。
深吸氣,鼻子卻閉塞至極:“知道他和我見過,又聯系我,你是還要給他一個教訓嗎?”
聲音止不住地,“一個沒辦法見我,沒辦法聯系我的教訓,落得家破人亡,像嚴博揚那樣?”
“你覺得他不該有這種下場?”傅硯清輕哂,大仇將報的快意貫徹全,他不明白,為什麼要提及第三個橫亙在他們之間的最惡劣的男人。
喬寶蓓不敢置信地睜大雙眼:“你真的找人打了他一頓,把他打住院?”
人證證皆在,已經證據確鑿,直到這刻還抱有幻想。
傅硯清結滾:“那是他做錯事了。”
“他做錯什麼了?只是和我好,你就要這麼對他?”
喬寶蓓耳鳴發作:“普通人在你眼里是微不足道的草芥,還是隨便可以踩死的螞蟻?你讀過軍校,我以為你至為人端正,不會像那些游手好閑的富家子弟那樣,你現在告訴我,你和他們一樣,也會做這種恃強凌弱的事?”
傅硯清極聽這麼主夸耀他,卻是在這種況下。
他心底翻涌萬千,闔了闔眼:“所以你心疼他們,覺得我做錯了?”
“你不覺得嗎?你不認為這是錯事嗎?”
想到過往那些平庸又俗氣的男人,眼淚像一張大網,不可分地籠罩雙眼。
Advertisement
“你這樣對待一個僅有一面之緣的普通人,我很難不懷疑哪天你要是不我了也會這樣對我,覺得我又麻煩又不值一提,可以隨便被置。”
“你就為了一個這樣的男人懷疑我?”傅硯清一字一頓,每個字都像從罅隙里發出的獵獵風聲:“你知不知道他肖想你,對你有不懷好意的念想?你有沒有想過,是他的問題。”
喬寶蓓氣笑了,燈下的眼淚清凌凌:“他有什麼問題?我怎麼不知道?何況我怎麼知道別人如何想我?我管得了別人的想法嗎?他拿得出證據證明被你欺辱,你呢?你這樣污蔑他,就為了給自己罪嗎?還是想拐彎抹角敲打我不應該在夜里見他和他有微信聯系?”
聽百般庇護其他男人,心底的絞痛令他不由手箍的手臂,幾近控不住握力:“你確實不該跟他有聯系。”
他雙眼漲紅,死死盯著:“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瞞著我和他去了海邊?你把我留在家里,坐著他的車,和他談天說地,和他拍照留念。你以為你瞞得天無,我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討厭你對他笑,對他那樣友好,我忍不住去比較你對我的態度。你對他比對我還要寬容放松,你從來沒有主和我約會過,對我總是笑得勉強,迎合得拙劣,你仍把我當做住在你隔壁的那個沒有用的修理工,可以請上門無條件地修理家用,適當地留下來喝杯茶,從未把我當做你真正的的丈夫。”
“我知道我年紀比你大,比你年老,是在你最貧窮最孤苦無依的時候趁虛而。如果不是你的生父婚,你本不會對我求助。我什麼都知道,我都清楚,我也默許你沒那麼我,是貪圖我的財產和庇護才答應和我結婚。我沒想過你全心全意我,是我開始貪心,是我變得貪得無厭,對你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Advertisement
妒火仿若將要從他腔噴涌而出,蔓延到咽的卻是苦而辛辣的哀歌。他的嗓音變得更加低沉,滯:
“我們結婚三年了,我以為我是你的丈夫,可以無條件有你的,被你偏心依賴,我以為你已經對我產生了一眷,哪怕把我當做你的父親一樣對待,我以為你說過的話十句里有一句是真實的,哪怕你只是在哄騙我。”
“我開始看不清,分辨不清你對我的示好是不是真的。你說我對僅有一面之緣的學生狠心,我如何不狠心?你把我當做敵人,站在他邊偏袒他,庇護他,你我怎麼不嫉妒?他甚至不是你往過的男人,僅僅只是一個普通的不起眼的小鎮男孩,你本沒有考慮過我。”
也沒那麼我。
連虛假意地戲弄我,欺騙我都不肯了。
他該如何在一片看似鮮亮麗的空中樓閣里找到錨點?在一片廢墟的塵土里找到一株可以被呵護的花?他一無所有,也不被飾。他匍匐在下,的起手架在脖頸上的是涔著寒意的鐮刀。
“對,你什麼都清楚,你是縱容我包容我的那個,我在你面前一覽無,是個看不清楚狀況的蠢貨。”喬寶蓓笑了一聲,眼淚周而復始地淌落,在面頰上無法干涸,宛如一條永遠流的河。
那是一條心河,流著鮮活的,有糲的砂石捱過,發出陣陣鈍痛。
“你我所以我得回應你,你討厭誰所以我得遠離誰,我知道啊,你覺得我不守婦道,是不是啊?”
傅硯清沉聲:“我從來沒有這麼覺得過。”
喬寶蓓盯著他有些木然的面龐,因束刺眼而瞇起眼:“那你為什麼總是跟我翻舊賬?你就那麼記恨當初的我看不上你?上次提,這次也提。你覺得我不你,我也不覺得你有多我,你分明是把我當做演繹深的木偶,怪我不配合你的獨角戲而對我不分青紅皂白地責怪。”
Advertisement
討厭爭吵,討厭這種無法安定的親關系。惶恐,想逃避,但退無可退。分不清自己為什麼會流淚不安,覺得他說的不對,但又不知從何說起。
他們之間的爭吵就像山難,不論木訥地站在原地亦或是逃跑,都逃不開被湮滅的結果。
他忍無可忍,又何嘗不是?已經足夠忽視他那些見不得的作,他為什麼就不能稍微放過?說得那麼好聽,不還是斤斤計較。
傅硯清的手逐漸用力,疼得牙關相撞,控訴發:“你在我上裝定位,讓人時時刻刻盯著我,這是嗎?你考慮過我的嗎?你把我當豢養的寵,我就該對你恩戴德嗎?我已經足夠忍耐你了,你還要我你,你臉怎麼這麼大!”
空氣仿佛在霎那間凝結,傅硯清的虎口有一瞬松懈,似撞裂的冰巖。接著,他又反手攬住的腰,俯抱:“不是你想的那樣,如果你是因為手表和我生氣,我可以和你解釋。”
他像驟然失去支撐點的棚罩,將制得不過氣。喬寶蓓不明白他究竟為什麼要糾結這種事而不對其他問題解釋。為他不齒的行徑而氣憤,為他無底線的監視而發怒,究竟有什麼區別?
面頰的咸被他的吻拭,他頷首吻到邊,向下流連,如此輕低微。
喬寶蓓仿佛也沒了力氣,塌塌地陷在他懷里,面容滿是噴灑的氣息:“你放開我……”
“傅硯清你放開我……”
他死死不放手,著面頰,吻著耳畔,確保每個字都確鑿地送進耳中:“我是監視你,我可以向你承認。我知道這很不顧及你的私,但是我你,我是真的你,我想知道分居的日子你過得怎麼樣,但你很給我打過一通電話,發來一條消息。我知道你經常去酒莊喝酒,和你那些朋友打牌,我知道你對花藝馬繪畫不興趣,給我的是買下的畫,我知道在你眼里的我是迂腐無聊的,所以你寧愿和比我更年輕的男人趕海,我知道你和別人埋怨過我年老,我知道,我知道……”
無孔不地監視一言一行,病膏肓地收集所有,掉落的頭發,用過的穿戴甲,不要的換洗,他念,,,對抱有千萬種幻想,又逐次解構,深刻認識真實的。
是他的神,他千真萬確的,他怎麼會不?何故對他視而不見,又要棄若敝屣。
為什麼可以這麼狠心?
寶蓓,寶蓓……
聽著吃痛的聲音,他想放手又不肯放,像無家可歸的狗死咬著已經破爛的網球,怕垂涎的唾浸壞它,卻以獠牙狠狠含著。
喬寶蓓推他,擺著渾排斥:“松手……松開我……!”
滾燙的熱氣像洶涌的浪,將掀拍得不知方向。
不想聽,不想聽這些。
不明白他怎麼可以這樣?肆無忌憚地監視,還要冠以的名義,再在遮掩不住的況下毫不留地揭開傷疤。
襯的紐扣崩開了兩粒,傅硯清吻到的鎖骨,竭力托起雙,分開,穩穩嵌在腰側。半落不落,幾快沒了落定點,理智回籠,以掌拍打他的側臉,不斷推搡,拍到紅痕泛濫。
傅硯清凝矚不轉,邊涔著咬破的痕:“你告訴我,和我好好說,在我們相的日子里你對我不是沒有一丁點,對嗎?你騙我,瞞我,哪怕一開始是圖我可以給你安全,激我幫你把生父送牢里,但你還是愿意跟男友分手選擇我,做好在我面前演一輩子的準備。”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784 章

千億萌寶寵上天
五年前喬語蒙不顧一切的嫁給付千臣,最終以離婚收場,甚至被要求打掉屬於他們的孩子……五年後,喬語蒙帶著孩子回歸,付千臣卻又不肯放手了。喬予希:那啥,叔叔你做我爸比吧!付千臣:我覺得可以。喬語蒙:滾!
140.3萬字8 3276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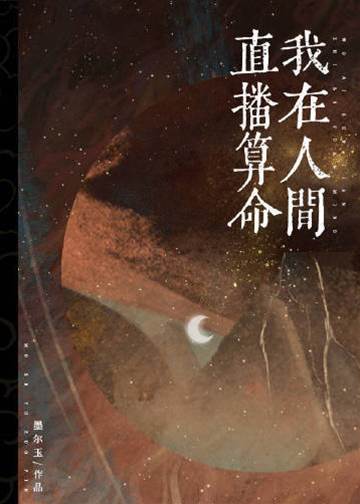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9642 -
完結1314 章

為躲姐夫騷擾,我閃婚豪門大佬
【先婚后愛+婚后日常+細水長流+甜寵+雙潔+1V1】 因為被姐夫騷擾,陸惜決定找個男朋友。 相親對象長得英俊,舉止優雅,陸惜很滿意。 男人說:“我家里催婚催得急,如果你愿意,我們就領證結婚。” 陸惜震驚的看著男人,“結、結婚?!可我們剛、剛見面啊,這有點太快了。” 男人的唇畔淺淺一勾,“戀愛,結婚,生子,我們只不過跳過第一個部分。 當晚姐夫又闖入房間,陸惜嚇壞了,立刻決定閃婚。 “江先生,我是陸惜,我想清楚了,我同意結婚,您現在有時間嗎?” 傅南洲看了一眼會議室的幾十個高層,濃眉一挑,“現在?” “嗯,現在,我有點急。”” 傅南洲忽然站起身,沉聲道:“會議暫停,我結個婚,盡快回來。” 陸惜火速領證,拿到結婚證才如遭雷擊,結結巴巴,“你、你叫傅南洲啊?” 傅南洲莞爾一笑,“是。” 陸惜后悔萬分,萬萬沒想到她竟然坐錯桌,認錯人,還閃婚了個老男人! 更讓人沒想到的是,閃婚老公竟然是自己的頂頭上司! 某日,陸惜又偷偷溜進總裁辦公室。 完美老公將她拉到腿上,熱吻粉唇。 “老公,別~有人會看到~” 傅南洲輕笑,“傅太太持證上崗,看見又如何?”
251萬字8 18063 -
完結276 章

夜夜難哄:京圈大佬很野很欲
未婚夫假死,跟閨蜜私奔。她一夜放縱,招惹了京圈叱咤風云的太子爺。 本以為完事后各不相干,卻不想對方竟然是自己未婚夫的堂哥! “除了床上,我不會讓你受一點委屈!” “那床下呢?” “床下你還是得叫我哥!” 從此他們開始了地下戀情。 直到她傳出婚訊,凌啟寒被拍到大雨中失控地將她抵在豪車上強吻。 “凌總,這熱搜要不要撤下來?” “砸錢掛著,掛到她愿意改嫁我為止!” 京圈人都說他凌啟寒不當人,竟然霸占堂弟的未婚妻。 凌啟寒囂張地回:我橫刀奪愛,你有意見?
49萬字8.33 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