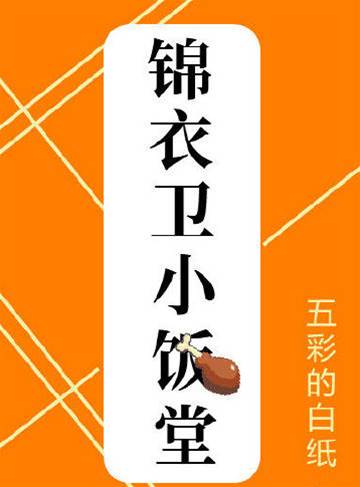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千嬌百寵》 第16頁
爐中的炭火燒得極旺,青煙吞吐,砸砸地冒火星兒。
太后放下手裡的玩意,回到暖塌上坐下,「這麼說,那丫頭瞧見紙團上的字了?怎麼樣,有打算麼?」
余嫆亦步亦趨地跟著,「現下還沒什麼靜,是個懂事的,知道把紙信兒燒了不留痕跡,只是膽子小了些,家出來的姑娘,刀子都沒過,哪裡敢殺人呢。不過,倒也不是沒有可能。天下苦戰久矣,西北之地尤甚,遙州府的姑娘平時耳濡目染的,大抵都是咱們陛下殺人如藨的輝事跡,找人吹吹耳旁風,說不準還真敢手。」
太后眸中冷掠過,「哀家本也沒指,試探試探罷了。」
余嫆給太后倒了杯茶,笑了笑說:「太后好謀算,送過去實乃一石三鳥之計,昨兒個陛下喝人的事兒,奴婢已經讓青霧悄悄往前朝後宮傳出去了,玉照宮人親眼所見作不得假,眼下後宮裡那些個婢子心都懸得高高的,生怕陛下瘋癲起來吃人呢。不過姜阮那丫頭倒還有幾分本事,青靈回來說,那丫頭昨兒個睡的龍床,今早起來,連汪順然都對畢恭畢敬的。」
Advertisement
太后面鄙夷之:「汪順然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誰不是畢恭畢敬?」
余嫆笑著應了,又聽太后疑道:「皇帝昨夜沒殺,怕不是心了?」
「這奴婢說不準,不過姜阮是奴婢親自去藏雪宮挑的人,陛下沒置,可見對您是十分的信賴,更不願駁您的面子。這麼多年來,您待他比待昭王殿外還要親厚,人人都看在眼裡,任誰也不敢置喙一句。」
「這麼說,這姜阮還是有幾分用的。」太后瞇眼,靠著繡丹山彩的錦枕,面容閒舒:「勾魂還是奪命,你且看著辦吧,別讓人瞧出端倪來,尤其太傅那頭,千萬莫要走風聲。」
余嫆垂首應了個是。正要退出大殿,太后忽然抬頭:「昭王近日在忙什麼?」
余嫆回道:「前兒北疆下了今年第一場雪,昭王與大司徒正商量著賑災減稅的事宜,去年北方連日大雪,凍死的人和家畜數以千計,如今北方百姓看到雪便人心惶惶,昭王殿下早日決斷,也能在百姓心中博個賢名。」
太后眉目舒展開來,緩緩笑道:「昭王爭氣,不枉哀家在後宮為他百般籌謀。」
Advertisement
余嫆退下後,太后獨自倚在榻上小憩。
佛龕中供奉著一座玉面朱的觀音像,裊裊青煙淡掃,出莊嚴慈和、普度眾生的味。
-
玉照宮。
汪順然調來兩名穩妥的宮伺候阮阮起居,梳妝過後,阮阮便隨兩人一同到偏殿用早膳。
眼下殿中空無一人,汪順然悄悄上了傅臻的手腕。
先後伺候兩位帝王,耳濡目染也學了一些醫,雖不如太醫院業有專攻,聞問切倒也得心應手,不至於遭人蒙蔽。
這一點,外人並不知曉。
誰知才一龍,床上的男人竟倏地睜眼,將汪順然嚇得一哆嗦,撒往後退了幾步,「陛下,您不是……」
不是說短時間醒不過來麼?
沒點心理素質,有時候還真承不住這種魔王突然甦醒的震慄。
他總能給人驚嚇。
有時候在殿裡說話,保不齊這位就醒了過來,被他聽去幾分胡話也不知道。
傅臻緩緩起,著床新搬來的被褥,冷冷掃一眼汪順然,扯了扯角:「你幹的好事?」
汪順然眉心一跳,趕忙撇清:「是太后的吩咐。」
Advertisement
見他神不虞,又滿臉堆笑道:「平衡乃天地萬之綱紀,奴才想著,多個姑娘在此,興許對陛下的子有好。」
傅臻冷哂:「你也學那郁從寬,睜眼說瞎話?」
汪順然躲開他的目,自然而然地甩鍋:「奴才該死,可這話是玄心大師說的,奴才只是照辦罷了。」
姜阮是否當真對傅臻有用,汪順然還不敢斷言,生怕昨日所見皆是自己的錯覺,只是見他似乎興致頗好,便換了個法子問:「陛下今日能醒,難不真是人的功勞?」
傅臻角冷冷勾起,「嗤」了一聲。
汪順然撓了撓頭。
傅臻神淡漠,想到昨夜子上和的佛香,心中困,也怔了片刻,「半夜看朕,今晨亦如此。」
汪順然仿佛沒聽懂,雙目瞪圓:「……啊?」
傅臻眸黑沉,語調卻平靜:「昨夜借著替朕拭汗,看了朕整整兩盞茶的功夫。」
他手垂下來,帶著幾分慵懶地倚在床邊,抬眸冷眼看著汪順然:「若不是犯了頭疾,眼皮子掀不開,朕一定將雙眼剜出來下酒。」
汪順然深以為然:「是,是。」
傅臻眸漆黑,眼底涌著躁鬱和嫌惡:「這般以下犯上,朕若還不醒,哪日被人殺了都不知道。」
說到這個,汪順然斂了斂神,「昨晚有人往殿裡傳消息,姜姑娘看過信便焚毀了。」
傅臻眉梢一挑,寒聲譏笑:「這麼快就出馬腳了?」
汪順然昨日見了阮阮,看得出心腸不壞,聽到這話也忍不住多一番:「姑娘是遙州府的千金,昨兒是頭一次進宮,太后的面還沒見著呢,只是余嫆倉促點過來伺候您的。」
傅臻手指輕敲著梨木床沿,「信上寫什麼?」
汪順然了鼻子,心道信上寫什麼,您還不清楚麼?
猜你喜歡
-
完結439 章

傳聞中的陳芊芊
母胎單身七流編劇陳小千嘔心瀝血寫了一部女尊題材大劇,原可順利開機,卻因為演員韓明星對劇本感情戲質疑過多而崩盤。憤懣難平發誓要證明自己能力的她,意外卡進了自己的劇本,變身東梁女國地位尊貴但惡評滿國的三公主。原本一個活不過三集 的小女配,為了活命開編劇副本,逆轉荒唐人生,在不懂套路的犬係世子韓爍和人設完美外貌滿分的太學院少傅裴恒之間,最終學會愛與成長。《傳聞中的陳芊芊》根據同名影視劇改編,作者棒棒冰。是趙露思、丁禹兮等主演的古裝愛情劇,由騰訊視頻全網獨播
78.1萬字8 11913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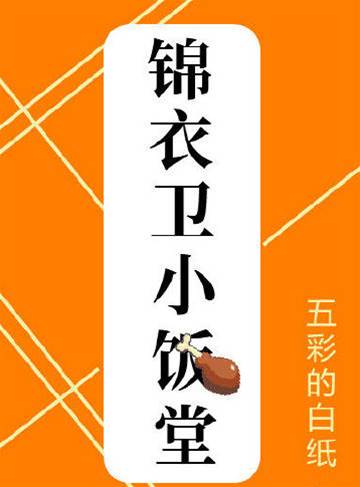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