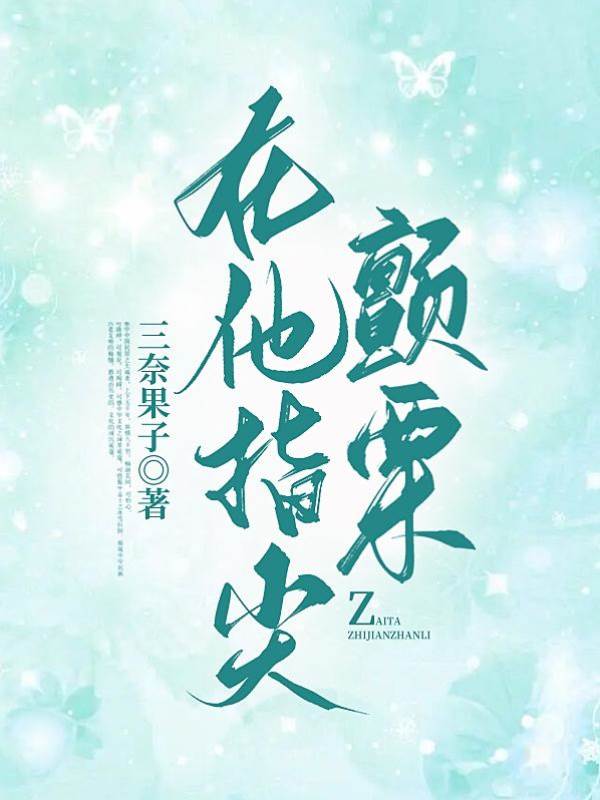《熱戀預告》 第97頁
太令人震驚了。
震驚到忘記呼吸,空白占據了大腦中的所有空間。
他們早在多年前便已經見過面。
初次相遇的地點還是從小生活到大的紀家。
此刻,紀知鳶只覺得世界如此之小,小到近乎荒誕。
連電視劇都不敢輕易編排的巧合,偏偏這樣上演在了的生命之中。
紀知鳶紅輕啟,怔怔地出幾個字。
“爺爺壽宴那天,你就聽過我彈鋼琴了?”
齊衍禮點頭。
紀知鳶又問:“之前怎麼沒有聽你提起過這件事?”
齊衍禮話音微滯,眼底掠過一不易察覺的慌。
他結微,頓難以啟齒。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做過在墻角聽這種不彩的事。”
“特別是,聽的對象還是你。”
紀知鳶不以為然地挑了挑眉,角忍不住上揚。
“承認吧。”
“你一定也很為我著迷吧。”
齊衍禮歪頭淺笑,語氣寵溺地應下,“是,我很為你著迷。”
“等等。”紀知鳶臉上的喜逐漸凝固,圓溜溜的杏眼中閃過一狐疑,上下打量著面前的男人,掰著手指小聲嘀咕,“爺爺六十大壽……那個時候我才……十……十歲?”
忽然間,瞳孔猛地收,像是被自己的推算結果驚到,聲音陡然拔高。
“所以你……你該不會從那時開始就心了吧?”
紀知鳶下意識地后退半步,雙手叉護在前,滿臉難以置信地說:“天吶,你……”
后面的話語還未及傾吐,便被齊衍禮熾熱的吻封緘于畔。
到懷中人終于安靜下來,他幾不可察地松了口氣,眼底掠過一縱容的笑意。
修長的手指輕輕抬起,在潔的額前不輕不重地敲了一記。
Advertisement
“這個小腦袋整天胡思想。”他的嗓音帶著幾分無奈,“我當時確實是心,不過不是你想的那種心,而是對你彈出來的鋼琴曲十分心,想要一直聽下去。”
齊衍禮繼續講述著往事。
“之后我申請了赴留學,在遠渡重洋繼續深造的期間,我很能有回國的機會。”
“原本以為我們緣分就此為止,我也在繁重的學業中漸漸忘記了這件事。”
“沒想到命運讓我們在異國他鄉的街頭重逢,再次聽見悉的樂聲,我才明白有些緣分從未真正結束。”
他的目在紀知鳶臉上短暫停留,聲音隨結的滾變得低沉。
“你也都看見了。”
“在之后的事,日記里面都寫了。”
紀知鳶眸幽深,眼底似有暗流涌,讓人辨不清此刻的緒。
是看了他記在日記里面的容。
不僅如此,還把日記中的主人公誤認了別人。
但是!這不是的錯!
不知道自己與齊衍禮的初遇,比想象中要早那麼多。
紀知鳶撅起,聲若蚊吶的咕噥:“誰能想到你說的人是我呀,我還以為是……”
話音戛然而止,慌忙地咬住下。
齊衍禮卻不肯就此作罷。
他狹長的眼眸微微瞇起,眼底掠過一危險的暗芒,慢條斯理地追問:“哦?那你以為是誰?”
刻意拖長的尾音在空氣中緩緩開,激得紀知鳶的小心臟一。
躲開他揶揄的視線,半天才說出來一個名字。
聲音很小,小到僅有自己能夠聽清楚。
“喬若宜。”
齊衍禮緩緩傾靠近,這三個字清晰地落耳畔。
他角不自覺勾起,最終低笑出聲。
沙啞的聲線里帶著磁,像是羽輕掃過耳廓,讓紀知鳶不自覺地攥雙手。
Advertisement
他說:“阿鳶,你是不是吃醋了?”
聽到這句話,紀知鳶的臉頰瞬間染上一抹緋紅。
吃醋?
確實是在吃醋。
可齊衍禮怎麼能直接點破的小心思呢?
不要面子的呀。
紀知鳶別過臉去,抿著一言不發。
齊衍禮瞧見這般態,心頭一,忍不住手輕的臉頰。
他指尖輕挑,纏了一縷的秀發,在指節間細細把玩,那發便如般繞指纏綿。
紀知鳶簡直被他鬧得沒了脾氣,索橫了心,眼波瀲滟地嗔道:“是。我就是在吃醋,我就是看不慣除了我之外,你還過另外一個人。”
哪怕是在未曾出現在他生命中時的青春悸。
哪怕告誡自己這些只是過去式,才是他的現在和未來。
紀知鳶仍能覺到心底翻涌的酸,像止不住的水。
聽完這句類似于真心出的話語后,齊衍禮眸中驟然迸發出熾熱的芒。
他猛地扣住人的雙肩,將擁懷中。修長的手臂如鐵箍般收攏,力道大得幾乎要將進膛。
紀知鳶的臉頰著齊衍禮的膛,那熾熱的溫度過料傳來。
耳邊響起一陣急促而有力的心跳聲,如同擂鼓般‘咚咚’作響,震得耳發。
下一秒,齊衍禮帶著難以抑制的激聲音從頭頂落下。
“阿鳶,我很高興。”
“你會為我吃醋。”
在上,終于不是單方面的付出了。
他也終于會到了被放在心上的滋味。
“我真的很高興。”
“阿鳶,我好高興啊。”
齊衍禮像極了一個得到心玩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呢喃著滿心雀躍。
如果凝神細聽,那歡喜的聲線里還藏著幾不可聞的哽咽。
Advertisement
紀知鳶輕輕回抱住他,掌心溫地過他的后背。
等待齊衍禮激的緒逐漸緩和,稍稍后退,在兩人之間留出一段恰到好的距離,大概一個拳頭的寬度。
既不失親近,又給予彼此足夠的空間。
紀知鳶斂去方才的似水,轉而擺出一副‘秋后算賬’的冷艷神。
“別高興得太早。”
“我還有些事沒有問完。”
“哦。”
齊衍禮低低應了一聲,局促地收回手,強下心底那想要將擁懷中的。
他抬起眼簾,猝不及防地跌眼中。
那雙含著水的眸子讓他呼吸一滯,心跳不自覺地了一拍。
還想問什麼?
齊衍禮捫心自問。
好像沒有了。
他埋藏在心底的都已全盤托出。
不對。
還有一件事。
令他于啟齒的事。
口下方,第二肋骨傳來約的鈍痛。
無端發燙,灼熱在皮下蔓延。
如同一種不容忽視的警示。
第71章 一直親到你缺氧……
“藍鉆項鏈是怎麼回事?”
“這是你專門在拍賣會上為我競拍下來的,并且日記中也出現過著四個字。”
紀知鳶微微蹙眉,不記得自己以前帶過藍鉆項鏈。
再者,向來不偏鉆石這類的珠寶,只是喜歡所有麗的東西罷了。
喜歡藍鉆的另有其人。
曾無意間聽見喬若宜和友人之間的談話。
‘太可惜了。拍品里有你喜歡的藍鉆,還是稀世罕見程度的。’
‘我記得你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用藍鉆做的飾品。’
‘齊家是不是也送過你一條藍鉆項鏈?’
紀知鳶一字不差地將
這番話復述給齊衍禮聽,末了又淡淡添上一句,“喜歡藍鉆項鏈的人是喬若宜,不是我。”
話音剛落,齊衍禮便急不可待地為自己辯解,神萬分急迫,仿佛稍慢半拍就會百口莫辯。
“我從來就不清楚喬若宜的喜好。”
“至于齊家送過什麼,我更是一無所知。”
齊衍禮說完,仍覺得這兩句話分量太輕,不足以取信于人。他干脆舉起右手,掌心朝外在額邊,擺出一副鄭重起誓的姿態。
“阿鳶,我和喬若宜清清白白,連點頭之都算不上。”他頓了頓,又補充道,“我甚至都沒有存的聯系方式。”
紀知鳶輕笑著握住男人懸在半空的手,指尖在他掌心輕輕一劃,眼波流轉,將對方繃的手指緩緩攏住。
“好了好了,我只是隨口一問,沒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或許眼睛會看到一些令人誤解的事,但心不會騙人。
紀知鳶能到齊衍禮對自己的。
“阿衍。”放聲線,眼睛一不地盯著他,“我還有最后一個問題。”
紀知鳶指尖過他的指節,在間流轉,細膩與礪撞。
某種久違的異樣悄然攀上心頭。
一個不可思議的猜測在腦海中漸漸形。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yanqing/08_b/bjYT1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68 章
重生後薄情傅少他又暖又撩
傅琛梟死了,死在一場早有預謀的車禍中。他的葬禮,傅家的人為他的遺產的分割鬧了個不歡而散,卻隻有一個人在他的墓碑前安安靜靜的流著眼淚,全程哭紅了眼。“傻子,小傻子……”傅琛梟呢喃著,他想安慰他,可是他的手卻隻能穿過他的肩膀。原來在他人生後最後一程,為他傷心,為他哭泣,甚至為他去死的,隻有那個整日裡跟在他屁股後頭卻被他忽視了的小傻子。他這一生手上太多血腥,他不奢望還能投胎成人。如果有來生,他願是一棵樹,一定要長在他的小傻子身邊,半截埋在泥土裡,根深葉茂,半截讓他依靠,為他遮風擋雨……重生護崽深情攻x軟萌傻乎乎受1v1你許我一世情深,我許你經年不負
27.8萬字8 27606 -
完結485 章

逃婚后,她闖入了大佬的天羅地網
一場逃婚,她從美若天仙的海城首富千金偽裝成了又土又醜的鄉巴佬。剛到京城的第一天,就招惹上了京城第一家族繼承人霍煜琛,那是一個今人聞風喪膽的男人,大家都稱他活閻王,做事六親不認,冷血無情、果敢狠絕。他為了氣自己的父親娶了她,整個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娶了個醜的,殊不知她卸下妝容後美若天仙。婚後的生活她過得‘水深火熱’。不僅每天要面對一個冰塊臉,還要時刻隱藏自己的身份,她每天都想著離婚,想著擺脫這個男人
84.8萬字8.18 112479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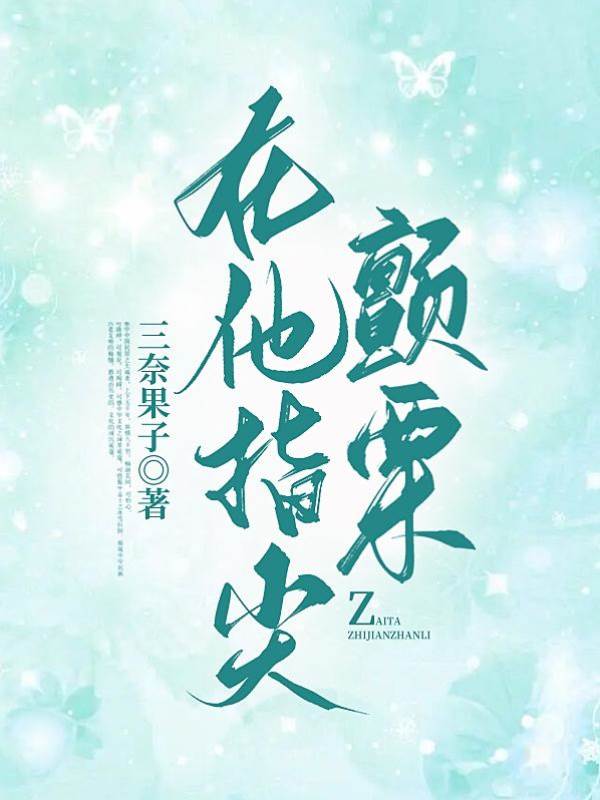
在他指尖顫栗
【美豔釣係旗袍美人VS清冷矜貴貧困大學生】【欲撩?甜寵?破鏡重圓?雙潔?暗戀?豪門世家】他們的開始,源於荷爾蒙與腎上腺素的激烈碰撞她看上他的臉,他需要她的錢他們之間,隻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蘇漾初見沈遇舟,是在京大開學典禮上,他作為學生代表正發表講話他一身白衫長褲、目若朗星、氣質清雅絕塵,似高山白雪,無人撼動驚鴻一瞥,她徹底淪陷人人說他是禁欲的高嶺之花,至今無人能摘下可蘇漾不信邪,費盡心思撩他,用他領帶跟他玩緊纏遊戲“沈會長,能跟你做個朋友嗎?”“蘇漾,”沈遇舟扣住她亂動的手,“你到底想幹什麽?”“想跟你談戀愛,更想跟你……”女人吻他泛紅的耳朵,“睡、覺。”都說京大學生會主席沈遇舟,性子清心冷欲,猶如天上月可這輪天上月,卻甘願淪為蘇漾的裙下之臣然而蘇漾卻突然消失了多年後,他成為醫學界的傳奇。再見到她時,他目光冷然:“蘇漾,你還知道回來?”房門落鎖,男人扯掉領帶,摘下腕表“不是喜歡跟我玩嗎?”他親吻她,偏執且病態,“再跟我玩一次。”“沈遇舟,對不起。”男人所有不甘和怨恨,在這一刻,潰不成軍他拉住她,眼眶發紅,眼裏盡是卑微:“別走……”沈遇舟明白,他是被困在蘇漾掌中囚徒,無法逃離,也甘之如飴
20.8萬字8 2982 -
完結174 章

那晚之后,宋警官別來無恙
【雙潔x追妻x暗戀x久別重逢】* 宋知年看著發呆的林桑初,不免走近她,“林醫生,這是睡不著嗎?” 林桑初回過神來,“沒......沒有,這就睡了。” 林桑初支支吾吾地說完剛要上床,余震又再一次襲來。 宋知年下意識地將她護在身下,他們之間近的,林桑初可以很清晰地聞到他身上的泥土味,甚至還能聞到一絲血腥味。 * “宋知年......我不需要你負責的。你也不需要有什麼負罪感。”林桑初忽然伸出雙手,撫上了宋知年的臉頰,踮起腳尖雙目盡量與他平視。 宋知年忽然就想起了那一枚小小的平安符,他帶去部隊后,被戰友發現,并拿來取笑了他好一陣。 說他明明有意中人,卻死鴨子嘴硬不肯承認。 宋知年壓抑了許久的欲望終是戰勝了自己大部分的理智,他反客為主,伸出右手撫上林桑初的后腦勺,低下頭去親她。 * 夜晚,宋知年撫摸著林桑初后背那條細小的疤痕時,懊悔地親了上去。繾綣間,宋知年呢喃道:“桑初......以后我只有你一個,再不會拋下你。”
31萬字8 156 -
完結95 章

當我拿錯三次貓之後
黎霧三天前帶回家一隻銀漸層,但工作太忙只能將貓寄放寵物店。 好巧不巧,寵物店還有一隻總是託管的銀漸層。 於是—— 貓放寵物店了,拿錯貓了。 貓放寵物店了,拿錯貓了。 ...... 第三次,對方忍無可忍,找到了黎霧家門口,並拽下了自己的口罩。 年輕的男人拉口罩的手袖口往下,露出一截清瘦的腕骨。 黎霧呆愣愣地看着他。 某乎求助:當我拿錯三次貓之後,發現這貓的主人是我喜歡的那個頂流——OoO 半月後跟帖:這貓好像很喜歡我,賴着不走了——O-O 再兩個月:它的主人也不走了——T-T 起初,黎霧以爲程清覺是冷漠厭世的高冷頂流。 後來才發現——她看別的男人時,他會撐着生病的身體,從後把下巴搭在她的肩膀處,用滾燙的體溫把她一起燙熱,啞啞聲線:“只許看着我。” 之後會再問“今晚還留下嗎?” 黎霧深深吸氣,對上他的目光,眨了眨眼,想到昨晚半夜被弄溼了大片的牀單。 後來她發現,他是一隻有病的粘人大狗。
27.4萬字8 1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