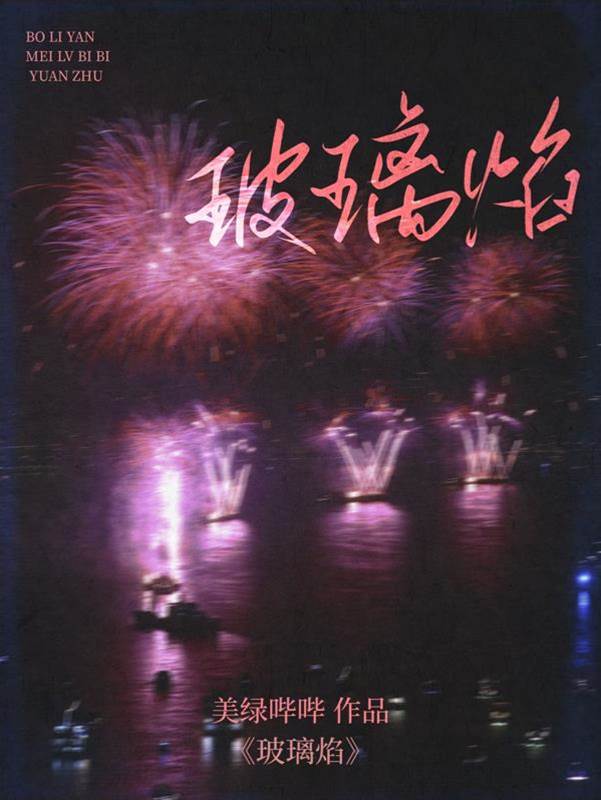《乖乖,你哄我一下》 第1卷 第9章 情趣?忽然之間情的哪門子趣?
一班教室后門,兩名生拉門框,探頭探腦往里面瞧。
看一眼,回來;看一眼,又回來。
如此循環往復。
“不行不行,我還是不敢。”扎低馬尾的生連退兩步,問右邊的同伴,“你確定看清楚了?他當時真收了?”
“保真!就昨天下午,籃球場上。”
昨天下午……
籃球場……
江霧眼睛一瞇。
這時間、這地點,有些悉哦。
接著,那名同伴用手指臉上架的眼鏡。
“你要知道,為了看清一個東西我可是花了大價錢,是真金白銀的親眼目睹!”
聽了這段話,低馬尾生反倒出“我更不敢信了”的表。
配眼鏡才能看清的視力,好得到哪里去?
同伴掃一眼時間,著急地催促:“別猶豫了,沒什麼大不了的。最終結果無非像樹葉一樣簡單——”
“——不是綠了就是黃了。”
低馬尾生角搐:我謝謝你哦。
走廊的另一側,江霧同志被這句話逗笑。出于禮貌,自覺舉起文件擋了下。
可惜有事沒干,不能逗留太久,沒一會便抬腳離開。
誰也沒注意到,太照下反的玻璃窗后,一雙黑眸直勾勾地盯著——從始至終。
“硯哥,你覺得我說的對不對。”
Advertisement
無人搭理。
“問你話呢,怎麼不回答?”
等了老半天,沒收到回應的路緒扭頭,撞見傅池硯正偏頭對著窗戶。
“硯哥?傅池硯?”
路緒腦袋湊近,跟著一起往外面瞅,“在看啥呢,讓你如此迷。”
傅池硯收了目,面不改撒了個謊,“一只傻鳥。”
“傻鳥?”
路緒又瞧了瞧,走廊上除了兩位互相推搡的生,沒看到傅池硯提到的鳥。
“它干什麼了,你居然說人家傻。”
傅池硯回想剛才看見的一幕。
抱著一疊文件的江霧出現在走廊,不知聽見什麼,沒忍住笑漪輕牽。
笑意浸染的眼眸明亮,紅上揚勾出弧度,整個人變得生起來,宛如春花般明耀眼。
晨傾瀉,仿佛在發。
傅池硯收回思緒,勾了勾,“沒什麼,就自己在那傻笑。”
路緒:“?”
鳥?笑?
還特麼在傻笑?
怎麼聽起來骨悚然的。
“你是不是最近幾天沒睡好啊,出現幻覺了?”路緒了兩條胳膊,“這世上有會笑的鳥?我怎麼不知道。它長啥樣,你給形容一下,我回去搜搜看到底是什麼鳥。”
傅池硯剜了他一眼,“你是好奇寶寶嗎?對什麼都好奇。”
“也沒吧。”路緒很認真想了想,才說:“好像只有和你扯上關系的事,我才會到好奇……”
Advertisement
沒等說完,傅池硯神寡淡,干脆利落吐出三個字:
“閉。”
“滾。”
被打斷的路緒:“……?”
不是,又哪得罪了?
后方,一直沉默的沈商瑾單手撐下,另一只手在桌上輕輕點了點,將發生的一切盡收眼底。
他饒有興趣地彎,探出手,拍了拍一臉困,還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的路緒。
“別問,這是一種趣。”
“? ? ?”路緒回頭看沈商瑾。
他沒聽懂,準備追問這句話什麼意思,傅池硯跟著回頭。
“你也閉。”
“OK。”沈商瑾點頭,臉上笑意未減,語調懶懶散散,“我閉,您別惱就行。”
“嘖。”路緒不耐煩地抓了把頭發,目在兩人之間流轉。
什麼跟什麼,說的什麼鬼啊。
哇塞,現在說話都流行加了?
趣?
忽然之間的哪門子趣?
他特別想問沈商瑾那句話的意思,奈何邊杵了位冷氣制造機,只能作罷。
不知道為什麼,總覺一晚上沒見的傅池硯有點不對勁。
就像是……有什麼事瞞著他們一樣。
……
江霧踏進辦公室,里面坐著好幾位老師。
每張桌上立有名牌,標了姓名和科目。
江霧很快找到一班班主任——桑偉國老師。
一班和二班科任老師是同一批,兩班消息互相流通。
Advertisement
桑老師知道江霧,對這位轉校生很興趣,于是多聊了幾句。
等走出辦公室,上課鈴響已經是五分鐘前的事。
離開前班長提過一,第一節是班主任的課,所以并不著急。
上課時間走廊上空無一人,安靜到可以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前不久還不風的一班,眼下門窗全部大敞。
走廊左側,沒了窗戶的玻璃遮擋,傅池硯那張臉毫無遮擋地暴在眼前。
余瞥到的江霧心尖一跳,不控制地朝他去。
利落的黑發垂落,微微遮住眉宇,隨風小幅度擺。眼睫纖長、高鼻梁、眼尾深長……
松散隨意覆在后頸上的手,五指修長,骨節清晰分明。
平心而論,確實帥人一臉。
就是太拽,喜歡冷臉。
還有——
江霧越過敞開的窗戶,朝講臺看一眼,又回到他上。
眼底出幾分難以置信。
上課鈴早八百年前響完,班上同學正襟危坐認真聽講。
這位哥居然堂而皇之埋頭睡覺?
老師本人正站在講臺上,盡職盡責且聲并茂上著課。
這位哥居然桌上連本書都沒有?
但凡手機在邊,真想拍下這一幕發給許姨。
該不會真是砸錢進的一班吧。
果然,一切都是有跡可循的。
江霧嘆氣加搖頭,一臉“失”地離開了。
一班的講臺上,英語老師不久前拋了一個問題,隨機喊人回答。
除了數人已經想好答案,其他人紛紛垂下腦袋避開對視。
同樣不想被點名的路緒默默扭頭,將臉朝向窗戶。
也正因這一轉,湊巧撞見一道離開的背影。
“哐當。”
安靜的教室發出一道響聲,靜不大,但足夠引起他人注意。
英語老師聞聲掃視,鎖定手忙腳穩住自己的路緒。
角一揚,對這邊說:“看來路緒同學已經有答案,迫不及待想起來回答問題。OK,就你了。”
危機得以解除,周圍人如釋重負呼了口氣,激的目四面八方集中過來。
路緒一臉黑線。
我可去你的,哪只眼睛看出我迫不及待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88 章
七零嬌女有空間
花朝大夢一場,帶著空間重生了! 這時候,她才十六歲,還是個嬌嬌俏俏的小姑娘,二哥沒有過失傷人致死,父母也都好好地……最重要的是,她還擁有一個健全又幸福的家! 撥亂反正重活一世,她腳踹渣男,拳打白蓮,護家人,踩極品,還反手捉了一個寬肩窄臀腰力好的小哥哥,利用空間一起玩轉七零,混得風生水起……
105.7萬字8 50643 -
完結552 章

全娛樂圈都在等影后打臉
雲城第一名媛葉傾城重生了! 從此,娛樂圈多了個叫蘇淺的巨星。 從娛樂圈新人到影后,她一路平步青雲,所謂人紅是非多,各種撕逼黑料接踵而至。 蘇淺冷笑! 她最擅長的就是打臉! 越黑越紅,終有一天,她另外一重身份曝光,再次重回名流圈。 看她如何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跪著讓他們唱征服!
97.1萬字8 17046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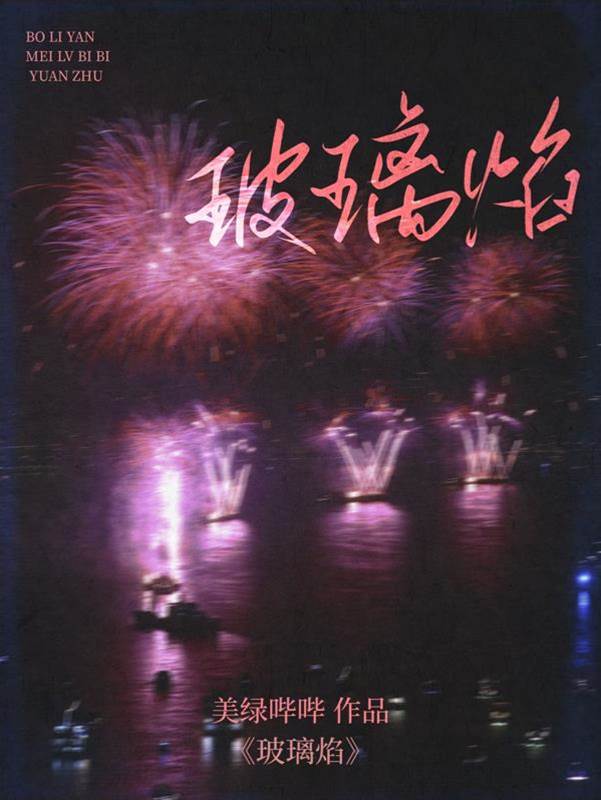
玻璃焰
[已簽約實體待上市]【天生壞種x清冷校花】【大學校園、男追女、協議情侶、強製愛、破鏡重圓】黎幸在整個西京大學都很有名。高考狀元,夠美,夠窮。這樣的人,外貌不是恩賜,是原罪。樓崇,出生即登上金字塔最頂層的存在優越家世,頂級皮囊但卻是個十足十的人渣。——這樣兩個毫無交集的人,某天卻被人撞見樓崇的阿斯頓馬丁車內黎幸被單手抱起跨坐在腿上,後背抵著方向盤車窗光影交錯,男人冷白精致的側臉清晰可見,扣著她的手腕,親自教她怎麼扯開自己的領結。——“協議女友,知道什麼意思嗎?”“意思是牽手,接吻,擁抱,上床。”“以及,愛上我。”“一步不能少。”——“玻璃焰,玻璃高溫產生的火焰,銀藍色,很美。”
25.7萬字8 14204 -
連載274 章

前妻太難追,偏執總裁他步步緊逼
【男主偏執病嬌 女主清冷美人 強取豪奪追妻 1v1雙潔 HE】五年婚姻,陸玥隱藏起自己的本性,乖巧溫順,取悅著他的一切。可圈內誰人不知,傅宸在外有個寵上天的白月光,為她揮金如土,就算是天上的星也給她摘下來。而對於陸玥,他覺得,她性子溫順,可以永遠掌控在手心。直到某天,她一紙離婚協議甩給他,轉身走人,與新歡站在商界巔峰,並肩而立。可在她一回頭,卻看見菩提樹下,傅宸的臉。“想離婚?”他一身純黑西裝,矜貴無比,淡淡道:“做夢。”
30萬字8 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