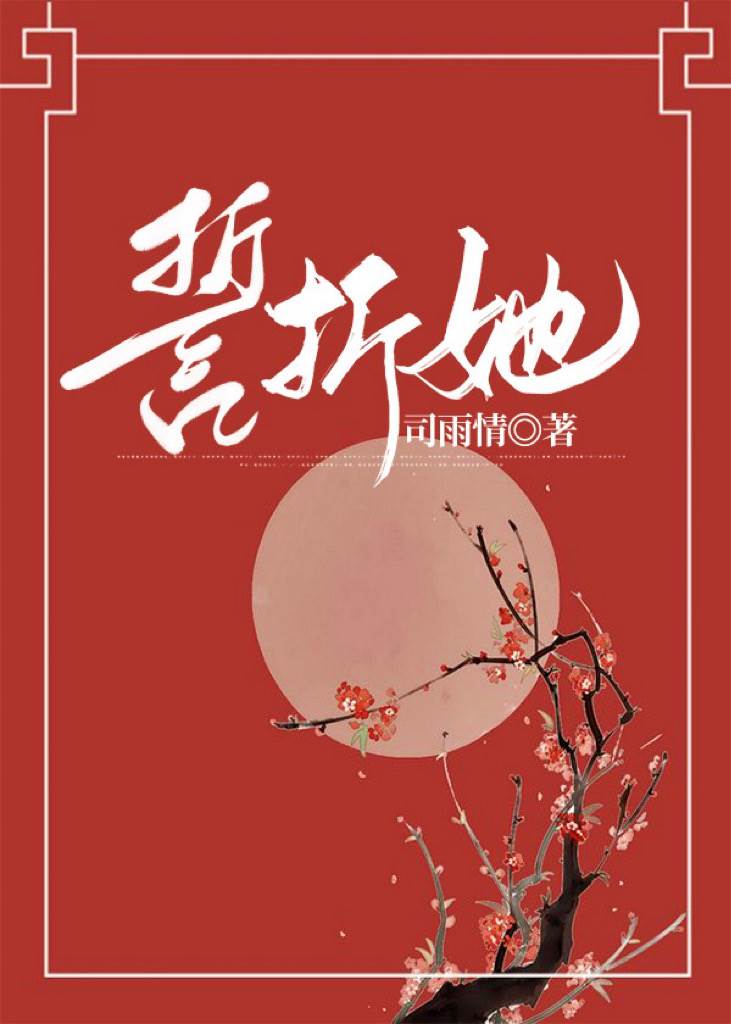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頂級偏愛!陛下輕點寵》 第1卷 第57章 將崔寶珠除族
崔仁貴在京中為多年,自詡人脈廣博,平日里稱兄道弟,推杯換盞的同僚故舊,也不在數。
他想著,王家這樁事,雖則棘手,但總能尋到幾個肯出力,或是肯指點迷津的人。
他接連拜訪了好幾平日里自以為匪淺的員府邸。
有的是避而不見,推說公事繁忙。
有的倒是見了他,只是聽他一開口,便顧左右而言他,眼神躲閃,生怕沾染上半分。
更有甚者,先前還與他把酒言歡,稱兄道弟,此刻見了,那眼神卻像是看什麼瘟神一般,唯恐避之不及。
誰也不敢拿自己的家命,去為一個商賈,去為一個前途未卜的崔家,冒這樣的風險。
他們看他的眼神,都變了。
仿佛他崔仁貴,已經是個將死之人。
崔仁貴奔波了大半日,口干舌燥,心力瘁。
馬車在崔府門前停下。
他掀開車簾,扶著小廝的手,巍巍地走下馬車,徑直往和善堂去了。
和善堂里,崔老夫人正歪在榻上,由張嬤嬤替捶著。
劉湘君和崔雪賦侍立在一旁,屋的氣氛,已不復往日的輕松。
崔仁貴一腳踏進門檻,崔老夫人便猛地坐直了子。
“如何了?”
劉湘君和崔雪賦也齊齊向他,眼中帶著探詢與不安。
崔仁貴走到屋子中央,子晃了晃,險些站立不穩。
Advertisement
“沒……沒人肯幫忙。”
“平日里那些稱兄道弟的,如今……如今都像是躲瘟神一般躲著我。”
“他們說,王家這事,是通了天的案子,誰沾上誰倒霉。”
“譏諷朝政,影圣上……這罪名,太大了,太大了!”
他一屁跌坐在椅子上。
“完了……咱們崔家,怕是也要完了!”
崔老夫人聽了這話,只覺得眼前一黑,子往后一仰,險些暈厥過去。
“老夫人!”張嬤嬤和劉湘君連忙上前扶住。
“母親!”崔仁貴也驚呼一聲,慌忙起。
崔老夫人緩過一口氣,淚水便像斷了線的珠子一般滾落下來。
“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啊!”
“好端端的,怎麼就招惹上這等禍事!”
“那王家,就是個掃把星!是來禍害我們崔家的!”
捶著口,哭天搶地。
劉湘君看著崔仁貴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心中也是一片冰涼。
崔雪賦站在一旁,臉也有些發白。
前世也看過不史書,自然明白“譏諷朝政,影圣上”這八個字的分量。
那意味著,滿門抄斬,株連九族。
好不容易才有了今日的局面,眼看著就要攀上靖國公府這棵大樹,難道就要因為一個不相干的王家,全都化為泡影?
崔仁貴看著哭泣的老母,又看了看面慘白的妻,心中更是焦躁如焚。
Advertisement
他猛地抬起頭,目落在劉湘君上,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救命稻草。
“湘君,你……侯府那邊……能不能……”
劉湘君聞言,苦笑一聲,眼底閃過一悲涼。
“老爺,您是知道的,妾不過是個庶。”
“在侯府里,向來是人微言輕,說不上話的。”
“更何況,這等牽連家命的大事,侯府……侯府又豈會為了我這個嫁出去的庶,去冒這樣的風險?”
“他們不落井下石,便已經是天大的恩了。”
崔仁貴聽了,臉上最后一也褪盡了。
是啊……怎麼可能。
他頹然地垂下頭,目又不由自主地轉向崔雪賦。
雪兒……雪兒與靖國公府的小公爺……
這個念頭剛一冒出來,他便自己先打了個寒。
荒唐!簡直是荒唐至極!
他這是病急投醫,昏了頭了!
小公爺是什麼份?會為了崔家,去這等潑天大案?
更何況,雪兒與小公爺之間,八字還沒一撇呢!
崔雪賦一直垂著眼眸,安靜地聽著。
忽然開口道:“祖母,父親。”
崔老夫人和崔仁貴都停了下來,看向。
“依孫看,眼下最要的,是如何撇清咱們崔家與王家的干系。”
“那王家犯的是謀逆大罪,咱們崔家,可不能被他們拖下水。”
Advertisement
崔老夫人聞言,急忙問道:“雪兒,你……你有什麼法子?”
崔雪賦淡淡道:“王家出事,皆因那批瓷。”
“而王家與咱們崔家唯一的牽連,便是大姐姐。”
“只要咱們與大姐姐斷絕了關系,對外宣稱,崔寶珠早已不是我崔家之人,那王家之事,自然也就與咱們崔家無涉了。”
“什麼?”崔仁貴和劉湘君都吃了一驚。
與崔寶珠斷絕關系?
這……這如何使得?
崔老夫人卻是眼睛一亮。
“對!對!雪兒說得有理!”
“那崔寶珠,就是個不祥之人!留在府里,早晚是個禍害!”
“如今正好,將逐出家門,與斷絕一切往來!”
“如此一來,王家的罪孽,便與我們崔家再無干系了!”
崔仁貴皺著眉頭,遲疑道:“母親,這事沒那麼簡單!”
“如今這風口浪尖上,咱們崔家若是急吼吼地跟寶珠斷了關系……”
“這……這外頭的人,會怎麼看咱們?”
“他們都會說,咱們崔家是為了避禍,連親骨都不要了!”
“日后,兒子在場上,那些同僚們,又會如何看待兒子?”
他越說,聲音越低,臉上也火辣辣的。
這種卸磨殺驢,過河拆橋的事兒,傳揚出去,他崔仁貴的聲,還要不要了?
崔老夫人聞言,卻是重重一哼。
“聲?聲能當飯吃,還是能保命?”
“如今是保命要!旁的,都顧不得了!”
崔仁貴依舊面帶愁容,搖了搖頭。
“母親,就算咱們單方面宣稱與寶珠斷絕了關系,可……可上頭,能認嗎?”
“這宗法禮教擺在那兒,父關系,豈是說斷就能斷的?”
“萬一朝廷追究下來,咱們這般做,只怕是蓋彌彰,反而更惹人懷疑。”
崔雪賦又道:“父親,兒的意思是,這斷親,自然不能只是口頭說說。”
“咱們得做得真切些,做得讓所有人都相信,崔寶珠,與我崔家,再無半分瓜葛。”
“如何做得真切?”崔老夫人急忙問道。
崔雪賦抬起眼,目在崔老夫人和崔仁貴臉上一掃而過,緩緩道:“一,將崔寶珠從族譜中除名。”
“二,昭告天下,崔寶珠品行不端,忤逆不孝,自今日起,逐出崔家,從此恩斷義絕,死生不復相見。”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農家酒娘:天上掉下個傻王爺
對于分家涼七完全沒在怕的,只要記得以后不要來抱大腿就好!只不過從天上掉下來的‘傻子’,卻叫涼七犯了難……“娘子,我餓了。”“餓著!”“娘子,我冷了。”“滾開!”突然的壁咚……“娘子,以后本王保護你!”不是傻了麼,難道是裝的【某女紅著臉心想】…
77.7萬字8 98913 -
完結199 章

新婚夜,我被冷冰冰的王爺讀心了
王妃一心守活寡 【貪生怕死小撩精vs口嫌體正戀愛腦男主】喬樂歌穿進自己的小說中,即將嫁給暴戾王爺,然后雙雙喜提短命便當。喬樂歌:?棺材板是絕對不能躺的,她直接化身綠茶小撩精,一心一意抱大腿茍命,等短命王爺去世后繼承遺產當富寡婦。——喬樂歌:“為王爺癡,為王…
30.8萬字8 22250 -
完結497 章

貴妃太野太茶!皇帝要不換個寵?
穿乞丐都比穿后宮好,沈卿對自己的身份絕望,女主出場還有兩年,她是男主后宮里位分最低的,家里父親不給力,手里沒錢沒實力,除了等皇帝寵愛好像也沒出路,而且還長了張招人的臉,爭吧,她沒資本,不爭吧,就是個被欺負的命,要不咸魚兩年等女主進宮幫她兩把確保自己能茍到皇帝掛?這麼一想似乎是個好主意,但是萬萬沒想到女主沒進宮呢,她就成了皇帝身邊最得寵的妃嬪了,emmmm這怎麼辦?她還能茍嗎?
94.1萬字8 44520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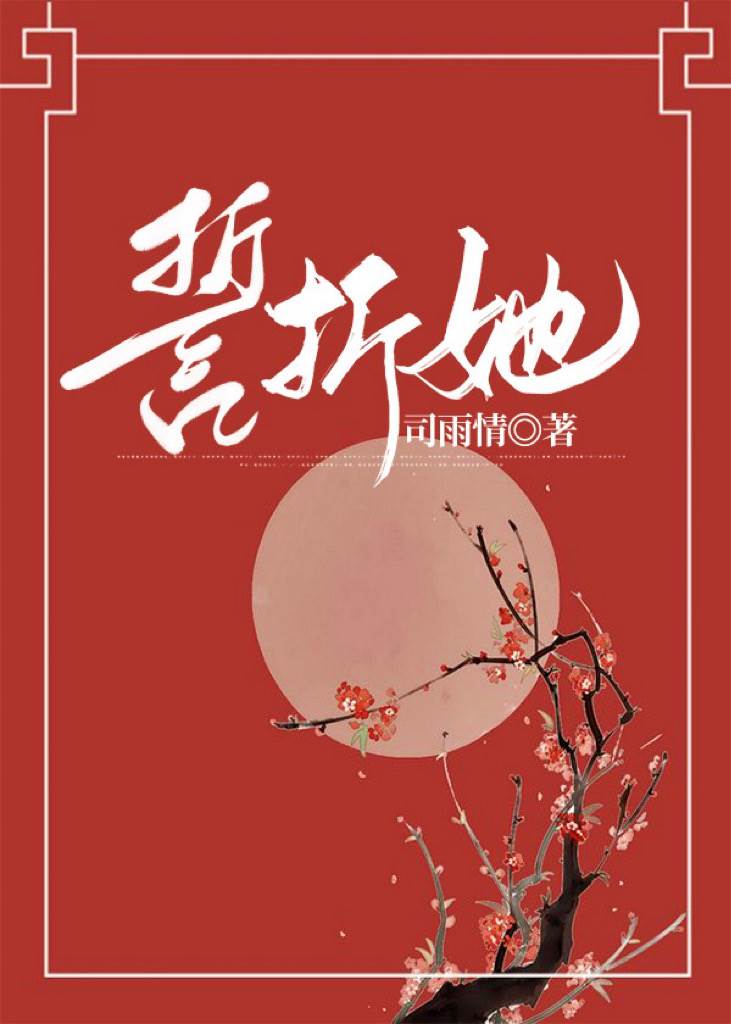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75 章

嫁給未婚夫的兄長
謝珈寧初見戚聞淵是在大婚那日。 她是江寧織造幺女,生在煙柳繁華地,自幼炊金饌玉,養得一身嬌貴。 及笄那年,應約北上,與指腹爲婚的永寧侯府三公子成親。 到了大婚的日子,未婚夫婿卻沒了蹤影! 珈寧一身織金紅衣,聽着賓客的低語聲,生出三分鬱氣。 在江南時,她何曾受過這樣的委屈? 正想說聲不嫁了打道回府,卻見一位神清骨秀的青年策馬而來,語氣平淡:“夫人,請。” – 永寧侯世子戚聞淵溫潤端方、玉質金相,只可惜他無心風月,惹得京中不知多少少女扼腕嘆息。 他那幼弟風流頑劣,迎親前日拋下新婦負氣出走。 戚聞淵道婚約只是戚謝兩家,並未言明究竟是戚家哪一位兒子,旋即放下公事,前去迎親。 起初,戚聞淵只是不想與謝家結親變結仇,想着自己總是要成婚的,倒不如娶謝珈寧。 至於婚後,他會給她足夠的體面,卻也僅此而已。 情愛那般飄渺無依的東西,他並未放在心上。 後來,在逶迤的江南煙雨裏,戚聞淵撞見了一雙盈盈的眸。 像是一滴水,落入無波的古井之中,盪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 戚聞泓在外野了許久,聽聞自己的婚約已落到兄長頭上,便收拾好行囊,回了永寧侯府。 繞過連廊,卻見羣花之後有一驕矜少女,高髻濃鬢,脣若夏櫻。 她朝着戚聞泓的方向粲然一笑。 眸中似有明珠萬千。 未幾,少女翩然行至他身前。 戚聞泓剛想開口,眼前卻掠過一個紫袍男子。 只見戚聞淵伸手幫少女理了理衣襟與袖口,順勢握住少女的指尖,將她拉至身後。 復又望向戚聞泓,冷聲道:“叫嫂嫂。”
18.2萬字8 57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