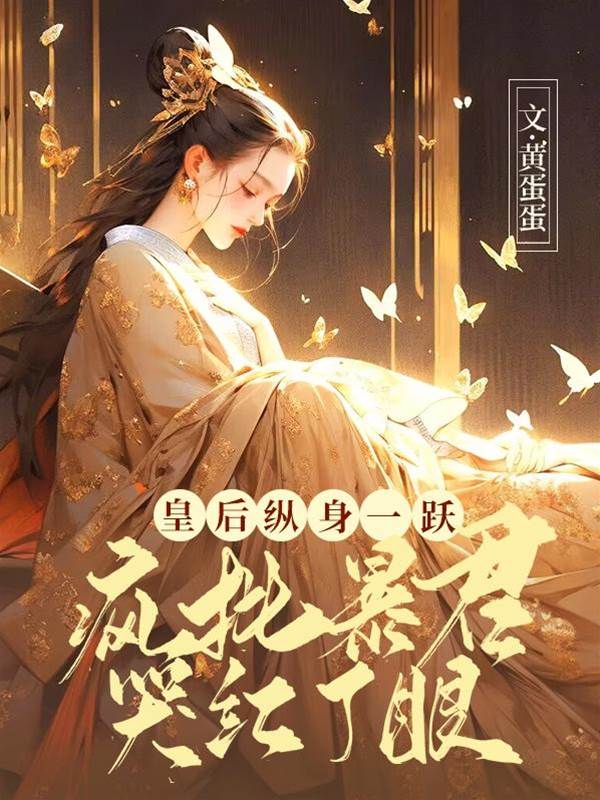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和離前夜,她重生回了出嫁前》 第161章 被劫之事(2)
卻說寧芙在聽了男子這句“我缺人”的話后,倒是有那麼一瞬,懷疑這是宗肆同調。
因著慕容的事,對他的喜好是持懷疑態度的,他似乎喜歡這種匿的忌。
只是在男人說出那句“你若是同意跟我睡了,我就放你一馬”后,便否認了這個想法。
宗肆從不直接如此低俗的提及男之事。
他雖會想,可不會要求同他睡覺,從不在這事上脅迫君。
孟澤見似乎只是沉默,并無半分害怕,眼下的寧四姑娘,冷靜得很,一時不由挑眉道:“你愿意”
眼下寧芙不知他是誰,若是敢說愿意,他也定然會冷臉,他接不了如此輕浮的寧芙,哪怕是為了自保。
寧芙沉思片刻,勸他道:“你若是想婚,不如好好去追求一位子。且世上不乏比我好看的子,你縱然強迫了我,我也會以死明志,當不了你的人。”
明面上,還是得有子的桀驁的,但為了失去死,這等并非是錯之事,不認為值當。
男子好,憑什麼子去死呢,是吧
“比你還的子有誰”男人道。
寧芙自然不能真說出其他君來,否則指不定給旁人招致危險,是以胡編造道:“陸府的陸蘭,還有雪姬,姿在京中都是有名的。”
孟澤倒覺得有幾分有趣,這種境地下,還能面不改的胡謅。
今日,只要他要了的子,之后又以救世主的份,出現在面前,表現出對的關心和心疼,甚至為了的名聲,愿意告訴外人,是無意中失與自己。
這般即便是敬文帝賜婚,可事既然已發生,便也只能如此。
至于自己救,也尋好了緣由,自己找衛霄談完事,正好得知了寧芙失蹤的消息,又正好見到寧芙的馬車離開,無意間留意了方向,是以能那般快找到。
Advertisement
如此一來,會激自己,寧真遠也會激自己,自己不但能娶到寧芙,對國公府也有恩,便是一舉兩得之事。
想到這,孟澤便不再耽誤,手去扯寧芙的領。
寧芙被綁著,卻是連掙扎也掙扎不了。
男人的手,及口時,一屈辱涌來,寧芙有些發抖,卻是冷靜道:“若我給你一萬兩黃金呢”
男人卻是毫不在意,手一撕,那領散開來。
寧芙白的鎖骨出現在了男人眼前,俏的脯,雖大部分藏于襟之下,可那一條淺淺的壑,還是讓孟澤在心中暗罵了聲。
妖!
如若不是走到了這一步,孟澤倒真不想在這要了,如此人,該在六皇子府,好生憐惜才是。
寧芙眼眶潤,倒不是害怕,是屈辱,是恨,閉上眼,將眼淚死死憋住,心中亦有了個猜測:尋常人劫,在一萬兩黃金之下,必然會蠢蠢,可這人卻是半點停頓也無,分明是這萬兩黃金,不足以讓他驚訝。
這人并非是普通人。
這細節,騙不了人。
而大燕之中,尋常人誰會去得罪寧國公府,便是有恩怨,有政治目的,也未必會對一個君如此。
寧芙想到了孟澤。
想到了上一世,他對自己勢在必得、帶著侵略的眼神,想到了他想強要了自己的模樣,想到了他的威利。
這一瞬,不由渾發涼,如置冰窖之中。
然后又想到了宗肆。
孟澤對宗肆,如今依舊是忌憚的,誰會愿意要一個人,連江山社稷也不要了何況上一世,自己與宗肆親之后,孟澤對自己,的確收斂了。
如今只有破罐子破摔了,是孟澤,遠比是尋常劫匪,要更讓心生張,如若孟澤一旦得到了,敬文帝還能怪自己唯一能立儲的兒子
Advertisement
恐怕只會瞞下這件事,而將自己送與孟澤,至多是給國公府一些補償。
敬文帝雖看重陸行之,也極在意重臣的看法,可事若有了比較,在意也無濟于事,有何事能比保住孟澤重要
是以在男人徹底拉下寧芙的里時,忍住聲音中的抖道:“你若了我,宣王府世子,是不會放過你的。”
也未點明自己的猜測,在這時若自己猜到孟澤,絕不是明智之舉。
孟澤猛地一頓,冷冷道:“什麼意思”
“宣王府世子,對我也有幾分心思,他對我是勢在必得,若知曉我被人占了去,不會放過你的。”寧芙道。
孟澤的息聲重了些,停下了作。
他卻想到了寧國公夫人生辰那日,宗肆所說那句,國公府婿,是誰,還不一定。
原先他還以為宗肆是向著自己。
卻是沒想到他也在打寧芙的主意。
孟澤幾乎忍不住地在心中冷笑了一聲,好一個宗肆,表現得不聲不響。
但,這足夠讓他生出退意。
自己想要寧芙,本就是為了國公府的支持,拿下晉王手中的兵權,要是得罪了宣王府,于自己而言,那便是得不償失了。
因為寧芙,與宗肆針鋒相對,并非是明智之舉。
不過孟澤卻也想到了讓自己舒心的一點,寧芙可能是被宗肆脅迫,才不敢與自己走的太近的。
怕宗肆,有可原。
正想著,忽聽外邊有一陣幾不可察覺的聲音傳來,他不由警覺幾分,下一瞬,一人破門而,劍朝他刺來。
來人不是宗肆又是誰
孟澤卻未見過他戾氣這般重的模樣,鷙沉戾,那劍分明是殺招。
他心下一驚,那劍便刺他口,孟澤暗不妙,在那劍尚未深時,抬手將劍刺向寧芙,宗肆果然回劍,手格擋。
Advertisement
與他僵持并非長久之計,孟澤手拉下屋里的機關,火勢突起,若是宗肆追自己不顧寧芙,寧芙便會與這屋里的證據一起,在這場火中,燒得干干凈凈。
孟澤趁機離開了。
宗肆卻顧及不上,轉將大氅下,披在寧芙上,將抱起,往屋外走去。
寧芙聞到了那陣悉的梔子花味。
那懸著的心,便放了下來。
那因盡屈辱,而憋回去的眼淚,也忍不住落了下來。
未說話,宗肆也未說話,似乎一切,在此時都并非那般重要。
他只是這般穩當的抱著,而也任由他抱著,順從地靠在他膛之上。
寧芙若是看見宗肆出手,其實便能明白他為何忽然不開口了。
方才宗肆,在看到那般時,是真生出了殺人的念頭,不論是誰,他都不在乎。
他如今不敢在面前做出這番舉,那人卻那般肆無忌憚的屈辱地去的。
如何不該死
這會兒,鷙還未散去,怕嚇到。
宗肆將抱回了自己的馬車,讓坐在自己上,手替解開了捆住雙手的繩子。
又手解開了寧芙眼睛上的布條。
不過卻是未讓立刻看他,而是手覆蓋在眼睛上。
寧芙便也坐著一不,即便看不見,可是此刻男人的氣場,還是能到幾分的,眼下他心不平靜。
“我心中猜測是孟澤。”過了須臾,寧芙開口道。
“嗯。”宗肆淡淡應著,半擁住微微發抖的軀。
“我提及黃金萬兩,他也毫無所,顯然不在乎金子,而其他人之中,只有孟澤嫌疑最大,他上一世對我的心思,便是如此。”寧芙道。
“我還提到了你對我有幾分心思,我不知這是否會對你造困擾,只是方才那種形,思來想去,他有求于你,提及你,或許能自保。”
在認真回憶著方才自己同男人的對話。
宗肆卻是半分也不想回憶。
他的心在發抖。
若是自己晚來一步,會如何他只慶幸還能想到以自己為借口,如此便也拖延了不時間,他從不在意在外挑明他的心思。
“這是否會不太好……”
寧芙本想再問一遍,他卻低下頭,輕輕地吻在的上,很輕,不帶,只帶了安,溫而又小心,似乎生怕驚擾一樣。
他謹慎地,安著。
他在讓知曉,他在同臣服,他愿為做一切。
寧芙未阻止他,因他能讓注意力集中在此時的吻上,不必去想別的。
見配合,他才加深了這個吻。
吻中逐漸帶了占有。
他不會再讓落到這種境地里。
寧芙這才抬手拍了拍他。
宗肆微微一頓,隨后便放開了。
寧芙的臉,從方才的蒼白,變得紅潤了幾分。
看著他。
“孟澤知曉你的心思了。”寧芙道。
“正好。”他淡淡說,“早就想讓他知曉了。”
寧芙的心復雜了幾分,低聲道:“若是我未記錯,你想扶持他,你當那個攝政王。”
宗肆道:“我與孟淵之間,亦有不易。原先我是想扶持孟澤,不過被你救了之后,孟淵亦在我考慮范圍之。”
寧芙見他這些事,說的這般坦誠,就如同在和說著閑話,心便更復雜了。
“你傷了”寧芙聞到了點腥味,便轉移話題道。
“那人的。”宗肆道。
寧芙心中生出不好的預來,“你方才是想殺了那人”
宗肆未否認。
“你怎麼能這般沖,若是那人真是孟澤,敬文帝能這般算了”
“便是孟澤,也無妨。”宗肆卻道。
猜你喜歡
-
完結201 章
穿越之絕色寵妃
一恍神,一轉身的相遇;從時光的一端輾轉到時光的另一端;繁華落幕,從此不再是陌生人...她是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人類,卻一次陰差陽錯穿越到了一個聽都聽沒說過的朝代...從此,在歷史上繪畫出她專屬的美妙絕倫的一筆...他本是生性冷酷、拒人千里的一朝太子,卻因爲她,成了淡然溫漠、溫文爾雅的翩翩公子..
51.2萬字8 16143 -
完結451 章
踏枝
秦鸞夢見了師父。 師父說,讓她下山回京去,救一個人,退一樁親。 * 我的道姑女主是有些玄學在身上的。
80.6萬字8 1509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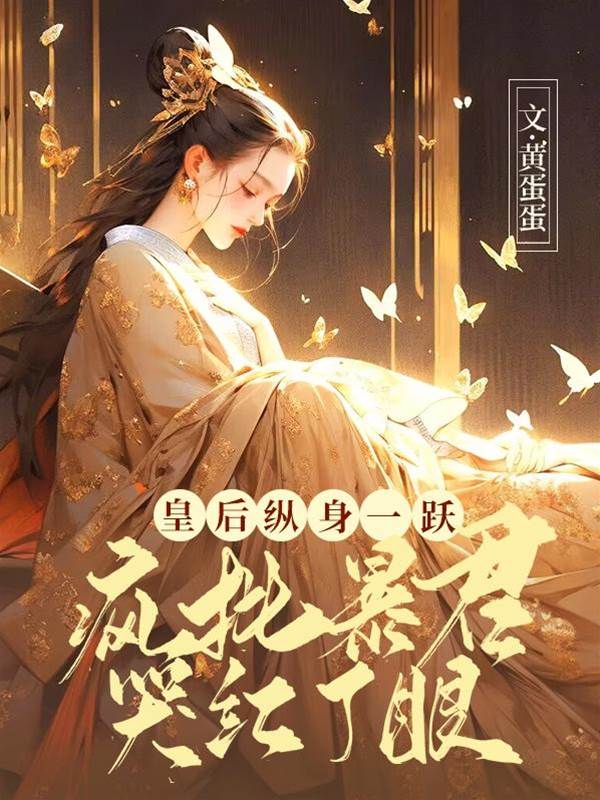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135 章

弄春柔
昭武元年,薛柔第一次見到謝凌鈺。 剛登基的天子尚年幼,容貌端華,寡言少語,唯獨淺笑喚她阿音時,眉間鬱色稍淡。 彼時,她姑母貴爲攝政太后,權傾朝野,龍椅上稚嫩的帝王不過傀儡。 薛氏適齡的女兒皆入宮,長伴太后左右,不出意外,其中最得太后青睞的便是下一任中宮皇后。 然而薛柔生來嬌縱,更對龍椅上陰鬱寡言的少年無意。 她屢屢行出格之舉,任由薛家嫡女水性楊花的謠言愈演愈烈。 及笄那年,天子離宮,親至薛府道賀。 衆目睽睽之下,愈發端默冷肅的帝王褪去威壓,露出堪稱溫潤的笑。 “阿音莫要爲了躲朕,與無名鼠輩爲伍。” “朕永遠不會強迫你做任何事。” 少年的聲音如敲金擊玉,引她信以爲真。 — 昭武十二年,孝貞太后薨。 年輕帝王親政後第一件事,便是清算外戚和薛黨。 洛陽滿城風雨,卻在一夕之間雲開雨霽,只因宮中多了位神妃仙子般的美人。 新建的寶玥臺中,薛柔推開半跪在地的男人,冷言冷語。 “陛下出爾反爾。” 謝凌鈺:“朕本不願如此。” — 謝凌鈺拖着病軀,御駕親征之時,得了一則消息。 薛後穢亂宮闈。 他在帳中枯坐至天明,一夜之間鬢邊已現銀絲。 心腹不忍,勸他放手。 謝凌鈺垂眸,當年,她既對自己無意,便該躲遠些,偏要招惹他。 巍巍皇權,豈容她肆意踐踏,合該餘生困囿深宮,一點點報償君恩。 爲何放手?他今生今世,與薛柔生同衾死同穴。
32.5萬字8 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