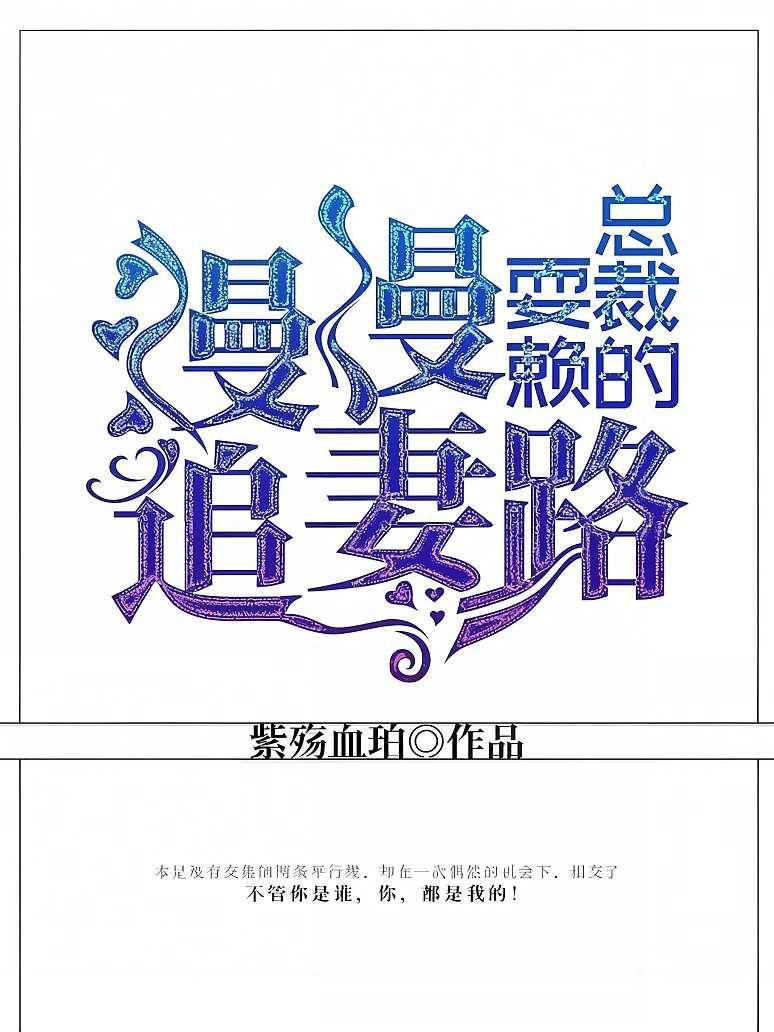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于后悔中說愛你》 第177章 離婚
結完賬往外走,季臨川順手接過椅推手,丁覓荷在上面坐穩了,跟季母并排說著話。
季父走在旁邊,偶爾應兩聲。
鹿鳴跟在季臨川側,聽著前面長輩們說小葡萄晚上睡不睡得安穩,腳步放得緩。
夕把幾人的影子拉得很長,融一團暖融融的廓。
沒人注意到餐廳轉角的柱子后,時野站在那里,指尖攥得發白,目落在鹿鳴搭在季臨川臂彎的手上,一不。
陳默站在時野側,低聲喊了句:“時總?”
時野回過神,聲音發:“季臨川父母什麼時候回的國?”
“今天下午的航班。”陳默答得利落。
時野沒說話,下頜線繃得死,臉沉得像要落雨。
陳默揣度著他的神,繼續道:“聽說鹿小姐和季已經定下婚約,剛才包廂里,應該是兩家人在商量婚事。”
時野間溢出一聲極輕的嗤笑,聽不出是嘲諷還是自嘲,周的氣低得嚇人。
他盯著遠一行人漸遠的背影,眸深得像化不開的墨。
他轉融進走廊影里,腳步踩在潔的地磚上發出沉響,背影在暖黃燈里個孤寂的點。
陳默見狀,快步跟了上去,不敢再多說一個字。
黑邁赫停在酒吧后門,時野徑直往里走,陳默快步跟在后面。
吧臺前,時野一杯接一杯地喝著,琥珀的酒見了底,空杯在臺面上摞了半排。
Advertisement
陳默在一旁低聲勸:“時總,別喝了,傷胃。”
時野沒應聲,只抬手又敲了敲吧臺。
陳默遞過溫水:“時總,您胃本來就弱,這麼喝下去該疼了,回頭老太太看見您這臉,不得又要念叨。”
時野著酒杯的指節泛白,間溢出聲悶笑,酒晃出杯沿。
時野著杯底晃的酒,胃里泛起悉的酸脹。
以前應酬喝多了,鹿鳴總會端來溫好的蜂水,指尖按他眉心時帶著輕嗔。
如今,只剩空杯映著自己狼狽的影子。
時野閉了閉眼,苦漫上來。
是他沒珍惜,從前做夫妻時,總追在他后笑,眼里的比星辰亮。
方才見眉眼舒展的樣子,竟像看到了很久以前那個笑的姑娘。
原就該是這般鮮活的模樣,只是如今,那份溫全給了別人。
時野又開了瓶酒,琥珀直往杯里倒。
陳默看他臉發白,大著膽子按住酒杯:“時總,再喝真要出事了,我送您回去吧。”
“走開。”時野聲音發啞,揮開他的手。
陳默沒退,低聲道:“時總,有什麼事不能好好說?”
“你不懂。”時野仰頭飲盡杯中酒。
陳默咬了咬牙:“您要是……還惦記鹿小姐,不如……”
話沒說完,就被時野冰冷的眼神截住。
陳默心一橫,梗著脖子往下說:“您前幾次喝醉,里喊的都是鹿小姐名字,還非要往家闖。時總,當局者迷,您心里到底還有沒有,自己該清楚。”
Advertisement
時野握著酒杯的手猛地收,指腹被玻璃硌出紅痕。
像是被破了什麼,他的肩膀垮了下來。
“是又怎麼樣,”他聲音發飄,“就要嫁給別人了。”
陳默垂手站著,聲音放得更輕:“時總,只要還沒塵埃落定,總有機會的,您當初……”
他沒說下去,只看著時野驟然繃的下頜線。
陳默斟酌用詞:“當初是您先松的手,可心要是沒放,總該試試往回拉一把。”
吧臺頂燈落在時野臉上,半明半暗里,他睫了。
陳默又道:“鹿小姐不是鐵石心腸的人,你從前待的好,未必全忘了。”
他頓了頓,補了句:“鹿小姐心里若真沒你,當初也不會……”
時野指尖懸在半空,許久,才緩緩蜷起,眼底那片死寂里,浮起星點微。
陳默著他繃的側臉,語氣添了幾分懇切:“您和鹿小姐年相識,三年夫妻,那些日子里的分不是說斷就斷的,旁人再親近,哪比得上十幾載的浸出來的了解。”
“論基,誰能比得過你?”
時野握著酒杯的手松了松,酒晃出細小的漣漪。
“可現在……”時野聲音發,像被砂紙磨過,“連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怎麼會原諒。”
陳默嘆了口氣:“當初本就是被人挑唆才走到這步。人心是的,也念舊,您肯低頭認個錯,好好說說,總有轉圜的余地。”
Advertisement
時野指尖抵著眉心,沒應聲。
陳默深吸口氣,擲地有聲:“時總,有些人一旦錯過,這輩子都找不回來了。”
這句話像針,準刺破時野強撐的鎮定,他抬頭,眼底是驚惶的空白。
“你說得對。”時野抬手抹了把臉,聲音里帶著剛醒的清明,“既然放不掉,不如……去試試。”
陳默見他眼底那點穩了下來,微松口氣:“從在意的事著手總沒錯,宋小姐和顧淮卿那邊都生了變故,如今沒了當年那些阻礙,總比從前順些。”
時野指尖在桌面叩了兩下,沒說話,卻像是聽進了心里。
在意的事……時野心頭一沉,在意的人事,如今都安穩在邊,分明都已繞開了他。
丁覓荷那里行不通,看季臨川的眼神,分明是滿意,認了這個婿。
他指尖攥得發白,忽然一頓——對了,還有孩子。
時野眉峰蹙,想起先前做羊水穿刺的事。
那時他幾乎用了所有手段,卻死死護著肚子,像護著最后一道防線,任他如何迫都不肯松口。
那項檢查終究是沒做,到現在,他仍說不清那孩子究竟是誰的。
鹿鳴一口咬定是季臨川的,可他們在島上那幾日的重合,偏巧卡在最微妙的節點上。
越是抗拒,反倒越像藏著什麼。
時野眸沉了沉,這事總得有個定論。
他不能就這麼糊里糊涂地,連個爭取的由頭都沒有。
那個雕玉琢的小家伙——是他唯一的突破口了。
時野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步頻沉穩地走向門口。
陳默快步跟上,聽見他頭也不回地問:“離婚協議送宋家了?”
“送了,”陳默低聲道,“但宋小姐那邊……還是不肯簽。”
“不肯簽?”時野手搭在門把上,聲線冷,“把協議釘在宋家大門上,告訴,簽不簽,這婚我離定了。”
“讓宋家知道,這份協議簽與不簽,結果不會有兩樣。但拖得越久,他們要付的代價就越重。”
陳默見他眼底戾氣翻涌,不敢再多言,只低眉應道:“是,時總,我這就去安排。”
猜你喜歡
-
完結1297 章

戰神歸來,大佬馬甲颯爆了
【女主殺伐果斷,男主霸道傲嬌粘人】令全世界俯首稱臣的帝國女王,重生在了被親奶奶迫害致死的廢物少女身上。重生后,她用五年成了最年輕的戰神!今日,她榮耀歸來!然而,還沒等她回去搞死奶奶毀了家族,六歲弟弟就被霸道總裁抓了,還要抽光他的血?很好!既然如此,她就讓那總裁體會一下自己的血被慢慢抽干的感覺!什麼?!總裁他爹是戰部高層?還敢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況下來找她算賬?她直接甩出比對方高出兩級的戰部徽章:“不想在戰部待了就給我滾蛋!”
137.4萬字8 295587 -
完結322 章
全球首富的頂流嬌妻
徐願景招惹上榮聿深是不得已而為之。一心當個隱身的合格女朋友。等著大佬厭倦,她立刻收拾包袱滾蛋。誰知。著名狗仔突然爆料:驚!當紅小花徐願景深夜私會全球首富榮聿深,車內密會數小時。商界黑馬當眾放言:徐願景,我小嫂嫂。榮聿深親弟接受采訪:快領證了。貴太太圈流傳:榮夫人在準備婚禮了。 “假的!造謠!” 徐願景一邊回應,一邊收拾包袱。神情危險的男人堵在門口:“想走?兩個孩子留下。肚子裡的生出來。等我死了。”
68.7萬字8 33220 -
完結105 章

于雪落時分
十八歲的顧允真,純得像搪瓷娃娃。初上大學,她被父母託付給周循誡,請他多多照拂。 周循誡,京城周家最小的兒子,雷霆手段執掌合泰六年,頂着重重阻力,將合泰帶回巔峯。 她和他第一次見面,在慌亂中拽住他的衣袖,陽光被紫檀木屏風的橫柵篩落,他立在午後陽光中,輪廓分明,骨相明晰。 男人腕骨上佩着薄薄一枚白金腕錶,表情漫不經心,居高臨下俯視她,薄脣勾起冷淡笑意。 “拽夠了沒有。” 自此,顧允真一點點熟知周循誡的個性。殺伐決斷,雷厲風行,說一不二。同時,也冷淡,沒耐心,嫌麻煩,對於他不感興趣的,一點耐心也欠奉。 - 同一屋檐下,少女情愫如破土的新芽,與日俱生。 一夜,她穿吊帶和超A短裙出入酒吧,周循誡趕到,將人帶回家。 顧允真醉酒後醒來,周循誡命她反省錯誤。 她說不過周循誡,便開始不講道理,胡攪蠻纏。 大滴晶瑩的淚珠從眼尾滴落,她眼尾瀲灩,鼻頭立時染上一層暈粉,楚楚可憐。 “你看,你就是嫌我麻煩。” 聞言,周循誡眉心狠狠跳了下,理智的弦幾乎要斷掉。 “嗯,麻煩死了。”他語帶不耐,手指扣住她後頸,“所以,過來給我親一下。” ——周循誡最怕麻煩,顧允真是他見過最麻煩的女孩子。但是沒辦法,誰叫他栽了。
41.4萬字8 149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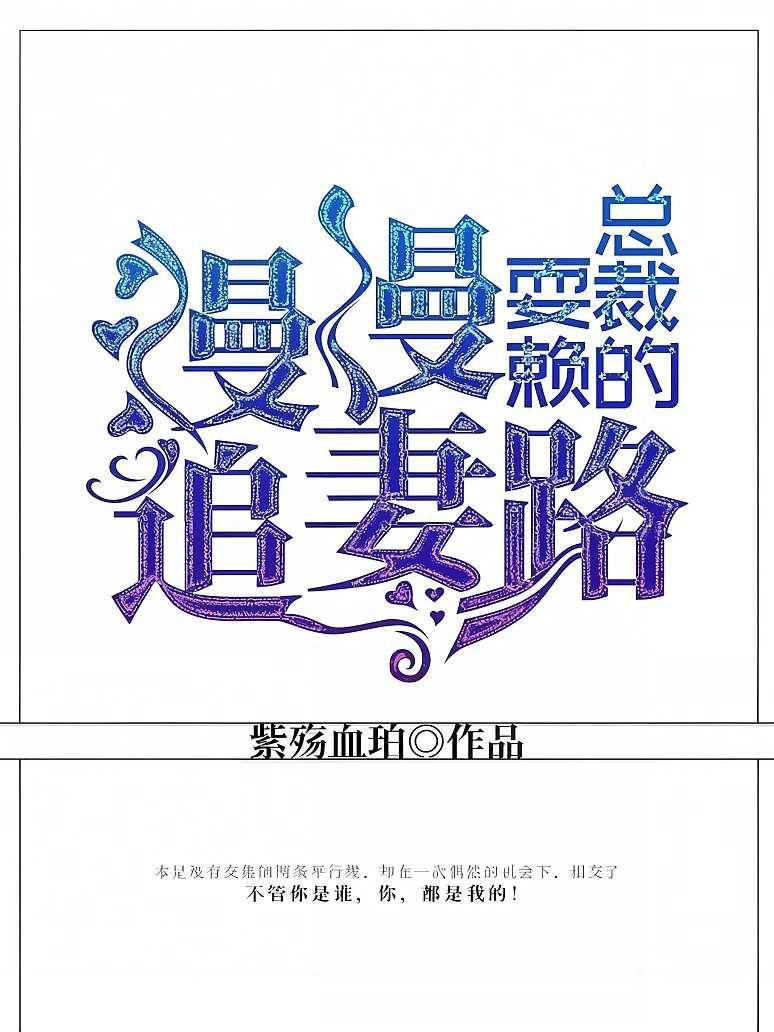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
完結939 章

親親小萌妻:腹黑老公愛不夠
「老公,我想麼麼噠」 捧著文件的謝景曜頭都沒抬,「英語考了18分,這月取消麼麼噠」 白翩翩垮下雙肩,一臉挫敗。 夜裡,身邊的男人睡的迷迷糊糊,感覺到唇上有...
172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