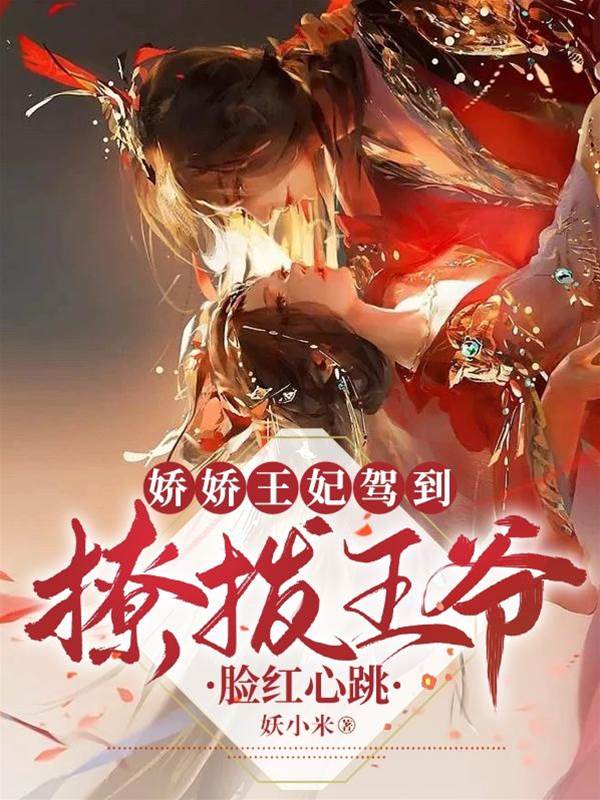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昭月長明》 親密
賀祈年點燃了床榻旁的一盞燈,小聲道:“殿下吩咐在下來為您診脈。”
這睡在太子寢居,又頗得太子寵,賀祈年起初是將當了侍寢的宮婢。可待燭大亮,那張豔冠京華的面容闖眼簾,賀祈年嚇得手腕一抖,險些摔翻了燭臺。
“衛、衛七姑娘?”
衛姝瑤著眼,迎著燭火晃了晃眼神,瞇眼打量了賀祈年一眼。
“你是……”茫然開口,腦子因今夜謝明翊的輕薄之舉仍是混沌一片。
賀祈年忙放了燭臺,低聲道:“在下乃是賀春水的弟子,名祈年,如今在太醫院當值。”
衛姝瑤一怔,又仔細看了一眼,終于想起來,“原來是你!”
年病重,父親尋遍天下名醫,最後求到了曲州千花谷賀神醫門前,托他研制了一味藥丸,常年配著不離,方才平平安安長大。
衛姝瑤小時候只見過賀春水幾回,約記得他邊有一個藥,生得眉清目秀,待人溫潤。
眼下這境地,自然不便敘舊,賀祈年不敢耽擱,連忙上前為診脈。
“殿下這也太……”他收了手,眉心微擰,低聲道:“姑娘子過虛,需得好好補補,近日不能再……”
他止住了話頭,咳了兩聲。
衛姝瑤見他話裏有話,只覺得愈加赧,面上一紅,尷尬回道:“并非你想的那樣,你開了藥方于長順吧。”
賀祈年應聲,準備出門時,忽聽得衛姝瑤喊住了他。
“賀太醫稍等,你能否再給我配一味藥丸?”手從懷中出那空的藥瓶,于他手中。
賀祈年聽了的托付之事,頷首應下,臨去前,瞥見手指因凍紅腫,約長了凍瘡,心中便記了下來。
衛姝瑤這一睡,又是睡到第二日午後才醒。
Advertisement
回想著昨夜的事,仍是心有餘悸,心尖發。
謝明翊此前對頗為克制,即便那回失控,也只是重拿輕放。可、可他昨夜……
他上的炙熱和滾燙的指腹,還有那令人意神迷的微涼的瓣,都讓心緒不寧。
想著想著,卻又紅了眼睛,不知他究竟是何用意。
直至寶枝進來喚,見到衛姝瑤腫著一雙眼,長睫在下眼瞼投落的影和眼底青重疊,愈發顯得憔悴了。
“姑娘這是怎麽了?”寶枝心急問道。
衛姝瑤委屈抿了抿,小聲道:“被狗咬了。”
許是心裏難,嗓音沙啞得厲害。
“啊!那,那這可如何是好,姑娘必定得……”寶枝擡手了的額頭,見一切如常,方才緩了緩氣息,“這寢殿哪裏來的狗呢?姑娘必定是又夢魘了。”
衛姝瑤眉心擰起,見帶了一碗湯藥,忙岔開話,問道:“怎的又要喝藥?”
寶枝答話:“長順說,是殿下特意吩咐的,許是看姑娘病了這麽些日子一直不好,賀太醫又開了新的方子,說是好好調理調理。”
衛姝瑤瓣抖,自知那是什麽“補藥”,越發窘迫,只得深深嘆了口氣,無力招手,“拿走拿走,不喝。”
最是怕苦,原先吃那味藥丸都是因著救命才迫不得已。這算什麽?
正要拒絕,卻聽得外面踱步來了人。
“既是病了,怎能不喝藥?”
低沉的嗓音伴著一道月白影,衛姝瑤子驀地一僵,雙手不自覺攥了被子,往裏又了。
謝明翊依然是擺著張毫無波瀾的臉,角卻是輕勾著淺淺的弧度。
衛姝瑤懊惱地垂下眼,咬了下瓣兒,深吸了一口氣,才直脊背,向走到榻前的謝明翊。
可一對上他那雙清冷的黑眸,就想起昨夜種種,深如旋渦般要將吸納進去的眼神,被他欺而近時狂的心跳,還有他微涼的瓣。
Advertisement
衛姝瑤心中愈發窘,不想開口說話。
謝明翊微斂了神,端上藥碗,在側坐下。
衛姝瑤打量他。
他修長的手指了瓷勺,攪著湯藥,慢悠悠地轉著勺子。
……莫名就想到他的手指扣自己十指的覺,和他緩慢吮著時,指節的用力。
“昨夜孤喝醉了,不記得發生了什麽。”他慢條斯理地開口。
衛姝瑤難以置信地擡眼,倏地直起了子,怒瞪他一眼,心裏大罵:怎有如此厚無恥之人……
比昔年還過分!
謝明翊將湯藥遞過來,舀起一勺,送到衛姝瑤邊。
衛姝瑤哪裏肯開口,抿了,瞥過眼去。
卻見他子微傾,略湊了過來,低嗓音道:“若你不喝,只能用昨夜那種方式喂了。”
衛姝瑤猛地轉過頭來,氣得手指發抖,“你、你、你……”
又又惱,毫不設防地開了口,冷不丁就被喂進了一勺湯藥。
齒間的苦霎時沖擊開來,連帶著心緒激,緋浮上了面頰,染了耳。
雙眼蘊著淺淺淚,委屈地看他,“好苦……”
這人年時尚且沒有這般厚臉皮,怎的會長這個樣子!
卻見謝明翊懶懶了一下瓷勺剩餘的藥,結輕滾,詫異道:“這哪裏苦?”
衛姝瑤心裏氣惱,覺得他定是故意的,嫌棄矯而已。
因著心裏賭了一口氣,瓷勺再遞過來時,便忽地張了口。
謝明翊神淡淡,卻是并未有波瀾。
就這樣,將一碗湯藥喂完了。
可這人喂完了藥,卻沒有離去的意思,徑自在側躺了下來。
“孤昨夜沒睡好,勿要擾我。”他拽上錦被前,淡淡道:“你可自行出去。”
衛姝瑤自然不想留在這裏,可肩上還疼著呢……
Advertisement
許是記恨他昨夜的所作所為,將子蜷得很,極抵。
衛姝瑤索著,看見被下的小黑罐,神微頓。
半晌,也不見謝明翊有醒來的意思,衛姝瑤到底不忍擾他休憩,只悄悄在一旁,反複轉手裏的藥罐,好打消些張。
這東西是寶枝進來時最先遞給的,說是太子殿下特意吩咐的。
衛姝瑤遲疑了片刻,擰開蓋子,挑起一抹淡綠質潤的膏,在手背上了兩下。細膩的藥膏之即化,彌漫一清涼的草藥香氣,還有些香樟的味。
衛姝瑤低眉細細嗅聞了一會兒,蹙眉思索。這東西不知道用來做什麽,寶枝也不在邊,總不能直接去問謝明翊。
便下了床,將藥罐握在手心裏,想出去找寶枝順問個究竟。
正要悄悄出去,卻聞後有了響。
一只手有力地扣住了的雪腕。
腳下頓時不穩,整個子立即跌落下去,竟直接跌坐在謝明翊懷裏。
“方才……聽得外面有人來了。”結結出聲,音若蚊蠅,“我只能留在這裏面。”
謝明翊順勢箍住的手,薄微勾,忽問:“手裏拿的什麽?”
“是寶枝拿給我的。”衛姝瑤下意識攏手指,卻被他掰開手心,徑直將藥罐拿走了。
謝明翊眸頓了頓,淡淡“哦”了一聲。
他擰開蓋子,指腹刮了點藥膏,在衛姝瑤手背上慢慢勻開。
微涼的膏脂化薄薄一層,幽淡的清香中混著點味。
他修長的五指輕輕順著的手背,“你不知這是什麽?”
衛姝瑤愣愣搖頭。
“嘖,真是貴的千金小姐。”謝明翊手指微頓。
“你的婢先前不是想問長順要這個麽?”
衛姝瑤這才知道,是前兩日寶枝想求的凍瘡膏。
謝明翊給塗了藥,方才起,出門去了。
他剛出去,就聽得外面梁錦的聲音傳來:“殿下,刺客餘孽發現了……”
謝明翊離去的腳步聲,顯然急促了不。
衛姝瑤沒有聽得太清楚,只是攥著手裏的藥罐子,托著下,若有所思。
春蒐還有幾日呢?這……
還有機會逃嘛
懊惱地將藥罐子扔在一旁,幹脆拉下被子,索讓自己睡個夠……
天已暗。
陸青婉擰著帕子,在苑林中徘徊,不時幾眼東面高聳的配殿。
“小主,回去罷。”邊宮婢悄悄開口,勸道:“您想找太子殿下求,何不等明日夜宴?”
陸青婉遲疑了一瞬,扶著往回走。
回了住,陸青婉去宮裝,換了件素雅常服,一并拆下繁複頭飾,隨意扔到妝臺上。
“您現在就卸了釵環,若聖上過來,如何是好?”宮婢見狀,急得上來就要挽發。
陸青婉冷眼一挑,“誰管他,難不因這個,便要把我拖出去埋了?”
掌事宮紫鵲捧著一盤子賞賜進屋,忙上前屏退了衆人。
紫鵲閉門窗,上來給陸青婉梳發,低聲道:“公子護送老爺先回府了,臨走前才叮囑姑娘在獵場安分些,斂斂脾氣。”
陸青婉卻是昂起臉,一雙圓眼向,焦急問道:“怎樣,太子見了大哥嗎”
紫鵲頷首,將陸青澤代之事一一說與聽了。
陸青婉將梳篦重放在桌上,嘆氣:“若非這妃嬪份礙事,我早親自上門去了,董興如此仗勢欺人,太子怎容他猖獗至今!”
紫鵲神一頓,俯在耳邊,說:“姑娘,你可知太子是誰?”
悄聲嘀咕,陸青婉聽得心驚跳,騰地站了起來。
“怎會是他!”
紫鵲眉頭皺得甚,“雖說知曉此事的人不多,但那夜見面後,公子確信是他。”
陸青婉面上刷地褪去,陡然轉白,“昔年瑤瑤得罪了他,他怎會為主持公道!”
“我竟還大哥去找他求,當真是自投羅網!”
陸青婉宮以來,從未出席任何宮宴,故而竟不知太子模樣,當下只覺如遭雷擊。
一下跌坐在椅上,又急又悔,眼底落兩行淚,“當年若不是我的緣故,瑤瑤也不會去招惹他……”
“他最痛恨瑤瑤!”
陸青婉五味雜陳。
想起很久以前,衛姝瑤和謝明翊的集乃是意料之外促。
那年秋高氣爽桂子飄香,衛姝瑤和父親鬧脾氣,心中煩悶,陸青婉拉著出門戲耍。
京城權貴的年郎們見二人出來,說有個好去帶們去耍玩。
到了地方,陸青婉才知道那是“鬥場”——奴隸與兇的鬥場。
衛姝瑤當場就要走,陸青婉卻生出了好奇,拽著留了下來。
天暮沉,微冷秋風吹得單薄衫簌簌作響。
一群世家子弟們高坐檐下,神閑氣定地準備觀賞腥的廝殺。
衛姝瑤頗為不悅,正想拖著陸青婉離開,突然看見一道影自影裏慢慢踱步上了場。
了幾天的狼從另一邊的籠子裏竄出來,擋住了那年的去路。
陸青婉蹙眉,卻見衛姝瑤瞳孔一,渾僵。
現下想來,衛姝瑤或許當時便留意他了。
年生得俊朗如玉,上舊袍襤褸,獨獨一雙清冷黑眸出的氣勢,極為迫人。
然而在這群世家子弟面前,他不過是個奴隸,亦如低賤的螻蟻。
偏就是這不起眼的“螻蟻”,僅用手中的短刃便將那條狼斬殺膝下。
世家子弟們高聲唏噓,有人見他手不凡要買下他時,衛姝瑤“嚯”地起。
“這人歸我了——!”擲地有聲的嗓音帶了點。
等散了場,陸青婉才知,原來這人并不是奴隸,而是沈興良府上的小啞。因著不說話,無意中闖進了這鬥場,被人錯認為奴隸強行丟進了場。
陸青婉見他份落魄,悄悄同衛姝瑤說:“你不是厭煩國公爺給你議親麽,咱們打個賭………”
衛姝瑤本不想應,可最終卻是頷首應允了。
陸青婉摟住衛姝瑤,吧唧親了面頰一口,“你往好想,左右你對他好,旁的人也不敢再欺辱他了。”
陸青婉本也沒想著衛姝瑤能。殊不知,英國公當真斷了心思,轉而勸說衛姝瑤早日清醒,不要再與那啞年走近。
再後來,謝明翊被衛家趕出京城,去了北境寒苦之地。
最後一次見他,猶記得那雙清冷的黑眸盯著衛姝瑤,沒有毫波瀾,卻人遍生寒。
猜你喜歡
-
完結25 章
愛妻帶種逃
那婚前就放話不會把她當妻子看待的夫君,八成犯傻了,不然纔剛摔了交杯酒要她滾出去,怎麼一見她的手腕就變了,還是他真如傳言「生意做到哪,小手摸到哪」那般有戀手癖?要不爲何一眨眼就對她又是愛憐呵護又是纏綿求歡的……寵她之餘,還連所有她在乎的人也都一併照顧了,他說唯有這樣,她纔不會分心去擔心別人,能好好被他獨佔,他說不許她哭,除非是他的愛能寵她到令她流出幸福的眼淚,他說了好多好多,讓她甜上了心頭,也被他填滿心頭,然而也因爲他說了好多,讓她忘了問他爲何對她這麼好,纔會由上門「認親」的公主那兒得知,其實他寵的人不是她,他愛的是前世妻子,而自己手腕上的胎記讓他誤認了……而同時擁有胎記和記憶的公主,似乎纔是他尋尋覓覓的人,她想,他曾給了她那麼多幸福,這次,爲了讓他也得到幸福,即使已懷了孕,即使再痛苦,她都要將他還給他真正愛的人……
8萬字7.82 12634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60069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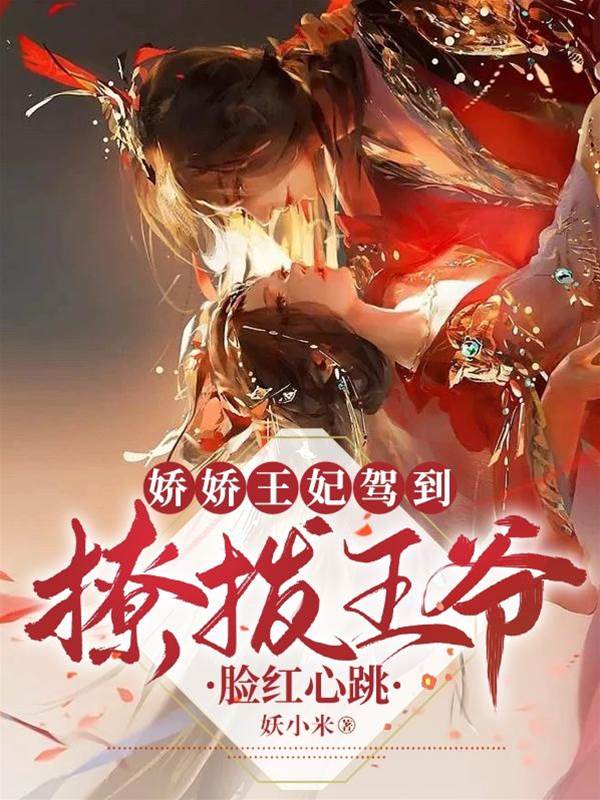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09 章

承秋波
東宮謀逆,北寧伯府做了件不大不小的錯事,但若要嚴辦,整個伯府都得出事,全家老少戰戰兢兢,生怕殺頭的禍事臨身。 伯府老夫人把孫媳林昭昭叫來,沉重地說:“昭昭,你得救救伯府。” “處置此事的,是靖國公,聽說你們林家以前和靖國公府頗有私交,試試看,能不能讓國公爺通融通融。” 林昭昭:“……” 老夫人不清楚,當年她可差點嫁給靖國公,是她夫君“橫刀奪愛”。 試試倒是可以,只是,依靖國公那脾氣,只怕試試就逝世。 * 靖國公府的老人都知道,公爺裴劭年少時有一段求而不得,大家都以爲,那女子已然仙逝,成了公爺的白月光,讓這麼多年來,公爺絲毫不近女色。 卻不曾想,原來公爺心裏裝的白月光,竟已嫁給他人。
16.6萬字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