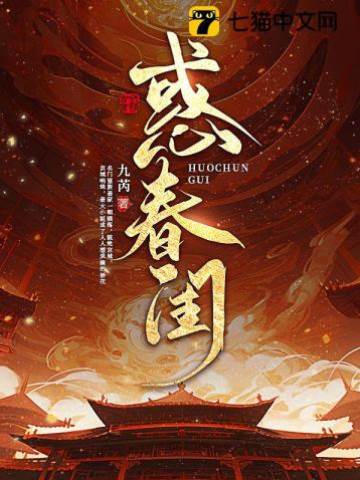《碎玉》 第84章
第84章
攻打函谷關的那一場戰役, 不可謂慘烈膠著。
長安的兵馬自知此地之後,再無險可守。故而浴戰、孤注一擲。
益州的援兵源源不斷,可長安軍卻制于北方的烏桓, 糧草殆盡。
繼續拖下去,函谷關被益州軍攻破指日可待。
一連七日之後, 城關上的驃騎將軍劉振帶來了一個人。
一個年輕的人,尚令嘉。
說:我要見齊楹。
的懷裏抱著不足一歲的孩子, 是如今長安名義上的天子齊鈺。
周淮冷笑:“豈是你說見就見的?”
尚令嘉走到牆邊:“他若不來,我便帶著他的兒子從這裏跳下去。”
攻城的軍士見此狀皆惶惶不安, 立刻八百裏急報送去了益州。
三日後, 牆下旌旗蔽空, 綿延數裏不絕,長安軍便知道是齊楹來了。
高大的青海馬上端坐著著戰甲的年輕男子, 齊楹單手執韁, 仰頭向尚令嘉看去。
太刺眼,照著滿目塵沙。
尚令嘉抱著齊鈺, 母子倆像是風中的落葉。
“孩子尚未見過父親, 我今日來, 只是想帶他見一見。”尚令嘉哭訴,“如今父子相殘,我除了痛心無計可施。只要你願意退兵,長安城的帝位依然要等你來坐。當年若不是你倉促而別, 我們孤兒寡母也不至于無所依傍。”
有不明所以的軍士面面廝覷,齊楹淡淡地看向元。
元會意,挽箭搭弓, 一箭中尚令嘉旁的旌旗。
尚令嘉顯然被嚇了一跳,下意識倒退一步, 懷中的齊鈺便嚇得大哭起來。
“主子從未寵幸過你,你說你懷中的孽種是主子的孩子實屬無稽之談。”元高聲呵斥,“你若求死,我等決計不會阻攔。若你打開城門,或許可以恕你一命。再負隅頑抗,下一箭便取你兒子的命。”
Advertisement
這句話顯然極震懾力,尚令嘉下意識將孩子抱得更。
黑暗中,一個男人沉默站起,對著尚令嘉出手:“把孩子給我。”
著他,尚令嘉淚如泉湧:“則簡,不要。”
連連搖頭,倒退數步,直至退無可退。
“你若此刻不再狠下心來,城破那日,你我都難逃一死。”薛則簡暴地拉住的胳膊,幾下便將齊鈺搶到了自己的手裏。尚令嘉跌坐在地上,鬢發散,淚如雨下。
薛則簡不再理會,而是獨自走到了牆邊。
“齊楹,你看好了。這是你的兒子。當年你拋下們孤兒寡母一走了之,是我薛則簡庇佑們至今。想不到你不不願相認,還要刀戈相向。”他走到牆邊,雙手將齊鈺舉起,“你若再不退兵,我便將你的兒子從這裏扔下去。”
尚令嘉聽到他這麽說,幾乎肝膽俱裂:“薛則簡,你敢!”
幾名鐵軍士立刻按住,力掙紮:“你畜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尚不足歲的孩子不知此刻發生了什麽,他對著薛則簡出的小手,咯咯地笑起來。
薛則簡靜靜地看著他的眉眼,眼中有一瞬間的轉瞬而逝。
他狠狠心,閉了閉眼,再向齊楹:“我數三個數。”
元有些擔憂地看著齊楹:“主子……”
齊楹平淡地看著薛則簡,依舊一言不發。
齊鈺還不大會說話,近來才學會阿娘,對著薛則簡也一口一個阿娘地。
這個孩子生得雕玉琢,項下的金鎖是今年才打的,穿在紅繩裏,像是年畫上的孩子。
“一!”
尚令嘉哭幹了眼淚,嘶啞著嗓子:“薛則簡,他心裏一直都是拿你當父親的。”
衆人對這話不覺得吃驚,只當是尚令嘉借此博得薛則簡的同。
Advertisement
而薛則簡心中卻在此刻五味雜陳。
齊鈺的手抓握著薛則簡的胳膊,繼續咿咿呀呀地說著聽不懂的話,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
薛則簡咬牙關:“二!”
尚令嘉的眼睛裏已經流不出眼淚來,掙紮著子求他:“你放過他吧,求你放過他。”
這明晃晃的太,像是要將一切灼燒灰。
突然懷中的齊鈺,口齒清晰地了一聲:“阿父。”
薛則簡的手猛地抖了一下。
他的目著城門下綿延數裏,一眼看不到頭的戰甲鐵騎,看著遠方被馬蹄踏起的黃沙。再轉過,看著邊渾汗如雨的軍士,最後是滿臉淚痕的尚令嘉。
懷中的孩子像是發現了什麽新奇的東西,一會阿娘,一會阿父,最後拍著手咯咯地笑起來,眼睛又圓又亮。
薛則簡仰天閉目,終于嘆息了一聲。
他把孩子塞給邊的一名校尉。
而後縱從城樓上一躍而下。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衆人都錯愕得回不過神來。
尚令嘉猛地掙開按住的幾名軍士,把孩子牢牢地抱在懷裏。
雄關萬丈,闃寂無聲,好像在這一瞬間為了一座死城。
*
第二年春,長安。
滿城春雪將盡未盡,零零星星的飄灑在街上。
老梅樹上掛著金銀索子,風一吹便是泠泠地響。
風將雪吹起,照落下來,像是滿城金一般。
一個使立在章城門的門口。
穿著夾襖,頭上梳著垂髻,不住地呵手取暖。
漸漸聽到了車馬聲,一輛由四匹高頭大馬駕著的馬車停在了章城門外。
一只纖細的荑從車簾後面出來。
白的鬥篷上拿金線繡著滾花,這種款式又常被人稱作是雪裏金。
從馬車上走下來的這名子梳著高髻,發間一對白玉鬢簪,整個人欺霜賽雪,風致無雙。
Advertisement
立在門口的使才見了,眼淚就奪眶而出。
三步并作兩步地上前來,撲倒在執面前:“娘娘。”
執看著,跟著也紅了眼,親手來扶起來:“卻玉。”
話都沒說上兩句,兩個人都潸然淚下。
手握在一,誰也不舍得松開。
另有使勸:“外頭冷,不是說話的時候。還是先進宮再說吧。”
有轎子停在宮門口,執換了轎子,卻玉跟在旁邊。
“王爺今日正在前殿見大臣,奴婢先來接娘娘到玉臺宮休息。晚上北狄王將會到漸臺飲宴,屆時還要請王妃一道赴宴。”卻玉說話時,聲音還在抖,顯然尚未從喜悅中回過神來。
執掀開簾子看:“這些年裏,你過得可還好嗎?”
卻玉吸了吸鼻子,笑:“自然是好的。”
執的目落在疊于前的手上,輕聲道:“連我都瞞著?”
卻玉是伺候過執的人,落在薛則簡手中,哪裏能有風面的日子。當初執讓快些離開長安,執意不肯,一心要守在這裏等著回來。
如今的手上滿是凍瘡,從袖口出的一節皮上,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見陳舊的傷痕。
除了臉上還是昔年那般清秀外,整個人都不再如同當年那般明豔活潑。
卻玉小心地將自己袖口拉得更低些,小聲說:“過去再不好的,如今也都好了。奴婢橫豎只是過得不如原先那麽面,可張通他……”
張通本就是個太監,在整個未央宮裏都是不拿太監當人來看的。
卻玉吸了吸鼻子:“晚一點,他會來給娘娘請安的。”
“他怎麽了?”執的心也揪了,“可是出了什麽問題?”
見不安,卻玉又安:“沒有,張通本是個機靈的人,早些時候日子的確過得艱難,可他後來憑借著一本事,只用三年時間,已經坐到了常侍郎的位置,且是十常侍之首,如今風頭無兩。”
這是好事,可卻玉的臉上卻沒有什麽喜悅。
執心中疑竇叢生,待到了玉臺宮又多問了卻玉兩句。
屏退左右,卻玉終于是直說了:“娘娘離開長安後不久便出了事,當年張通得罪過的劉常侍領了司隸校尉的差事,等到了每年給太監驗的日子,劉常侍說……說張通他那裏……”
卻玉到底是沒親的孩,越說聲越低,執便懂了。
“于是便將他帶去府監,重新刷了一茬。”
這不單單是上的罰,更像是對神的淩/辱。
這一句說完,二人皆是如鯁在。
執的眼睛有些紅:“當初為何不離開長安呢?”
卻玉低聲說:“娘娘,奴婢這樣的人若是離開了長安姑且罷了,可張通這般的人,離了長安又能去哪?風言風語又該如何面對?天生一輩子是要做奴才的。”
見執難過,卻玉又安:“過去日子再難,如今也都好起來了。娘娘是沒瞧見,他如今十足十的威風,不知有多人要攀附他的關系,就連奴婢也因為他的關系得了很多照拂,往後再沒人能欺負他了。”
就在這時,門外有使走進來說張通求見。
“請他來。”
張通走路靜得沒有聲音,從外面走來時,第一眼先看見他的冠穿戴,跟著才看見他的臉。如今他穿著的是金銀線繡的行蟒袍,頭戴絳紗帽,見了執并不擡頭,先是恭恭敬敬地行了大禮。
“你快起來。”執親自來扶他。
擡起頭的那一瞬,執這才驚覺于他的改變。
三年過去,那個笑起來有些諂的頭小子,已經長得比還高了。臉很蒼白,有久不見的覺,看上去格外郁。
眼窩有些凹陷,無端人覺得疏遠,尤其是那雙眼睛,冰涼冷淡像是作壁上觀的看客。
張通學著過去的樣子對著笑:“能重新見到娘娘,當真是奴才的福氣。”
執不想讓他看見眼底的淚,于是招呼他坐下:“早聽說你如今風頭無兩,今日一看果然大不一樣。我沒有看錯人,你當真是最機敏聰穎不過了。”
聽這麽說,張通出一個笑:“如今奴才這一切,也是托了娘娘的福。”
他的聲音低而細,與一般男子并不同。他比過去話更了,人也常常沉默。
執略問了問他近來的況,張通一一作答。
說到最後,他想到了什麽:“早聽說娘娘上個月誕下了小世子,奴才在此恭賀娘娘,也恭賀主子。”說罷,再次跪了下來。
聽他這麽說,全屋子裏的人都一起跪下,說著恭喜娘娘,恭喜主子這樣的話。
執笑:“都這麽說了,自然是要賞了,一會去找卻玉領銀子。”
張通站起,臉上也帶著笑:“江山有後,是奴才等的福氣。”
執做了個手勢打斷他:“這樣的話不許說了,未央宮的主子如今不是齊楹了。”
“張通說的,是張通自己的主子。”他微笑答。
執不想在這事上強行與他爭執:“孩子如今沒帶進宮來,一早的時候徐平過去瞧過了。若說起來,便是微明也還沒見過呢。”
那日他離開益州去了函谷關,便再也沒有找到回來的時機。他雖不用征戰沙場,卻有太多千頭萬緒的事等著他來點頭。他每一封書信中,字裏行間滿是焦灼,只恨不能即刻回到益州去。
就連世子出生,他也是在信中知道的。
彼時齊楹日夜懸心,總怕孩子如他一般弱多病。
執寫信說是個健康的孩子,他終于能長舒一口氣。
齊楹信上字不多,卻溢滿了歡欣。
他為世子取名齊鏘。
出車檻檻,被練鏘鏘。鏘者,高勇毅。
凰于飛,和鳴鏘鏘。亦寄予了他這做父親的心意。
下著春雪的日子,最能滌污濁醜惡,執手裏握著桂花香片茶,過蒸騰的水氣靜靜地看著張通。
“這幾年,過得辛苦吧。”
他垂著眼不看:“習慣了。”
這便是默認了。
又敘了幾句話,張通便告辭了:“府監還有事,奴才得去瞧瞧。”
執點頭:“卻玉,你替我去送一送。”
卻玉送張通到門口,外頭的空氣很冷,說出口的話都冒著寒意。
“你有一個月沒同我說話了。”面對著張通的,突然開口。
“若不是今日,你又要避我到何時?”
雪站在他上,很久都沒有融化。
猜你喜歡
-
完結1996 章
神醫農女:買個相公來種田
外科聖手穿越古代農家,逗逗相公鬥鬥渣!
344.2萬字8 166894 -
完結2599 章
毒醫狂妃有點拽
她,華夏古武唯一傳人,驚豔絕倫的鬼手神醫,卻一朝穿越成葉家廢物小姐。再睜眼,天地間風起雲湧!什麼?天生廢物?禍世之星?很好,她很快就會讓他們見識一下什麼是天生廢物,什麼是禍世之星。他是萬人敬仰的邪帝,神秘,高貴,不可攀。當他遇上她,她避他如蛇蠍,他纏她如纏藤。邪帝,不好了,夫人又跑了!追!邪帝,不好了,夫人躲起來了!找!
490.5萬字8.46 61520 -
完結264 章

嫁皇叔
顧清儀糟心的高光時刻說來就來。未婚夫高調退婚踩著她的臉高抬心上人才女之名不說,還給她倒扣一頂草包美人的帽子在頭上,簡直無恥至極。請了權高位重的皇叔見證兩家退婚事宜,冇想到退婚完畢轉頭皇叔就上門求娶。顧清儀:“啊!!!”定親後,顧清儀“養病”回鶻州老家,皇叔一路護送,惠康閨秀無不羨慕。就顧清儀那草包,如何能得皇叔這般對待!後來,大家發現皇叔的小未婚妻改良糧種大豐收,收留流民增加人口戰力瞬間增強,還會燒瓷器,釀美酒,造兵器,改善攻城器械,錢糧收到手抽筋,助皇叔南征北戰立下大功。人美聰明就不說,張口我家皇叔威武,閉口我家皇叔霸氣,活脫脫甜心小夾餅一個,簡直是閨秀界的新標桿。這特麼是草包?惠康閨秀驚呆了。各路豪強,封地諸侯忍不住羨慕壞了。宋封禹也差點這麼認為。直到某天看見顧清儀指著牆上一排美男畫像:信陵公子溫潤如玉,鐘家七郎英俊瀟灑,郗小郎高大威猛,元朔真的寬肩窄腰黃金比例啊!宋封禹:這他媽全是我死對頭的名字!
67.2萬字8.23 69546 -
完結625 章

王妃是個小祖宗
重生到前世勁敵身邊,失了武功又沒了靠山的孟青有些害pia。 王爺:「打斷了本王的腿,你得照顧本王一輩子」 孟青還在猶豫著自己是一銀針戳死對方還是戳殘就算,卻發現王爺把自己寵上天。 某王爺云:「把她寵得無法無天,她就只能留在我身邊」
80.4萬字5 35067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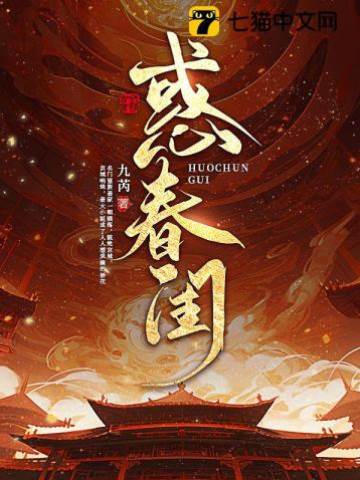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185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矯揉造作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着兄妹情深。 只是演着演着,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衆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裏,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
28.2萬字8.18 88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