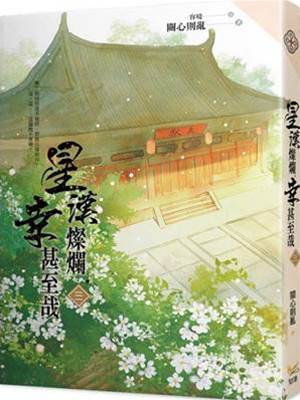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花嬌》 第108章 好意
胡興等人聽了忙退了下去。
裴宴抬了抬手,示意鬱文等人坐下來說話。
鬱文有些惴惴不安地坐了下來,阿茗幫他們帶上門,走了出去。
“三老爺留我們有什麼事?”鬱文困地問。
裴宴像是在清理思路似的頓了頓,道:“剛才宋家的四老爺來找我,哦,就是宋家的當家人,他們家當家的是三房的四老爺,他不知道從哪裡知道了輿圖的事,也想分一杯羹,還提出想和我們裴家合作。你們也知道,我父親剛剛去世,我們幾兄弟都無意做這門生意。但宋家四老爺和我們家有點淵源——他母親和我母親是姨表姐妹,他母親是姐姐,比我母親要大近二十歲,雖說老人家已經去世了,但我們兩家還是時有來往。我就想,如果你們家要是有意趁著這個機會參與到其中來,不如和宋家合夥。就想問問你們的意思。我也好安排。”
鬱文乍耳一聽,喜出外。
裴宴之前並沒有提及這件事,可見他並不看好他們家參與到這樣的生意中來,之後又給他們幾人細細地講了參加拍賣的人家的能力背景,也有告誡他們的意思,海上生意利潤巨大的同時風險也很大,不是他們這樣的人家能染指的。可現在,又做了中間人來給他們家和宋家牽線,可見是覺得他們兩家是有可能合作的。這其中要不是裴家有這面子和底氣能在宋家人面前保住他們鬱家的利益,就是宋家的行事作派忠厚老實,值得信任。
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他們家都是依靠了裴家的庇護。
對此鬱文十分地激。
那要不要抓住這次機會呢?
鬱文習慣地朝鬱棠去。
鬱棠心裡糟糟的。
的確有這心思,想留一份輿圖,以後如果他們家有機會,能做海上的生意。可從來沒有想過和諸如廣州陶家這樣的人家合作。
Advertisement
兩家力量懸殊,弱的一方沒有話語權,合作是不平等的,而且還很容易被別人吞噬。
最先的人選是江家。
就是出了那個江靈的江家。
按前世的記憶,他們家現在還沒有發跡,但從前世發生的那些事看來,他們家又有這個能力。
識於寒微之時,是最好的合作。
可此時,鬱棠又不得不承認,裴宴的提議如同在他們家面前擺了一碗五花,讓他們垂涎三尺。
好在是在父親的目中很快地冷靜下來。
被、得三心二意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鬱棠不由輕輕地咳了一聲,溫聲道:“三老爺,多謝您提攜我們家。但我們家到底只是小門小戶,這樣的生意,不是我們能掌控的,也不是我們能肖想的。我想,這件事還是算了。”
裴宴一腔熱像被三九天的冰水淋了個心涼,臉上頓時有些掛不住。
不是汲汲營營地想要發財嗎?
這麼好的機會,他難得心,想著一個姑娘家不容易,居然落得這樣一個下場。
“隨便你們!”裴宴周一寒,連氣氛都變得凝滯起來,“我也只是覺得你們若是和宋家合作,看在我們裴家的份上,他們不會私底下做什麼手腳而已。既然你們無意,就當我沒有提過。”說完,他端起了茶碗。
這就是送客的意思了。
鬱文覺非常不好意思。
裴宴的好意任誰都能會得到,沒想到鬱棠會拒絕。
當然,這個決定的確是他們早就商量好的,但什麼事都不是一不變的。
鬱棠也太不給裴宴面子了。
鬱文瞪了兒一眼,角微翕,想推翻鬱棠的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買裴宴這個面子,何況裴宴也是為了他們家好。
Advertisement
鬱棠在說出這番話之前就想到裴宴可能會有點尷尬,可沒想到裴宴說翻臉就翻臉,爹就更沒主見了,見裴宴不高興,立馬就想著買裴宴這個人,也不想想這個人會讓他們鬱家陷於何種境地。
“三老爺!”急急趕在鬱文之前開口道,“這大半年來我們家發生了很多的事,要不是有您幫襯,別說平平安安的,就是我姆媽的病,都能讓我們陷困境。我們鬱家能有今天,全是您的功勞。您剛才提出來的事,也全是為了我們家好。只是我們家的家訓素來如此,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宋家是蘇州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我們家除了個漆鋪子就沒做過其他的什麼生意。宋家就算是能帶上我們家,那也是看在您的面子,看在裴家的面子上。別人不清楚,我們自己卻清楚自己能吃幾碗飯。和宋家一起做生意好說,可我們總不能隻拿個輿圖夥?就算是隻拿個輿圖夥,怎麼夥?佔幾?組不組船隊?每次下海幾艘船比較好?每個船上配多人?運些什麼貨?到哪裡停靠?這些我們家統統不懂。難道還要一一來問您不?那我們能幫宋家什麼忙?宋家和我們合夥又有什麼利益可圖?如若利益長期不對等,我們又憑什麼總和別人家合作?那和靠您有什麼區別?”
現在他們家已經把輿圖拿出來賣了,宋家又不是出不起拍賣的錢,何必又要為了一幅能拿錢解決的輿圖來和他們鬱家合作呢?
說來說去,還是看在裴宴的面子上。
這個人還不是得裴宴來還。
就算是裴宴覺得不要,他們家卻不能就這樣接。
鬱文和鬱遠聽著連連點頭,剛剛那一點點的搖此時都煙消雲散了。
Advertisement
裴宴呢,還是覺得不痛快。
說來說去,聽著有道理,最終還不是拒絕了他。
“隨你們高興!”裴宴又抬了抬手中的茶碗。
鬱棠沒想到裴宴的氣這麼大,好說歹說都不能讓他釋懷。
若裴宴心懷叵測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一片好心,鬱棠明明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對鬱家最正確、最有利的選擇,可心裡還是覺得對裴宴很是愧疚。
裴宴高傲又不太理庶務,他難得管一次閑事,卻被拒絕了,也的確是太不知好歹了。
鬱棠就想讓他心裡好過一點,乾脆裝著沒看見他抬了茶碗似的,上前幾步,伏低做小地道:“三老爺,我們回去以後一定好好做生意,爭取有一天能接得住您的賞賜。”
裴宴見低著頭,潔的額頭像玉似的溫潤,長長的睫一不的,像羽般停歇在眼瞼,顯得順從又馴服,心中一,覺得那無名之火漸漸消散了一些。
還知道他的賞賜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接得住的,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了!
“算了!”他聽見自己語氣微霽地道,“也是我考慮不周全,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鬱棠暗暗籲了口氣。
終於把這祖宗哄好了一些。
要不要繼續哄一哄呢?
還想知道前世裴宴為何在他們家的山林種沙棘呢?
鬱棠的快於腦子。
聽見自己恭敬地道:“不管怎麼說,還是要多謝三老爺。要是三老爺不嫌棄,我姆媽前幾天在家裡做了些青團,我讓胡總管帶些來給三老爺嘗嘗。我們家也沒別的能拿得出手的,也就這尋常的吃食做得比別人家早點,能讓三老爺嘗嘗鮮。”
按理說,青團要再過一、兩個月家家戶戶才開始做。但今年陳氏的好了,興趣也高,就提前做了些青團,不多,卻勝在手藝好,又先別人月余,就了能拿得出手的吃食了。
裴宴聽著心裡的鬱氣又散了一些。
他不是那麼喜歡吃青團,但他在守孝,孝期就應該吃這些,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一回事,總是忘了他在守孝,不是請他去喝酒就是請他去賞花,只有鬱家送的東西還算是靠譜。
那些人好像都忘了他爹才過世沒多久。
最最讓他不舒服的是,這些人裡很多都曾過他爹的恩惠。
可見所謂的“殺人放火金腰帶,修路鋪橋無骸”是有道理的。
裴宴在心底冷哼了數聲,說話的聲音卻和了幾分:“不用這麼客氣!那就替我謝謝鬱太太了。”
這就是收下的意思了。
鬱棠大喜,忙道:“您喜歡就好。”又想著他匆匆而來,不知道和宋家的會面怎麼樣了,不好耽擱他的正事,就屈膝福了福,道,“那我們就先告辭了。拍賣結束後再來打擾三老爺。”
宋四老爺那邊還真被他暫時安置在了客房,等會還要設宴招待,裴宴沒辦法在此久留。他對鬱棠的懂得進退很是滿意,索又待了兩句:“這幾天各家的當家人都會來臨安城,你們沒事的時候最好別出門,免得被人看出點什麼來,惹出事端。”
是怕有人知道輿圖是他們家的會有人趕在拍賣之前強搶嗎?
那可都是些他們鬱家惹不起的人家。
鬱遠臉一白。
裴宴瞥了他一眼,道:“你們也不用太擔心,我已經吩咐下去了,凡是來臨安城的人家在拍賣之前都會限制他們出行的,你們家那邊也派了人在暗中盯著。我說的,是怕萬一……”
鬱棠立馬道:“是的,是的。什麼事都怕萬一。我們家在拍賣之前一定不會跑的。您放心好了。”
裴宴臉這才恢復了原來的冷傲。
鬱棠懸著的心也徹底地跟著落了地。
猜你喜歡
-
完結1644 章
神王毒寵:二嫁王妃
渣男負我,沒關係,姐改嫁,聽你喊我一聲「嬸嬸」過過癮。白蓮欺我,沒關係,姐搖身一變,手拿係統,開掛虐廢你。世人陰我,沒關係,戰神王爺護著我,不怕死就上啊!看現代病毒專家,強勢重生,攜絕世美男夫君,聯手虐渣……
295.1萬字8.3 174978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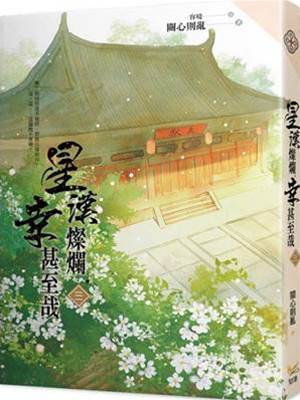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201 章

月明千里(嫁給一個和尚)
【漢家公主VS西域高僧】 瑤英穿進一本書中 亂世飄搖,群雄逐鹿,她老爹正好是逐鹿中勢力最強大的一支,她哥哥恰好是最後問鼎中原的男主 作為男主的妹妹,瑤英準備放心地躺贏 結果卻發現男主恨她入骨,居然要她這個妹妹代替女主和草原部落聯姻,嫁給一個六十多歲的糟老頭子 瑤英被迫和親,老酋長命不久矣,一群膀大腰圓的兒子摩拳擦掌,等著生吞活剝
88.1萬字8.33 26532 -
完結310 章

貴妃娘娘榮寵不衰
元徽五年,宮中選秀。 大理寺卿之女阮含璋入宮選秀,選爲正七品才人。 阮才人冰肌玉骨,仙姿迭貌,自然先得盛寵。 人人都羨慕阮含璋盛寵不衰,只阮含璋泰然處之,不卑不亢。 因她根本就不是阮含璋,她只是替名門千金入宮邀寵的揚州瘦馬。 只待真正的阮含璋大病痊癒,屆時阮家會送入“二小姐”,而她就再無用處。 當監視她的姑姑送來毒酒時,阮含璋含笑接過,一飲而盡。 一把大火燒光了棠梨閣,也送走了剛剛封爲莊嬪的阮娘娘。 同年中秋佳節,宮宴正歡。 皇帝於太液池遊園,於臘梅樹下驚鴻一瞥,看到一抹熟悉靚影。 之後,聽雪宮多了一位姜選侍。 姜雲冉坐在雕樑畫棟的宮闈中,慢慢勾起脣角。 替別人奪得的終究是空中樓閣,這一次,她要爲自己爭上一爭。 直到——坐上那人人敬仰的寶座。
75.9萬字8 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