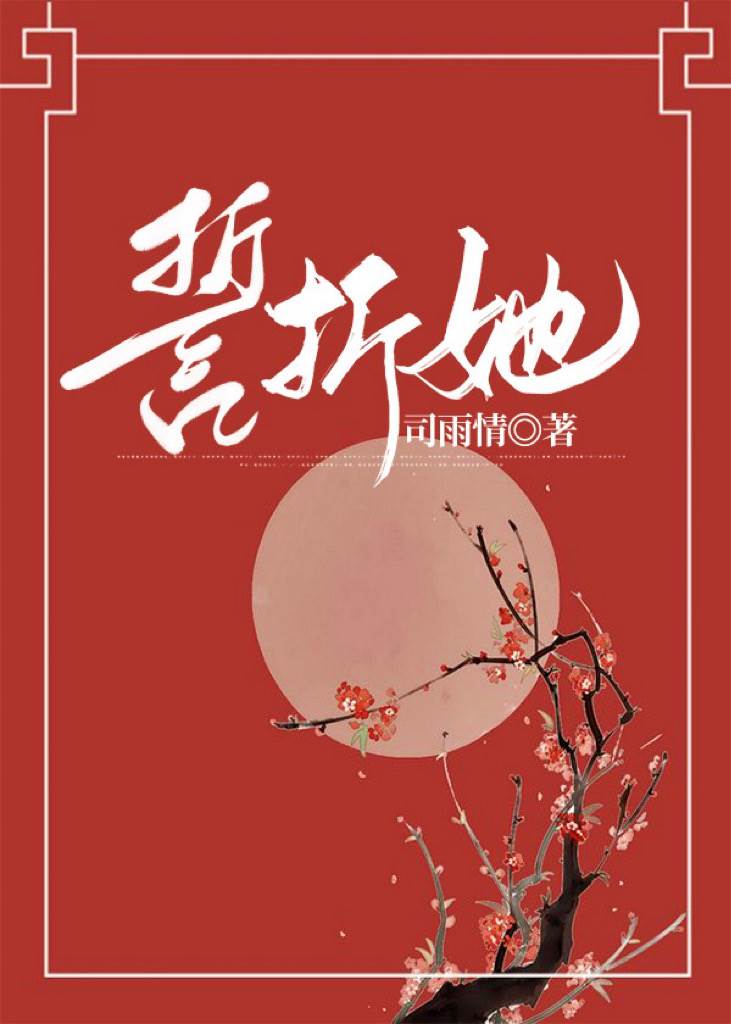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鳳月無邊》 第121章 火
盧縈這兩下作兔起鶻落,乾脆得很,一般權貴人家的姑子,也有手段狠辣的,不過們的狠辣著種驕縱,而不似盧縈這般,著種男兒的風流味道。
一時之間,四周的聲音都啞了,一個個轉過頭,怔怔地看著盧縈。
懶懶靠著船舷,好整以暇地欣賞著這一幕的貴人,面紗下的臉轉向執五,無奈地嘆道:“你說,一個姑子,怎麼就從來不在我的面前遮掩一下的壞呢?”
如他的份,不管是喜歡他還是要結他,或者僅僅是引他注意的人,都是儘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在他眼前。
眼前這小姑子,從來不在他的面前遮掩的壞,與其說,最開始時,他們的相識便是因他識破了的算計而起,沒有必要遮掩。還不如說,從來都不曾把他真正放在心上。的心穩著呢,所以在他面前,從不患得患失,從不害怕被他嫌棄。
想到這裡,貴人似笑非笑地低語道:“這個習慣,可不怎麼好!”
靠著碼頭的河水,看似淺,實際上卻是可以停放巨船的水泊,那河水深著呢。
那老婦人和一被踢到河中,便驚惶失措地拼命掙扎起來。就在們掙扎得了力,開始在河水中汩汩冒著泡向下沉去時,默默看戲的貴人朝人羣中點了點頭。
當下,兩個庶民打扮的漢子從人羣中衝了過來,他們跳到河中救起兩人,扶著們溼淋淋地來到盧縈面前張地問道:“姑子氣可消了?這鬧出人命可不好啊。”
盧縈瞟了他們一眼,扯了扯脣,冷冷說道:“滾!別再讓我看到們!”
“是,是。”一邊應著,兩人一邊拖著兩個淹得半死的人退了下去。
Advertisement
而他們一退,四周又恢復了喧譁。只是這些喧譁聲,在對盧縈時,都眼神敬畏了些。
而此刻,與盧縈同一客船的衆人,還張大,傻呼呼地看著盧縈,一副不相信自己眼睛的模樣。
還別說,盧縈這兩天扮年,當真是惟妙惟肖,當然,的長相還是氣的,可一切都抵不過眉眼中的冷,以及舉手投足間的那子強啊。這麼一個年,竟然是個應該乎乎的,藏在閨房到歲數就準備出嫁的姑子,還真讓人接不能。
那個喜歡過盧縈的也是,瞪著一雙杏兒眼,好一會才咬著脣難過地說道:“幸好,幸好我不喜歡你了……”不然,真不知道自己會有多麼傷心失。
在四周圍觀的人漸漸散去時,黑帆船上的翩翩青年,也念著笑上了岸,他明明是在百步外的碼頭上落地的,卻徑直向盧縈的方向走來。
一直走到盧縈側,青年朝打量了一眼後,低聲笑道:“敢問姑子貴姓大名?”
盧縈瞟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青年笑笑道:“姑子不說,在下也查得到……浪跡多年,竟是頭一回見到姑子這樣的人,著實歡喜。”
他在越過盧縈時,低語了一句“姑子雖與那人興止親暱,卻還是子吧?你那夫郎是誰家子?這樣一位人兒也不沾手,難道他已不行?”說到這裡,他著白牙惡劣地一笑,大步離去。
盧縈目送著他的背影,眉頭蹙了蹙。
這時,一眼看到走上碼頭的貴人,連忙提步跟上。
走到他後,盧縈低聲說道:“主公,我發現剛纔圍觀的人羣中混有刺客,那兩祖孫,是有備而來。我在猜想,他們原定的計劃量,在祖孫倆激怒我後,再有人趁著混,借我的手殺死們兩個或其中一人。只要出了人命,他們便有理由扣留我,然後順藤瓜地束縛住主公你了。”
Advertisement
頓了頓,盧縈瞟向人羣,得出結論“主公,這江州的府,已與匪人勾結。”
貴人慢慢回過頭來。
下,他靜靜地看著盧縈,手上的臉,他突然燦然一笑,道:“只憑著蛛馬跡,便能得出這些結論,阿縈果然聰慧。”
他微笑道:“與府勾結的,便是剛纔與你說話那人。連同那祖孫倆,也是他派過來的。只不過昨晚倉促之下,他弄錯了你的別,令得此番算計不。”那祖孫倆,只要再糾纏一會,埋伏在人叢中的刺客就會跳出來了。功敗垂,怪不得那人會沉不住氣,特意過來找盧縈說話。當然,這也是那青年自信,以爲盧縈怎麼也不會懷疑到他的上,所以敢大搖大擺地現。
“原來主公什麼都知道。”盧縈嘀咕出聲。知道,正是因爲自己連續兩次都表現不錯,貴人才跟這些。不然,便是到死,只怕都以爲一切不過偶然巧。
這時的盧縈,已經明白了。看來昨天晚上,自己與貴人在船頭你儂我儂,雖似對那幾十隻船沒有留神,可那黑帆的主人,還是不放心,還是了殺機。今番的出手,他們是想探一探自己兩人的底,然後,那人也做了順手把自己兩人滅口的準備吧?
畢竟,如果是昨晚上,客船要河道中出事,可能會查到他們上。可現在上了岸,通過遊俠兒和賤民出手,只要佈局巧妙,那是誰也查不到幕後的人的。
可惜,局被自己攪了,打草驚了蛇。
江州城十分繁華,碼頭上便人流如。客船上的人,這時都已下了船,沒有來過江州的人,這時正〖興〗的四下張著。
盧縈也是第一次來此地,也在四下張著。
Advertisement
看著看著,的心下有點失,暗暗想道:看起來與都,也沒有差多。
不管是遠的樓閣街道,還是水般的人流,還是碼頭的佈局,都與都沒有明顯的區別。盧縈以前幻想時,還以爲天下各地,城池都完全不同,風景也大異呢。
“主公,這是往哪兒去?”
“往哪兒去?”街道兩側的燈籠下,貴人的面紗被風輕輕吹拂著,令得他的聲音,也因這風有點輕錦“阿縈覺得江州如何?”
盧縈迴頭看了看,道:“通要道,繁華所在。”
一開口,便如一個通軍事之人一樣,直指要點。
啊,還真不似一個姑子。
貴人停下腳步,他看了看盧縈後,磁沉地說道:“既然阿縈覺得此地甚好,那我們就不走了。”他微笑著說道:“便在江州多留幾日,阿縈以爲如何?”
盧縈擡頭,對上他的笑,盧縈也笑道:“聽主公的。”無比恭順。
明明剛出碼頭便被人辱了,然後又從他那裡,聽到了兩人已經被人盯上的事,可這小姑子,卻依然應承得如此順溜,如此平靜。
……太不像尋常姑子了。
貴人低頭朝盧縈看了一會,出手把朝上一拉,輕輕著的頭髮,他嘆道:“阿縈,你讓我上心了……這可怎辦是好?”最後一句“這可怎辦是好”著濃濃地擔憂,彷彿他也覺得自個對盧縈上了心,對盧縈本人來說,真不是一件好事。
盧縈脣角了,忍不住點頭道:“這樣啊?是糟糕的。”眨了眨眼,盧縈認真地說道:“不過阿縈相信郎君,想郎君連滔天巨*都不曾在意,這個,郎君只要願意,也可以呼吸之間便放下盧縈,不再對阿縈上心的。”
真的很誠懇,這是無比的誠懇,漸漸西沉的太中,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中,盛滿了對他的信心,以及支持。
只差沒有大點其頭了。
貴人角了,懶得理。而一側,青人執五則是忍俊不地哧聲一笑。
漸漸的,太轉向西邊,漸漸的,夕西下……
讓盧縈奇怪的是,貴人明明說了會在江州停留一陣,這會卻牽著的手,準時朝著客船停留的方向走去。
不一會,三人便來到了碼頭上。
客船上別的人也在絡續歸來,他們看到盧縈三人,都是目一亮。
盧縈瞟了那眼神複雜的一眼,想到喜歡執五的事,不由轉頭向貴人問道:“主公,執護衛可有婚配?”
這話一出,貴人低頭,執五則騰地轉頭,警惕地盯著。
見狀,盧縈一樂,扯了扯脣,說道:“是這樣……”
才吐出三個字,猛然的,一道漫天火伴隨著慘聲,刺紅了盧縈的眼!
騰地轉頭。
然後,一陣驚嘶喊中,盧縈震驚地發現,那隻停在碼頭旁,正等著他們歸來的客船,已燃起了滔天大火。那火勢起得很猛,幾乎是船頭船尾船中一道燃起,大船上顯然還有人,有幾個人影在烈火中掙扎著,尖著,卻很快就沒了聲息!
而那慘聲中,盧縈清楚地聽到,其中有一個,正是那圓胖溫和的船主所發出來!
火實在太猛了,而隨著吹起的南風,那火勢已向停放在旁邊的另外兩隻船上蔓延開來。直到客船燃得差不多時,纔有醒悟過來的人衝河中,淘起河水滅起火來。
陡然的,盧縈轉過頭來。隔著遙遙的人羣,對上那個黑帆的主人,那個看起來風度翩翩的佳公子。
隔著無數的腦袋,盧縈地盯著那人。的目雖然鋒寒無比,卻因中間隔了太多人,那青年一直含著笑溫文地看著那燃燒的大船,都不曾留意到。
盯著那人,盧縈慢慢地說道:“主公。”
的聲音有點奇異的冰寒。貴人轉頭看來。
盧縈還在盯著,輕聲說道:“主公,我來理此事,如何?”
猜你喜歡
-
完結699 章

農門醫妃寵上天
家窮人弱?醫術在手,賺得萬貫家財,橫著走。 極品親戚?棍棒在手,揍他滿地找牙,誓不休。 流言蜚語?夫妻聯手,虐得小人自苦,猶不夠。 …… 深夜,蘇果抱著錢罐子數完錢,顰眉問:“相公,你瞧我們還缺點啥?” 宋安之漫不經心的撩著她的發:“嗯~缺人……娘子,不如我們來聊聊怎樣添個人吧。”
121.1萬字8 288981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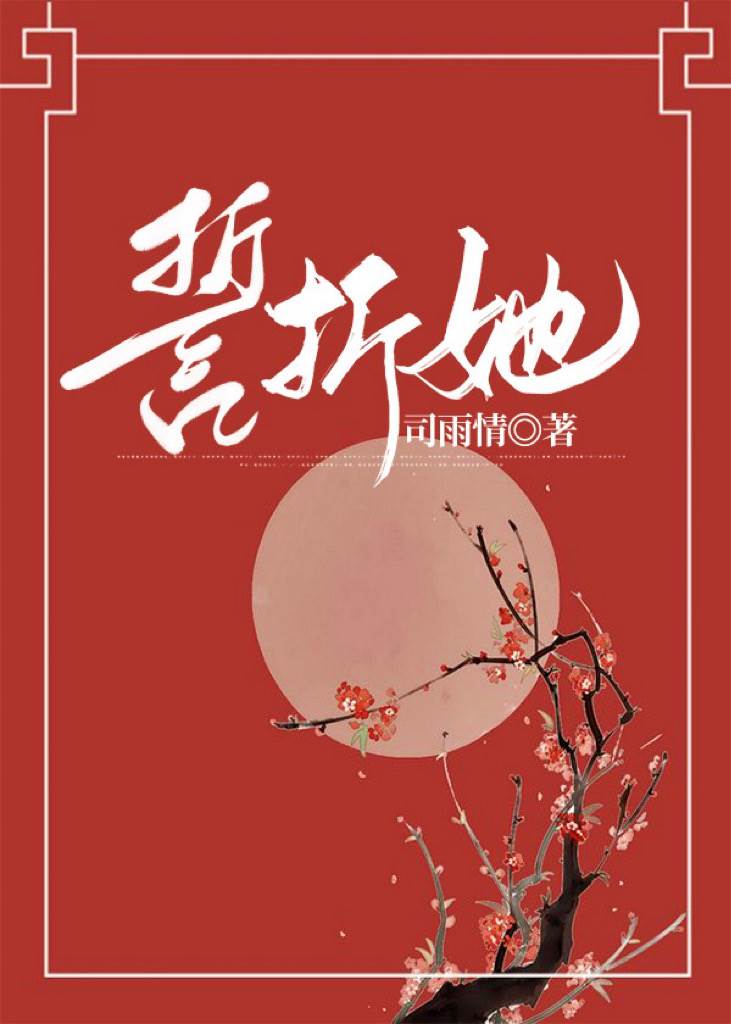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182 章

芳菲記/重生之盛寵
阿黎出生時就被睿王府討回去當兒媳婦,也就是定了娃娃親。據說是睿王府世子來吃週歲酒席,見她玉雪可愛,央着母親說要討她做媳婦兒。大人們笑過後,果真就定下來了。阿黎覺得沒什麼不好的。容辭哥哥長得好看,本事也厲害。教她讀書認字,送她華美衣裙,有時還會偷偷給她塞零嘴。後來皇帝駕崩膝下無子,睿王榮登大寶,容辭哥哥變成了太子哥哥。人人都說阿黎命好,白白撿了個太子妃當。阿黎不滿,怎麼會是白白撿的,她昨天還在太子哥哥馬車裏被欺負哭了呢。.世人都道太子殿下容辭,風姿卓絕、溫潤如玉。但只有容辭自己清楚,他是從屍骸堆裏爬出來的鬼。容辭跟阿黎做了兩輩子夫妻,可惜前一輩子他醉心權勢,將阿黎冷落在後院。他的阿黎,無怨無恨默默爲他操持家業,後來他招人陷害,阿黎也跟着慘死異鄉。上輩子重活,他步步爲營手刃仇敵,終於大權在握。轉頭想對阿黎好時,但晚了,阿黎病入膏肓香消玉隕。這輩子,他再次重生回來,早早地就將阿黎定下。權勢他要,阿黎他也要!他要寵她一世榮華!
26.4萬字8.57 37621 -
完結263 章

表姑娘
陳家有個生父不詳的表姑娘,還和京城的煞神許嘉玄結了仇。 眾人都看表姑娘熱鬧的時候,陳家卻在為這表姑娘張羅親事。 許嘉玄表示:誰娶誰倒霉。 沒過多久,給表姑娘賜婚的圣旨就砸到他頭上。 許嘉玄:???!!! 成親前的許煞神:士可殺不可辱。 成親后的許煞神:求辱。 ””追妻火葬場系
40萬字8 185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