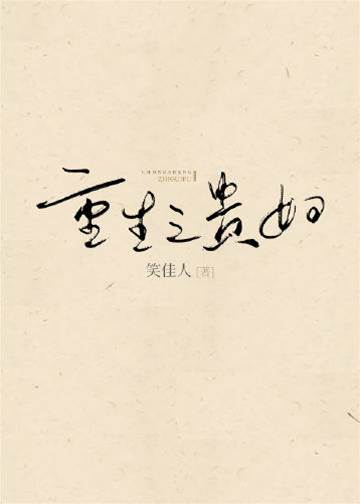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嬌娘醫經》 第47章 有說
室沉默。
懷裡的人子,呼吸勻稱。
晉安郡王忍不住擡,是又睡著了嗎?
“沒有。”程娘說道,轉頭看著他笑了笑。
晉安郡王忍不住也笑了,再躺下來子有些僵。
剛纔手抱過來是順手所爲,現在是鬆開還是……
“我也不知道對錯。”程娘的聲音在懷裡響起。
一向淡然到有些木然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聽起來反而帶著幾分和。
“我想大概最後不後悔,就是對的吧。”
後不後悔。
晉安郡王將懷裡的人抱了幾分,著清香的頭髮。
宮裡傳消息說太子又胖了很多,說太子連太后宮門都不讓出了,說吵鬧聲也了很多。
他們爲了讓他安靜不吵鬧,給他吃了藥湯。
“那幾個從慶王府跟著去的侍都已經被打發走了。”
“昨日有人的到太子宮裡看了一眼,說,太子坐在屋子裡,一不。”
抱著自己的子微微的抖,程娘手握住了攬在腰裡的手,那隻手反手握住。
“你是知道的,六哥兒他是不會安靜的坐著的…”
埋在脖頸裡的聲音有些哽咽。
“他們到底給他吃了多藥….”
“程昉我該怎麼辦?”
程娘閉著眼嗯了聲。
“我不知道你該怎麼辦。”說道,“因爲我不是你啊。”
其實有時候聽起來說話跟小孩子賭氣似的。
晉安郡王不知道爲什麼忍不住又笑了。
小孩子麼?其實小孩子說的也是實話啊。
“你啊。”他說道,胳膊再次收,玲瓏的子似乎怎麼抱也抱不住似的,語氣帶著幾分嗔怪的埋怨,“就是怕麻煩。有什麼話就說,好不好我聽。”
Advertisement
“好不好的你自己心裡有數,我何必還要說?”程娘說道。
晉安郡王就更笑了幾聲。
“可是。我還是想聽你說。”他低聲笑道,著程娘的脖子。噴出的熱氣又被回來撲在自己臉上只覺得熱烘烘的,聲音便變得有些奇怪。
就在鼻尖,是小小的耳垂,暗夜裡在烏黑的長髮間泛著亮的澤。
晉安郡王只覺得嚨有些發乾,呼吸也急促起來。
他手一,頭便湊了上去。
懷裡的人頭一歪移開了。
“你真想聽我說?”程娘問道,子半起,開了他的懷抱。
是故意的迴避麼?
晉安郡王一怔。心裡有些跳,又有些緒複雜。
“雖然說了其實最後做決定都是自己,但是,人總是願意找個藉口,寬於待已,苛刻待人。”
程娘的聲音繼續說道。
晉安郡王收起了心思,收回手支起子,笑了。
“要是別人或許我會。”他說道,“你的話,就不會。因爲別人是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說好壞,但是你是從別人的角度來說好壞的。”
程娘笑了。
“不用你誇我,我既然要說就會說。至於人怎麼怨我謝我,我會在乎嗎?”說道。
語氣裡帶著幾分驕傲。
晉安郡王看著,不知道是不是夜的渲染,眼前的子眉眼微挑,帶著幾分從未見過的神采飛揚。
他不由怔了下,就好似是另外一個人,那種鮮活的亮麗的璀璨的神采。
又似乎一眨眼,眼前的人恢復如常。
“夫人請說。”晉安郡王坐起來,端正的說道。
“你想守護六哥兒還是六哥兒的天下。”程娘問道。
這兩者還有區分?
Advertisement
“以前有。現在沒有了。”程娘又說道,似乎才反應過來出了口誤。
晉安郡王卻是神一黯。
現在的確已經沒有區別了。要想守護六哥兒,就要守護他的天下。六哥兒沒了天下,那就是沒了命….
“既然如此,你要怎麼守護他的天下?”程娘說道,“在這京城裡困籠裡就能做到嗎?”
晉安郡王擡頭看著。
“你的意思是,走?”他說道。
程娘沒有回答他的話。
“方伯琮。”說道,“你知道什麼是天下嗎?”
什麼是天下?
晉安郡王看著。
“天下,不是那個位置,而是那個位置以外。”程娘說道,“你看到過天下嗎?”
晉安郡王點點頭。
“我看到過。”他說道,微微一笑。
那巍峨的大山,大大小小的城鎮,汲汲而生的百姓,繁忙的街市,或貧瘠或沃的耕田,川流不息錯從橫的江河。
“你看到了,但是還沒跳出去。”程娘說道,“你所謂的能力不是守著一個人,而是要替這個人守著天下,不用我說你心裡也是明白的,他這樣的人登基,朝堂必然紛爭不斷,天下也必然盪,你要做的應該做的是住這天下的盪,替他震懾宵小,替他安百姓,江山百姓安穩,這纔是天下安穩,纔是穩住他的江山。”
“你要自己變得強大,這個強大不是爲了一個人強大,而是爲了很多人。”
“這個強大要錢要人要能力,更要的是要有施展的天地。”
“京城,不是你的天地。”
………………………….
顧先生等人進來時,天才亮,屋子裡晉安郡王已經在了。
Advertisement
這麼早?
顧先生愣了下。
“天不亮已經來了。”景公公低聲說道。
天不亮?
“又跟王妃鬧彆扭了?”顧先生挑挑眉低聲問道。
景公公撇撇。
“哪裡捨得。”他說道。
這邊二人低語幾句,看著晉安郡王始終粘在屏風前不。
那裡掛著一幅輿圖。
“殿下?”顧先生走過去說道。
晉安郡王手指著一點。
“鬆平是在這裡吧。”他問道。
鬆平?顧先生愣了下,旋即含笑點點頭。
“是,就是這個方位。”他說道。
晉安郡王便手在輿圖上丈量一下。
“從這裡到這裡…”他的手指停在京城,微微一笑,“也不算很遠啊。”
顧先生眉頭一跳。
“有時候遠的不是距離。”他說道。
遠的是機會。
晉安郡王轉過。
“準備準備。我們離開京城。”他說道。
“離開?”
顧先生等人驚訝的看著晉安郡王,以爲自己聽錯了。
這一大早就把他們進來還以爲是繼續安排進京的人呢,沒想到竟然是出京。
“只是我出京城。”晉安郡王說道。“那些人還是要進來的,正因爲我要走了。京城才一定要留更多的人,而且是城防要留足夠的要的人手。”
自來城防是要務,就如同京城的咽。
顧先生點點頭,不過,現在要說不是這個。
“不過,爲什麼要走?”景公公急道,“且不說他們會不會放我們走,就說這一走。路上可是十分的兇險。”
離開京城,漫漫路途,遇上個意外簡直太稀鬆平常了。
“沒有爲什麼,只是該走了。”晉安郡王笑了笑,“不是嗎?阿景,四年前我們就該走了。”
“可是…”景公公皺眉。
四年前能走的時候不走,現在想走卻已經沒那麼容易了。
“我知道。”晉安郡王說道,目看過屋中的人,“雖然遲了些,但也還算不晚。”
景公公要說什麼。顧先生先開口了。
“不晚,那有什麼晚不晚的,只要殿下想做。咱們就做就是了。”他整容說道。
“可是,現在走太危險了。”景公公急道。
顧先生看向他搖搖頭。
“錯了景公公。”他說道,“我們從來都很危險。”
既然都危險,也就沒有什麼過去曾經現在的區分。
景公公一愣。
“殿下,殿下。”
門外有人急匆匆進來,屈施禮。
“高凌波被罷黜了。”
什麼?
屋中的人皆是一驚。
不過旋即大家又冷靜下來。
高凌波被趕出朝堂一直在說,只不過偏偏次次都沒有功。
“陳相公說的嗎?”顧先生皺眉,“他還有什麼理由要驅逐高凌波?”
以前以外戚擅權,現在呢?他自己都了外戚了。
“不是陳相公。”來人說道。擡起頭,“是秦侍講。”
秦侍講?
屋中的人再次驚訝。
“而且。用的是皇帝上諭。”來人接著說道。
這一次連晉安郡王都出驚訝。
皇帝上諭?
……………….
“他孃的胡說八道信口開河!”
此時的高小人正大聲的喊道,在屋裡揮舞著手。
“哪裡來的皇帝上諭。睜眼說瞎話呢!皇帝要是能上諭,還到他們在朝堂上吵鬧不休!”
“小人,是起居注上所載。”一個幕僚說道,帶這幾分苦笑,“秦侍講拿出了皇帝的起居注。”
……………………
“起居注算什麼上諭!”
皇宮太后一把扯開簾子喊道。
“那不過是陛下的口頭閒語,還有玩笑話也有氣話,怎麼能當上諭!”
“玩笑話?”秦侍講面容一沉,握著手中的幾卷冊子,“陛下聖人金口玉言,不管是前朝後堂,遵從禮儀,從不虛言笑談,起居注記載也絕非是什麼口頭閒語,娘娘這樣說置陛下於何?”
他說罷展開一卷。
“陛下曾親口說出,待太子得定,高凌波當歸去,娘娘如果不信,臣就將起居錄念一遍,娘娘以及大家都來聽一聽,看看陛下論朝中人事是否是隨意玩笑。”
開什麼玩笑!
朝臣們面微變,誰知道還能念出什麼皇帝說哪個大臣的話來,好話也就罷了,壞話豈不是敗壞了名聲。
如今皇帝不醒,太子癡傻,太后又鬧出幾場笑話做出無知婦人狀,那秦侍講手裡的起居注相比起來,倒是最有分量的話了。
死道友不死貧道,當下便有好幾個朝臣站出來贊同秦侍講的話,認爲起居注不是戲言,更多人則選擇了沉默。
“哀家不同意。”太后氣的瞪眼說道。
陳紹在一旁端正而立,拱拱手。
“既然太后不遵從陛下的旨意,那日後太后的懿旨,中書門下也不能遵從,只能一概封還了。”他淡淡說道。
太后氣結,指著陳紹。
你,你,這不是欺負人嗎?
陳紹神木然。
欺負人,誰不會啊。
二更在晚上,嘻嘻……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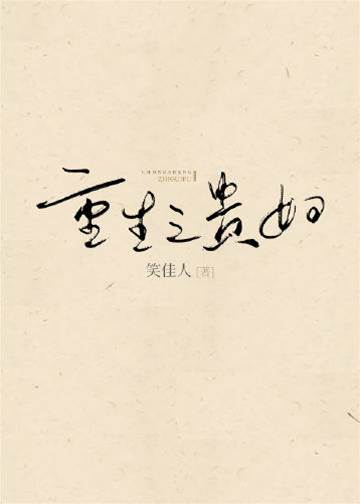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828 章

我是旺夫命
一朝穿越,鐘璃不幸變成了莫家村聞名內外的寡婦,家徒四壁一地雞毛也就罷了,婆婆惡毒小姑子狠心嫂子算計也能忍,可是誰要是敢欺負我男人,那絕對是忍無可忍!我男人是傻子?鐘璃怒起:這叫大智若愚!他除了長得好看一無是處?鐘璃冷笑:有本事你也那麼長。鐘…
170.9萬字8 233467 -
完結149 章

開封府美食探案錄
開封府來了位擅長食療的女大夫,煎炒烹炸蒸煮涮,跌打損傷病倒癱,飯到病除!眾人狂喜:“家人再也不用擔心我的身體!”但聞香識人,分辨痕跡……大夫您究竟還有多少驚喜是我們不知道的?新晉大夫馬冰表示:“一切為了生存。”而軍巡使謝鈺卻發現,隨著對方的…
45.8萬字8 13472 -
完結930 章

毒醫狂妃:誤惹腹黑九王爺
傳聞,相府嫡長女容貌盡毀,淪為廢材。 當眾人看見一襲黑色裙裳,面貌精緻、氣勢輕狂的女子出現時——這叫毀容?那她們這張臉,豈不是丑得不用要了?身為煉藥師,一次還晉陞好幾階,你管這叫廢材?那他們是什麼,廢人???某日,俊美如神邸的男人執起女子的手,墨眸掃向眾人,語氣清冷又寵溺:「本王的王妃秉性嬌弱,各位多擔著些」 眾人想起先前同時吊打幾個實力高深的老祖的女子——真是神特麼的秉性嬌弱!
153.2萬字8 334465 -
完結371 章

惑君
嫡姐嫁到衛國公府,一連三年無所出,鬱郁成疾。 庶出的阿縈低眉順眼,隨着幾位嫡出的姊妹入府爲嫡姐侍疾。 嫡姐溫柔可親,勸說阿縈給丈夫做妾,姊妹共侍一夫,並許以重利。 爲了弟弟前程,阿縈咬牙應了。 哪知夜裏飲下嫡姐賞的果子酒,卻倒在床上神志不清,渾身似火燒灼。 恍惚間瞧見高大俊朗的姐夫負手立於床榻邊,神色淡漠而譏諷地看着她,擡手揮落了帳子。 …… 當晚阿縈便做了個夢。 夢中嫡姐面善心毒,將親妹妹送上了丈夫的床榻——大周朝最年輕的權臣衛國公來借腹生子,在嫡姐的哄騙與脅迫下,阿縈答應幫她生下國公府世子來固寵。 不久之後她果真成功懷有身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嫡姐抱着懷中的男娃終於露出了猙獰的真面目。 可憐的阿縈孩子被奪,鬱鬱而終,衛國公卻很快又納美妾,不光鬥倒了嫡姐被扶正,還圖謀要將她的一雙寶貝兒女養廢…… 倏然自夢中驚醒,一切不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看着身邊沉睡着的成熟俊美的男人,阿縈面色慘白。 不甘心就這般不明不白地死去,待男人穿好衣衫漠然離去時,阿縈一咬牙,柔若無骨的小手勾住了男人的衣帶。 “姐夫……” 嗓音沙啞綿軟,梨花帶雨地小聲嗚咽,“你,你別走,阿縈怕。” 後來嫡姐飲鴆自盡,嫡母罪行昭彰天下,已成爲衛國公夫人的阿縈再也不必刻意討好誰,哄好了剛出生的兒子哄女兒。 形單影隻的丈夫立在軒窗下看着母慈子孝的三人,幽幽嘆道:“阿縈,今夜你還要趕我走嗎?”
61.6萬字8 10053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