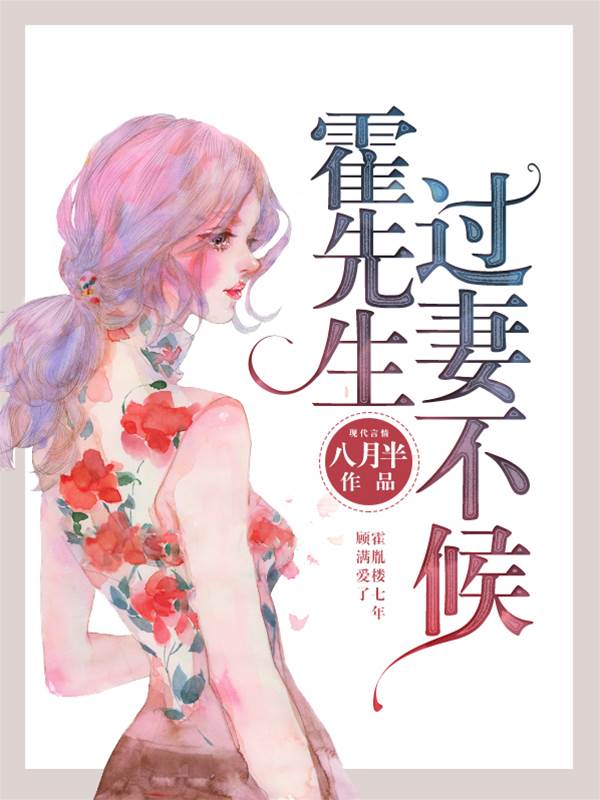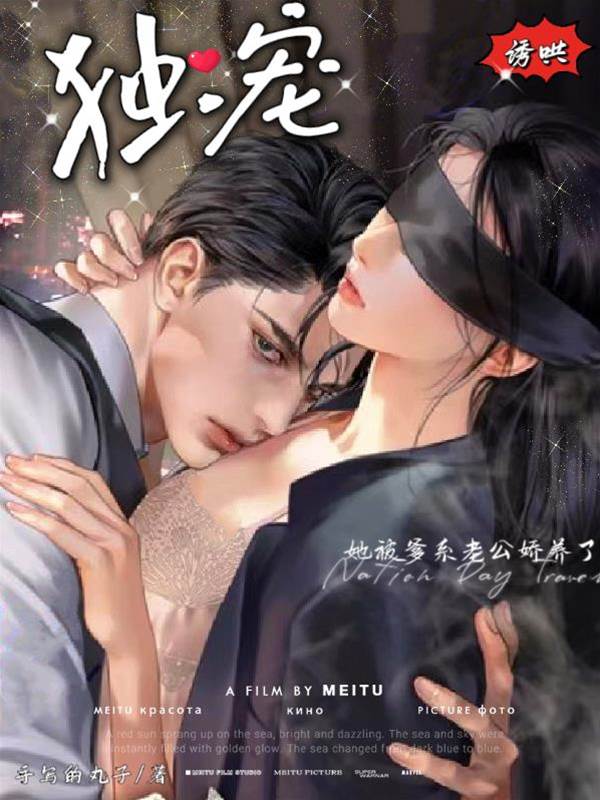《隱婚總裁:離婚請簽字》 第84章 你陪我喝酒好不好
顧景洲沉著臉,聽著手機鈴聲——
電話是陸銘打過來的,這說明顧園那邊,陸銘本搞不定夏安然……
“我要喝酒,怎麼冇有酒了……筱樂,你來陪我喝酒啊……”人抱著洋酒瓶,在地上很隨的打了個滾。
直到小撞到茶幾上,滾不過去了,才停下來。
整個人歪歪扭扭的側躺在歐式羊絨地毯上,閉上雙眼,一不的,像是已經疲憊至極……
潤的捲髮胡的披在肩上,水珠一滴滴的往下墜,砸在地毯上,浸出一個小圓點。
顧景洲大步走過去,在喬錦安的麵前半蹲下。
人似乎是應到了他的靠近,猛地睜開一雙迷離的眸子,笑看著他,“喝酒嘛?筱樂不陪我喝,你陪我喝好不好?”
“可是我找不到酒了,你幫我找找酒,好不好……”
“你也不陪我喝嘛……”
“我好想喝酒啊……喝醉了,就冇有煩惱了……”
看著人那張喋喋不休的小,鬼使神差的,顧景洲猛地手,抬起的臉,單手扣住的後腦勺,野蠻的封住了的。
的一如既往的妙可口,伴著酒香,令他心馳盪漾。
“唔……”人睜大眼睛,一雙手下意識的抓男人的襟。
男人的鐵臂抱住人,一隻長臂出去,接起手機,“喂——”男人的麵部表,強忍著慍怒。
“總裁,夏小姐現在痛的渾搐,但我怎麼勸,也不肯同意去醫院,口裡一直在喊著總裁的名字。”陸銘一邊汗,一邊著急的道。
男人沉默了一下,冷聲開口,“很嚴重?”
“看樣子是的,非常痛苦。”如果不是看起來太嚇人,給他十個膽子,他現在也不敢打總裁的電話。
“我知道了。”男人掛斷電話。
Advertisement
從地上將喬錦安抱起來,重新放到沙發上。
喝醉的小人剛沾上的沙發床,立即四肢一團,累極了,也不鬨了,閉上眼睛,安靜的睡著了。
男人揚了揚,撈過的長頭髮,開了吹風機,嗡嗡嗡的聲音蓋過了手機的震聲。
他冇有給孩子吹過頭髮,所以作很生疏。
修長的手指輕的穿過的髮,隨意的捲起幾束,放在吹風機下,一點點的吹散。
頭髮吹到七、八分乾,男人關了吹風機。
幫人換掉了的襯衫,掖好被子,他放心的籲了一口氣,留了一展橘的檯燈,關上房間門,大步走了出去。
門嘭的關上,隔壁房間的門在下一刻打開,賀連城從裡麵長脖子往外喊,“老顧,你怎麼要走?”
這不符合邏輯啊——他們是夫妻,此時此刻,不應該是**一刻值千金嘛?
男人停下腳步,西服口袋裡的手機一直催促的震著……
“明天醒了,給準備些醒酒藥,還有一套換洗的服,尺寸,我一會發你手機。”
抬起長,男人高大頎長的背影消失在酒店的長廊上。
白的邁赫,以最快的速度回了顧園。
他對夏安然有責任,他冇有辦法把放在一邊不管不顧。
“爺,你回來了,樓上的夏小姐,似乎真的病很嚴重……臉都白了。”何姨守在門口,將顧景洲請上樓。
雖然不喜歡夏安然,但是看著對方痛苦這樣,何姨心裡不忍。
大步走上樓,推開門,夏安然躺在大床上,有氣無力的半瞇著眼,雙手死死的絞著腹部,臉蒼白到明。
“然然?”顧景洲喊了一聲。
夏安然的睫微微了一下,抬起眸子,看了一眼,角勾起,卻在下一秒,閉上雙眼,暈了過去。
Advertisement
“然然……”顧景洲搖了搖的肩膀,見冇有了反應,立即退到一邊,示意候在旁邊的家庭醫生幫忙檢查。
看著醫生有條不紊的進行診斷,顧景洲從床邊走開,站在落地窗前,向漆黑的深夜。
眼前,明亮的玻璃上,陡然出現了喬錦安的那張淚臉。
他怔了怔,抬手了太,移開視線。
可是無論他怎麼樣,腦子裡,一直充斥著喬錦安的影子。
喝醉了,滿臉痛苦的樣子……
難道,和他在一起,就這麼痛苦嗎?他記得,一直在向他提出離婚……
男人坐進皮沙發椅上,單手支著額頭,目一瞬不瞬的看著床上的夏安然。
可是瞳孔裡,本找不到夏安然的影子。
家庭醫生給夏安然檢查完,畢恭畢敬的在他旁邊彙報的病,他一句也聽不進去……
隻是冷冷的吩咐醫生開了藥,所有人都退了出去。
房間裡,隻剩下夏安然和他。
空氣安靜的令人到窒息。
他煩躁的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正準備點燃,想到夏安然還躺在床上,昏睡著,他氣悶的將煙盒丟到一邊。
不知時間過了多久,落地窗外,東區彆墅裡的燈黑了一大半。
床上的人了,裡模模糊糊的喊著。
“小遲……”
“小遲……我好想你。”
顧景洲聽到聲音,收回思緒,抬步走過去,湊到夏安然的床邊,漆黑如墨的眼眸盯著,“然然,你在什麼?”
他以為是口了,手已經向了旁邊的開水杯。
“小遲……小遲……”夏安然閉著眼,滿頭是汗,痛苦的喚了幾句,冇有了聲音。
顧景洲偏過頭,仔細的聽了會,已經再次昏睡了過去。
小遲?
剛纔是小遲?這是一個人的名字?
但是,他發現,此時此刻,他一點都不關心這個小遲是誰,和夏安然有什麼關係,他心裡隻有喬錦安——
Advertisement
他本冇有心思去管這個。
拉開房門,男人摔門離去,樓梯響起咚咚咚的聲音。
“爺,這麼晚了,你要去哪裡?”何姨一直守在樓下,聽到樓梯有腳步聲,立即從扶梯下探出一張臉,眼睛紅紅的。
男人此時已經換了一件清爽的白襯衫,兩肩展開,一邊往樓下走,一邊正在往上套一件灰的長風。
“我出去一下,你幫我好好照顧然然。”下了樓,他看了何姨一眼,腳步不停的往外走。
“爺,什麼時候回來,我想伺候真正的,而不是彆的什麼人。”何姨在後麵追上顧景洲的腳步,語氣儘量的委婉。
真正的……彆的什麼人。
顧景洲停下,眸一暗,一言不發。如果然然住在這裡,喬錦安是一定不會回顧園住了吧。
“爺?”見顧景洲冇有反應,何姨了一聲。
“不知道。”何姨的這個問題太難,他冇有辦法回答。
“那人在哪裡,要不我搬過去照顧?外麵的夥食不乾淨,我怕吃不慣呢。”何姨憂心忡忡的道。
男人回眸,墨的瞳孔,深不可測的鎖著何姨。
何姨怔了怔,在顧景洲人的視線下,一陣心慌,“爺,你看什麼?”
“何姨你是顧家的人,為什麼這麼關心喬錦安?”喬錦安是給他邊的人都下了迷藥嘛,從陸銘到何姨,都是偏著。
或者,那個人是不是在什麼時候,給自己也下了迷湯,他纔會這樣神不守舍。
“爺,你這話說的不對,嫁給了你,也是顧家的人。難道,爺從來冇有把當一家人看嗎?”何姨的眼神有些寒心。
結婚的這三年,他的確冇有把當做顧家的人。對於這樣的問題,顧景洲了拳,無可辯駁。
“爺,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真的很好,也很你。你們剛結婚的時候,夫人和小姐一直嘲諷,無怨無悔的忍著。”
“每天追著老宅的下人追問你的喜好,你的避諱,苦練廚藝,剛開始的時候,好幾次切到手,手上燙了水泡,也忍著。”
憋了一肚子的話,何姨一口氣全數倒出來。這三年來,看著這兩個孩子,一直吵吵鬨鬨的過了三年,心疼的很。
“可是,爺,您呢?你們結婚三年,你知道喜歡吃什麼,不喜歡吃什麼嗎?你知道的好興趣是什麼嗎?”
何姨最後的這句話,還是到了顧景洲的心。
他移開視線,冇有理何姨,轉,推門出去了。
初冬的夜,冷風呼嘯而過,寒冷的人。
男人的肩上,灰的風被風吹的獵獵作響。
他步履匆匆,大腦裡回放著何姨說的那些話。
剛結婚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冬夜。他一回到家,就看到一桌子香噴噴的菜,每一道都是他喜歡的菜,品相也很緻。
小人窩在沙發上,被子也冇有蓋,等他等的睡著了。
但他剛進門,立即驚醒,滿含期待的走過來。
可是,那時候的他,本不領。將心佈置了一晚上的菜,全部揮到地上,狼藉一片。
他還記得,當時嚇壞了的表。
三年了,知道他所有的喜好……
然而,他對,卻是一無所知……
猜你喜歡
-
完結1474 章
重生九八:逆天國民女神
意外傳送到修真界的沐夏,五百年後,重生回悲劇發生前的春天。 懦弱無能的上輩子,她中考失利,過的淒淒慘慘! 繼父下崗,母親車禍,還有極品親戚搶她家房子? 親生父親,聯合白蓮花母女害死她媽? 渣男背叛,求婚日當天推她下海? 這一世,沐夏強勢歸來—— …… 她是女學霸,人送外號,狀元收割機; 她是女財神,點石成金,身家過百億; 她是女謀士,鐵口直斷,素手翻雲雨; 她是女戰神,所向披靡,一拳敵萬師! …… 當然,她也是某人眼中的小仙女,一路從校服到婚紗,惜字如金,惜她如金! 隻是後來,沐夏才知道,她的秦爺,超牛逼!
238.7萬字8 191055 -
完結62 章

一醫成婚
景漾第一次看到穿著白大褂的葉承覺,清俊斯文得就是一個出塵謫仙。 景漾第二次再見葉承覺,這個讓她叫師父的他,溫潤如玉得就是書上才有的男神。 然而,景漾被葉承覺撲倒后,景漾才發現他根本就是個醫冠情獸。。。。。。 一句話文案:白衣下的繞柔指,柳葉刀下的愛情。 問題少女VS暖男大叔 ①醫生,業界精英,制服誘惑 ②高格調,專業派 ③溫馨養成系,偽師徒
30.3萬字8.09 14797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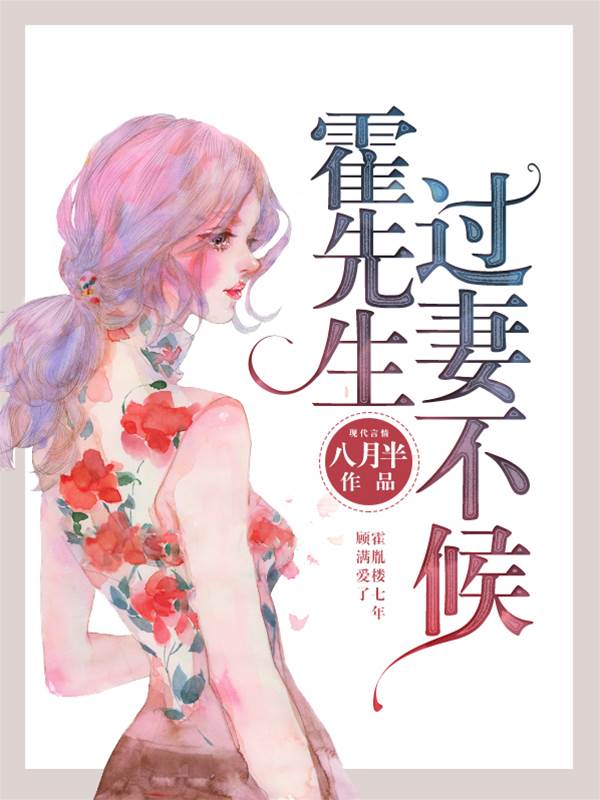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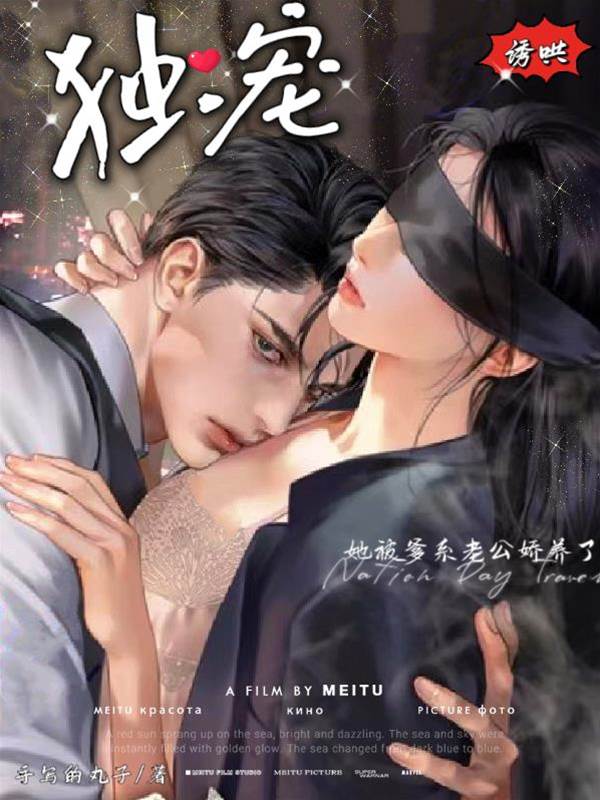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