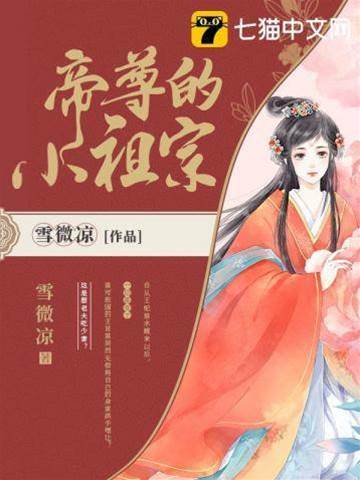《嫡女難求:殿下你有毒》 099大爺敢做敢當
櫟如故其實已經注意了他好一陣子。因為在的印象中,陳夫子的確稱得上是個好夫子。他從來不會偏幫任何人,因而這一次行事之前沒有和他報備,他不知道的目的,自然是要挑錯的。
不過櫟如故並不是很擔心。
南宮彥青的六壬星圖練到了第九層,已經是常人無法企及的一個高度。到了他這種水平,不需要任何武,世間一切皆可作為武。
倘若旁人利用暗發力,需要暗是飛鏢、是石子等的東西,南宮彥青可以做到將一片草葉、一髮擲出,就達到相應的效果。
當然,一髮還是誇張了些,等他突破了十級或許可以,如今卻還沒到那樣爐火純青的地步。
先前在林中,南宮彥青下手就還需將草葉碎球來著。
一不行,兩、三……
扯下三斷髮,作一團,疾而出。
這力道或許傷不了人,但對於一個被櫟如故刻意放在邊緣的花瓶來說,卻已經足夠了。更何況,櫟如故是刻意挑選了一個又高又瘦又輕的花瓶在那裡呢。
南宮彥青擊中最上部,相當於有槓桿定理的加,那花瓶落地便也不算奇怪了。
然旁人去看,卻是看不出半點蛛馬跡的。
「肅靜。」陳夫子開口,卻也抓不到櫟如故的錯,隻能先勒令大家安靜,「花瓶落地或許隻是巧合,大家不要相信無謂的鬼神之說。」
櫟如故不服,「陳夫子,學生有一問題想要請教。」
看到是櫟如故,陳夫子莫名有一種不佳的預。但人家好端端地問自己問題,表述也很有禮貌,陳夫子找不到理由拒絕,隻好道「但說無妨。」
櫟如故微微俯首,道「夫子方纔說,這世間並無鬼神,可有依據?」
Advertisement
陳夫子一愣,旋即道「世間萬發生與結束都有其特定的規律,所謂鬼神,不過是人見到一些無法用常理解釋的現象,而杜撰出來的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藉以安自己、欺騙自己。
我們所有人都在害怕鬼神、敬畏鬼神,可又有誰真正見過鬼神?我們先不談鬼。倘若真有神明,倘若蒼天真的有眼,這世上又怎麼會有無辜枉死之輩?」
櫟如故又俯首「夫子大義。」
頓了頓,又道「然即便如此,夫子還是不能證明世上沒有鬼神不是嗎?沒有見過就不存在嗎?夫子可知為什麼捂住人的口鼻,我們就會窒息而死?因為這看似『無』的萬千世界,充滿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一種氣,或者夫子可以理解為一種看不見不著的質。
看不見並不等同於不存在,所以抱歉,即便沒有人見過鬼神,學生也不能認為您說的是對的。夫子不能,學生卻可以證明這世上真有鬼魂。既如此,夫子為什麼要固守己見,不願去嘗試去麵對新的事呢?」
對於櫟如故的話,陳夫子仍是不贊同的,但話都說到了這份上,倘若不讓做出點什麼,就是他心虛似的。
陳夫子雖然不贊同,卻還是勉強道「既然如此,你就試試,老夫倒要看看,你如何證明。」
「簡單,我已經請了大師做法。大師說了,咱們屋子裡之所以有邪祟作怪,乃是有人在四周埋了金破了風水。金本就是忌諱件,倘若有人利用其作法,那後果自然是不堪設想,碎幾個花瓶都算是輕的。」櫟如故道,「那金被施了法,大師找到它的位置需要一些時間,夫子不必在意,咱們隻管上課就是。
再過一會兒,那金沒準自個兒就會現了。」
Advertisement
一番話說得玄玄乎乎的,櫟南依聽著皺了眉。這世上有沒有鬼神不知道,有沒有那樣厲害的大師,也不知道,但卻知道,屋子四周的確埋了金,是一柄短劍,親手埋的。
但蒼天可鑒,之所以把劍埋在那裡,隻是因為不方便帶出去,臨時找了個地方安放罷了,什麼鬼怪作祟,什麼被施法的金,什麼破壞了風水……
多半是櫟如故早就發現了那柄短劍,想要借題發揮。
那柄短劍學的時候就帶了,雖然不是人人都見過,但知道那柄短劍的存在的,卻也不止一兩個人。
看櫟如故的口風,完全沒有放過的意思,若那一柄短劍當著大夥兒的麵被挖了出來,那真是有一百張也說不清了!
不行,絕對不能被人發現。
劍是的已經是既定事實,從這個角度出發已經絕了出路,唯一能做的……
對,趁著櫟如故「作法」的時間,就要找機會去把那劍挖出來帶走!
讓知道什麼做人心不足蛇吞象!
不管櫟如故知不知道對付的那個人是自己,現在不是想要將拖深淵嗎?就偏不能讓得逞。
隻是……
倘若櫟如故知道背後之人是,自己的舉豈不是通通落了眼裡?應該怎樣,才能在櫟如故的眼皮子底下將劍拿出來?
櫟南依的目對上了一個人。
從容地從座位上站起,如同往常一般裊裊朝著一名男子走去,隻不過這一次,的件換了楊棟天。
「楊公子。」櫟南依隻微微一笑,就惹得楊棟天兩眼發直。
「櫟、櫟姑娘,有什麼事嗎?」
楊棟天癡迷櫟南依已久,卻一直不得櫟南依一個好臉。如今佳人主坐到了自己的邊,還對著自己眼如,他哪裡還坐得住,七魂都被勾去了一大半。
Advertisement
這種時候,恐怕櫟南依讓他為自己兩肋刀,他都是樂意之至的。
「楊公子,其實我……」櫟南依言又止,模樣我見猶憐,「其實我慕你已久,隻是苦於禮教之法不敢傾訴。卻也沒有關係,反正、反正我如今都要去死了,這些話再大逆不道,說出來也就說出來了。」
櫟南依說話的時候,人已經靠在了楊棟天的肩頭,湊在了楊棟天的耳邊,聲音是極小的。
若是放在平常,這樣的作勢必會引來眾人的圍觀,然而今日,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櫟如故和陳夫子上,一時之間無人發現的這一點兒小作。
唯有打從一開始就注意著櫟南依的櫟如故,隻用餘瞥了瞥,便又收回了目,並不打算打草驚蛇。
「姑娘為何如此說?」楊棟天嚇得後退一步,「莫不是姑娘得了什麼不治之癥?」
櫟南依看著楊棟天的一口黃牙,沒來由覺得一陣噁心,麵上卻半點不顯,出一副委屈的神道「公子怎麼這樣胡揣測?我、我隻是……不說也罷,既然公子沒有興趣聽,我也不是那等隨意之人,就此別過。」
一聽不是得了惡疾,楊棟天麵上神又變,笑著拉扯櫟南依的袖子,「都是我的錯。姑娘既然不是得了不治之癥,又怎麼會命不久矣呢?可是遇到了什麼沒辦法解決的大麻煩?給我去辦就好。」
楊棟天大手一揮,雖然說出的話未必能夠辦得到,氣勢卻是十足的。
他怨恨地看了那邊的櫟如故一眼,快速收回目。那小子考進來了,還名列前茅。當初他和行知書院的人舉報的時候,那些人分明說了要去找他算賬,怎麼這小子不但進來了,還混得如此好?
竟然還敢與陳夫子板了。
這還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
若不是因為他,他又怎麼會被南宮彥青警告?一個一個的,全他媽不是好貨!現在倒裝得一副人模狗樣的樣子,給誰看呢!
楊棟天的目落在櫟如故上的時候,一向敏銳的櫟如故自然也覺到了。借餘看了一眼,才發覺竟然是個人。
他方纔側對著自己,櫟如故沒看清他的臉,剛剛轉才瞥見了一些。
就算對那一張臉沒有多麼深刻的印象,櫟如故對他那一口黃牙卻是印象頗深。嘖嘖,真不知道櫟南依是如何忍住噁心對他笑如花的。
不過令櫟如故好奇的是,楊棟天這種蠢貨,竟然也考進了行知書院?不是說行知書院的門檻很高麼?如此看來,傳言也不可信。
別人的水平不知道,楊棟天的水平……
實在搬不上檯麵啊。
「公子,公子?」
「啊?姑娘你剛剛說了什麼?」被了兩聲,楊棟天這時纔回過神來,「抱歉啊櫟姑娘,我剛剛沒聽清,你看你能不能再說一遍?」
櫟南依麵不改,道「是這樣的。我前些日子在屋子外頭的那一棵大樹下埋了一柄短劍,但是公子你相信我,那真的就是一柄普通的短劍而已,不存在什麼作法的。但我琢磨著,除了我那一柄短劍,應該也不會有別人把金藏在地下了,勾言說得那個人很可能就是我。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定是因為我前些日子辱罵了他,他懷恨在心,所以才編出這樣一個謊言來害我!所謂的什麼大師也一定是和他串通好了,就為了把髒水潑到我的上!
我也就能快活這些時辰了,等這堂課一下,大家跟著夫子和勾言一起出去了,一切就都完了。他們看到了那一柄短劍,知道劍是我的,一定會相信勾言說的話,到時候隻要勾言再煽風點火,我肯定就沒命了!」
櫟南依佯裝掩麵哭泣,「這些其實本來不告訴公子也無妨的,可我即便是要死了,也不想公子誤會於我,我真的不是勾言說的那種人!公子你想想,我與大家素昧平生,何苦作一個這樣的陣法陷害大家?
那些本都是勾言為了報私仇編出來陷害我的故事!隻可惜故事信的人多了,也就不再是故事了。」
楊棟天聞言,陷了短暫的沉默。
他也不是個傻子,聽到櫟南依的話,哪裡不知道是在利用自己?可即便是利用,櫟姑娘為什麼選擇了自己,而不是選擇別人呢?可見對自己還是有好的。
人喜歡另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很容易為對方哪怕是很明顯的錯誤找出理由,試圖安自己。
楊棟天堅信櫟南依心中是有他的,但僅僅是這樣,還不足以讓他貿然應下此事。
他也怕死,也怕一個弄不好,這件事的罪魁禍首就了他。但一聽到「勾言」二字,他一直抑著的怒火驟然升騰,登時什麼都不顧了,當即應下了櫟南依的請求,「櫟姑娘大可放心,我一定替你辦好此事。」
櫟南依心中竊喜,麵上卻是一副喜出外的表,「真的嗎?這樣不會太冒險嗎?真是謝謝公子了,我都不知道該怎樣謝公子纔好!」
「櫟姑娘隻要說我該怎麼辦就行了。」
「很簡單,趁著大家都不注意,去門口把樹下的短劍挖出來帶走,臨時丟棄也可以,總之就是讓它離得越遠越好!」
兩人商談的時候,櫟如故正在和陳夫子講述一些微末之事,比如那個傳說中的大師是如何如何的厲害,道行是如何如何高。
然而,正在討論鬼神是否真的存在的陳夫子,卻在櫟如故刻意的引領下,忽然向櫟南依的方向瞥了一眼,而後迅速收回了目。
兩人又談了些別的什麼,臺下眾人也聽不太清楚,隻以為他們在談什麼高深的問題,頗為好奇地盯著兩個人。
誰也沒有注意到,就在楊棟天離開之後的下一瞬間,南宮彥青也溜出了屋門。
「啪。」
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眾人一跳,南宮彥青像拎小一般提著楊棟天的後頸,將他丟進了屋子裡,「本宮當是什麼人作祟,原來又是你。」
楊棟天從小生慣養,哪裡經得住南宮彥青這一摔,登時痛得齜牙咧,了一團。
眾人的目挪到他上的時候,同時看到了他手裡抱著的那一柄短劍,劍上還沾了泥。
猜你喜歡
-
完結257 章
庶女
人家穿越都當公主王妃,爲什麼她只是個不受寵的庶女?是庶女也就算了,爲啥嫡母總是想著法子虐待她呢?好吧!難得重生了一回,她決心要輪圓了活一把!嫡母要害她是吧?沒關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你用陰謀,我就用陽謀讓你沒臉!嫡姐欺負?沒關係!她可不是軟柿子,哪由得你來搓圓搓扁?只是,再聰慧靈巧,也敵不過封建家長的專制.無奈,她被迫嫁給一個雙腿殘疾王府次子.可是,等嫁過去才發現——原來,一切都不是她想像的那樣…新婚之夜,揭開蓋頭,她看著自己的新郎錯不開眼——世上還有更漂亮的男人麼?而新郎,他卻含羞帶怯的低下頭,輕啓紅脣:花癡!他貌似柔弱,常常睜著如小鹿斑比般的清澈大眼看她,卻在她最沒有防備時,將她吃幹抹淨,還讓她捨不得責怪半分.冷華堂,堂堂簡親王世子,曾用最卑鄙的手段得到了位子,又肖想不該喜歡的人,最後,終於敗在了某個小女人手上.
136.2萬字7.73 33088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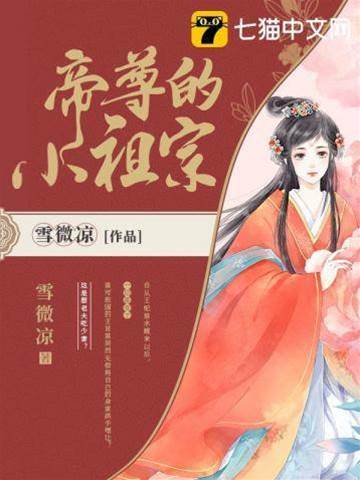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82 章

繼兄折娶
沈幼宜幼時隨二嫁的母親入了鎮國公府,此後她有了繼兄,郎豔獨絕的世子崔絡。 繼兄不苟言笑,冷淡疏離,沈幼宜有些怕他。 直到自己受人欺凌,繼兄替她撐腰,她才知他面冷心善。 繼兄對她好,沈幼宜便大着膽子親近他。 朝夕相處,兄妹間感情甚篤。 及笄之年,繼兄忽地冷淡下來,沈幼宜心中酸澀,寬慰自己:他們畢竟不是親生,是得避嫌。 此後她懂事地遠着繼兄,卻見他臉色一日比一日難看。 待他成了尊貴的太子殿下,她更是敬而遠之,不敢高攀。 與郎君相看那日,他失了君子風度。 沈幼宜受夠了,直接挑明:我的事,與殿下無關。 繼兄霎時黑了臉,往後行事愈發逾矩。 他看向她的眼神,讓沈幼宜又驚又怕,心裏起了個荒謬的念頭,他不會……喜歡我吧? 宴席後裝睡,一個輕柔的吻落到了她額上,沈幼宜錦被下的手攥緊了幾分,她以爲自己掩蓋的很好。 耳畔卻忽地響起一聲悶笑:醒了? 沈幼宜: ……好想暈死過去!!! · 崔絡天性涼薄,性情寡淡,府上的妹妹都對他望而生畏。 唯獨繼妹因着幾次無足輕重的善意,喜歡親近他。 崔絡面上不顯,心裏頭卻拿她當親妹妹疼。 一晃經年,繼妹出落的婷婷玉立,瓊花玉貌,叫他不敢多看。 不知何時起,那份兄妹情漸漸變了味。 崔絡及時止損,有意避着繼妹。 如他所願,繼妹待他日漸冷淡。 崔絡壓下心中苦澀,如此便好,往後他還是她心中光風霽月的好兄長。 直到撞見繼妹相看婚事,少男少女言笑晏晏,過分般配。 強壓在心底的妒意瘋狂滋長,崔絡只有一個念頭。 他不再是她兄長 這輩子亦不會再放手。
21萬字8 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