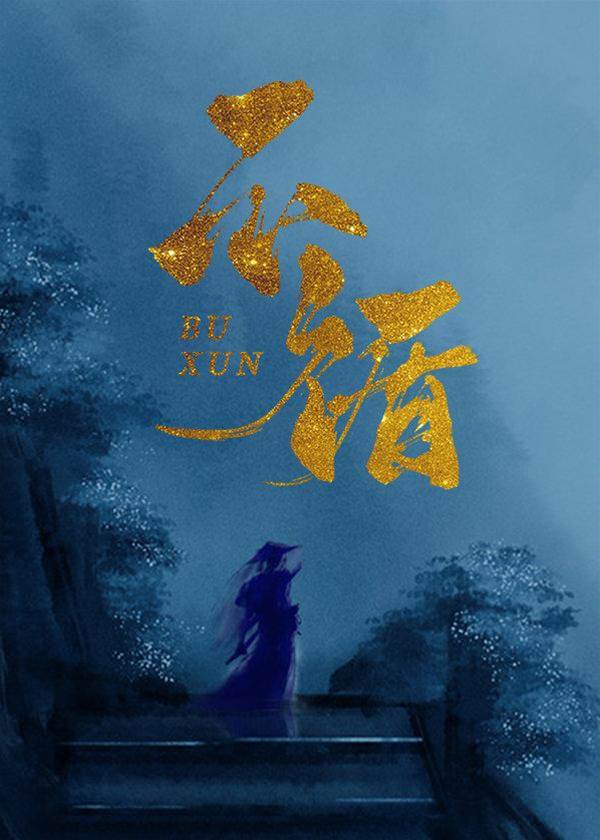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浮圖塔》 第78章 自足章娛情
文殊殿里的直欞窗悄悄落了下來,彤云回子道:“不知南苑王和長公主說了些什麼,我瞧他們得高興,南苑王還拽著長公主不撒手。”
團上的人合什念了聲佛號,“阿彌陀佛,這回可糟了,要勸也勸不住了。怎麼辦呢,全看各人造化吧!”
彤云搖頭嘆氣,“真湊到一塊兒,將來長公主多難啊,站在哪頭好?要我說宇文良時缺德得,好好的人他拖進棋局里,不擺布死不踏實麼?”
“他管那些個!尚了公主他就是皇親,這年頭,義值幾個大子兒?”音樓也覺得沒計奈何,數著佛珠道,“廠臣給長公主提過醒兒,人到了這種時候,什麼話都聽不見去了。你瞧那南苑王,長得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的,年輕姑娘架不住他的手段,幾句好話就哄得找不著北了。”
彤云唔了聲,再想說什麼,站在神案旁咽了兩口唾沫,臉一下變了。音樓心里發,跪得起不來,仰脖兒問:“怎麼著?又不舒服了?”
說沒什麼,“口堵上一陣,一晃眼就過去的。太醫瞧不出所以然來,我們家祖上也沒聽說有死在心病肝病上的,料著不是什麼大癥候。”瞧跪了半天了,在邊上勸著,“您忒實誠了,跪著上癮是怎麼的?起來吧,趙老娘娘不在,會兒懶不要的。說起來那天冷不丁聽人這麼稱呼,真我笑得小肚子筋。這名號是誰取的?聽說是肖掌印的手筆?這麼會損人,誰得罪他可算倒了八輩子霉了!”正前仰后合,錯眼兒朝門上一看,說曹曹就到了。笑了半拉憋住了,蹲聲督主,自己識趣兒,斂著子退出去了。
Advertisement
音樓仍舊跪在那里敲木魚,篤篤之聲不絕于耳。
他先頭忙,到這會兒才得閑。那些后妃們都安置到行宮殿里去了,們忙著找高僧搖卦解簽,他趁著去方丈室接布施賬目的當口遁了,知道在這里,心里熱得一捧火似的,著急忙慌趕過來,來了見還在裝樣,不覺有點好笑。踱過去,立在邊上探看,“娘娘的法事要做到什麼時候?”
拉著長音說:“我得對得起舊主,毗盧閣不停,我有什麼道理溜號啊!”
“你還真把榮安皇后的話當回事?”他背著手彎腰道,“意思意思就了,先帝看得見你的忠心。”
興嘆起來:“我在這兒跪著,先帝在上頭叉腰琢磨,心里八嘀咕呢——這姑娘是誰啊?瞧著有點兒面生,別不是認錯親了吧!其實先帝兒不認識我,我連圣駕都沒見過一回。”
“所以我說,面上帶過就行了。”他把一條胳膊到面前,“娘娘請起吧!跪了這半天,膝頭子都跪破了,臣看了要心疼的。”
紅著臉低低啐一聲,到底搭著站了起來,扭頭問他,“是你把宇文良時放進來的?他和婉婉在舍利塔那兒敘話呢,不知道說了什麼,我怕他哄人,婉婉著了他的道兒。”
他低頭拂了拂牙牌,“咱們不是佛祖,天下事多了,再憂心也不能代人家做決定。我知會過的,不是孩子了,有自己的主意,我總不能強。”
音樓鼓著腮幫子看他,這人很多時候缺乏同心,即便是在他跟前長大的孩子,他勸過、提點過就已經仁至義盡了。聽不聽是人家的事,他同樣的話絕不說第三遍,這麼看來真夠沒人味的。
“你就眼睜睜瞧著婉婉被他騙走?”
Advertisement
“要不怎麼?自都難保了,還管別人的閑事?我如今只想著你,忙著給你撐腰、替你出氣,心都碎了,哪有那勁道在其他事上耗神!”往外瞥一眼,左右無人,一下子把拖到帷幔后頭去了。欺上來,張開五指著的脊背,讓服服帖帖趴在他前。
低頭看,仰起臉來,頤養得滋潤,態較之前陣子更顯盈了。了的桃兒,一咬一口水。他著的下,狠狠在頰上親了口,“我把榮安皇后治了一通,聽說嚇病了,這才沒能來進香。我估著短期不敢來找你的茬,過陣子就不知道了,所以你萬事小心。倘或發覺有哪里不對的,趕打發人傳話給我,小事捂著就大事了,記著了?”
聽話地點頭,“記住了。不過人家好歹跟過你,你這麼對付人,手太黑了。”
他的眉直挑起來,“混說什麼,什麼跟過我?各取所需罷了!給我高厚祿,我替鏟除異己,就這麼回事。”言罷笑著晃一下,“怎麼,還吃味兒麼?”
在那兒冒充大鉚釘,“我量可是很大的,雖然知道你和那些后妃們不清不楚,我也從來不惱火。”給他整整盤領上的金鈕子,覷了他一眼,不不的嘀咕,“我瞧太后對你寵信有加,別不是有說頭吧!太監也這麼吃香,可見宮里人苦。”
還說不醋,分明醋大發了,連太后都牽連進來。他在鼻尖上親了下,“你傻麼?以前為奴為婢的時候要借助們登頂,如今到了這位置,靠的是自己的能耐。你只當單憑邀寵就能坐穩掌印的寶座?”他起先還嗤笑,轉瞬又睨起了眼,目空空落在佛堂西墻張的儀文上,“接下來得想法子徹底摧垮西廠,留著于尊是個禍害。至于咱們的事,暫且只有按捺。皇上既然有了耳聞,斷不會輕易放人的,咱們要在一,恐怕得費很多周折。”
Advertisement
這麼說來真有些傷,不過音樓想得不怎麼長遠,覺得只要他們之間沒有誤會,皇帝視而不見,一直在宮里生活下去也沒什麼不好。
兩手一焯,挎住了他的腰,“等我老了,你還會在我邊嗎?如果權力越來越大,大到你不用忌諱任何人的時候,你會不會嫌棄我,又去找年輕貌的姑娘?”
他在瓣曖昧地,“你現在雖年輕,貌也才沾邊,我還不是在將就麼!你放心,真到了那個時候,我頭一件要辦的就是把你討回去。咱們關起門生一窩孩子,好好振興肖家。”
有些惆悵:“我連想都不敢想,但愿真有那麼一天。今早聽長公主說,皇上要布施,要建攬仙樓,你勸諫了,鬧得很不痛快,是不是?”
他嘆了口氣道:“國運衰敗是不假,當家人要是勉力挽救,或許能多拖兩年。我也不愿意看著大鄴就這麼毀了,改朝換代,對我這樣的人來說沒有好。所以盡我所能拉扯一把,可惜收效甚微。”
他一副莫可奈何的樣子,音樓覺得很心驚,拽著他的襟道:“船到橋頭自然直的,你依著他,不要違逆他。橫豎這江山是他慕容家的,他作踐就由得他去吧!我怕你了他的逆鱗,回頭再生嫌隙,他又要借機削你的權。咱們現在這樣很安穩,維持下去也很好。你就算為了我,別管他的閑事,嗎?你不知道我聽見這個有多擔心,我是個沒用的,不像當初的榮安皇后,你遇上什麼難還能幫襯一把。我都指著你呢,萬一你有個好歹,那我真不能活了。”
他掩住的口,低聲說:“我都明白,也有分寸。順著他的意兒,我也想,可要國庫里調撥得轉才好。眼下批紅他是不管了,戶部的票擬他連看都不看,知道手要錢,哪里來的銀子供他驅使?這麼大個國,兵部、工部、吏部、各衙門各司,睜眼就有開支,這些錢哪里來?”說了半天才發現把說悶了,又不懂這個,跟著心也沒意思。兩個人難得見面,著說話更是之又,把時間花在議論國政大事上,白白浪費了。
佛堂里整天香火不斷,煙霧繚繞中看的臉,別有一種朦朧的態。其實他說錯了,不是和剛沾邊,在他眼里一點病都挑不出來,都是他喜歡的——他喜歡的臉架子、他喜歡的五、他喜歡的型、連那個自以為是的狗脾氣都是他喜歡的。喜歡到一定程度,恨不得把嵌進眼眶子里去。四下寂靜,只聽見毗盧閣約傳來鐃鈸的聲響,清脆的撞,一記記敲得不不慢,像一出冗長的悲歌。
他心澎湃,但終歸不好意思,扭道:“這會兒行宮殿里開了素宴,太后和主兒們都在用齋飯,咱們……找點事做?”
音樓哦了聲,無限落寞:“們吃飯都不上我。”
他聽了很不是滋味,“吃飯有那麼要麼?比和我在一起都要?”
他一副委屈的嗓子,心疼起來。這麼大的人了,有時候還像孩子。他的臉,踮起腳尖親他的紅,“自然是你要,婉婉給我摘佛果子去了,回頭在車里吃,也不著的。你剛才說找點事做,做什麼呢?一道出去走走麼?我怕人看見,傳到皇上跟前不好。”
“那就不出去了,外頭大太照著,什麼趣兒!”猶豫了一下,試探道,“做什麼好呢……你聽過《玉堂春》麼?有個橋段,蘇三和王金龍,那個……神案底下敘恩。”才說完,氣倒流,一張白凈的臉霎時漲得通紅。
音樓怔了下,心道這人真太壞了,這樣的地點,他卻在想那些東西!滿肚子花花腸子,偏偏長了張薄臉皮,在外面長袖善舞,往旖旎說,又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姿態,簡直人匪夷所思。忙對菩薩拜了拜,“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他垂下眼,濃的睫蓋住了里頭跳躍的火焰,”好不容易見的……我人外頭守著,不許任何人進來打攪。”說完含脈脈瞅著,探過來牽起的手,輕輕在那個地方,小聲嘀咕,“這模樣,怎麼出去見人呢?”
音樓大窘,想手他又不讓,只覺小督主熱力驚人,隔著料子都能描繪出劍拔弩張的形狀。嘆了口氣,“你以前是怎麼料理的?外頭走著,突然……這樣,那多危險吶!”
他怨懟地看一眼,“以前從來用不著為這個心,現在就像我那把三刃劍,嘗過了,一靠近獵就震嗡鳴。”
音樓忍不住扶額,好個比喻,十分的形象切。
“咱們就別蹉跎這大好時了吧!我提前知會了方丈,才把你安排在這文殊殿里的。這里安靜,來往的人也,倘或有個靜,外頭即時能傳報的。”他一面說,一面咬了咬,把手放在高聳的房上,“不著急,慢慢來。”
倒了半邊,想起上回的經歷,心里有點怕,“沒的玷污了佛門圣地,要遭天打雷劈的。”
他倒懂得開:“菩薩救苦救難,知道咱們這段苦,定然也可憐咱們。”
細打量臉,半闔著眼睛不說話,想來已經默認了吧!他竊竊歡喜,壯了膽子解的領,兩個人都張,大殿的落地罩上垂掛褚黃的帷幔,背靠在上面瑟瑟發抖,那幔子也跟著高低起伏。他低頭吻,手指盤桓在那一捻柳腰上,逐漸起的角轉移過來,找到原點輕攏慢捻,倚向他懷里,梅蕊初綻,不勝。
青山古廟,斜在翹角飛檐下一寸寸擴散,照著廟墻頂上朱紅的連楹和六角門簪,鮮紅如。
依舊是赫赫揚揚的富貴排場,因為要趕在下鑰前回宮,未正時牌就已經清道擺鑾儀了。彤云攙音樓登車,車里的帝姬顯得呆呆的,手肘支著窗欞看外面山水,眼梢約夾帶笑意。不說話也好,音樓自己滿腦子昏沉,索閉目養神,于是各藏心事,一路無話。
回到寢宮人也乏力了,本打算用過膳早早安置,沒想到才躺下,宮門上吊嗓子高喊“萬歲爺駕到”,把驚得縱起來,慌忙穿鞋抿頭到滴水下迎駕。
皇帝走得極快,沒等磕頭已經上了臺階。經過面前腳步并未停頓,聲氣兒也不好,冷冷扔了句“朕有話問你”,舉步便進了正殿里。
猜你喜歡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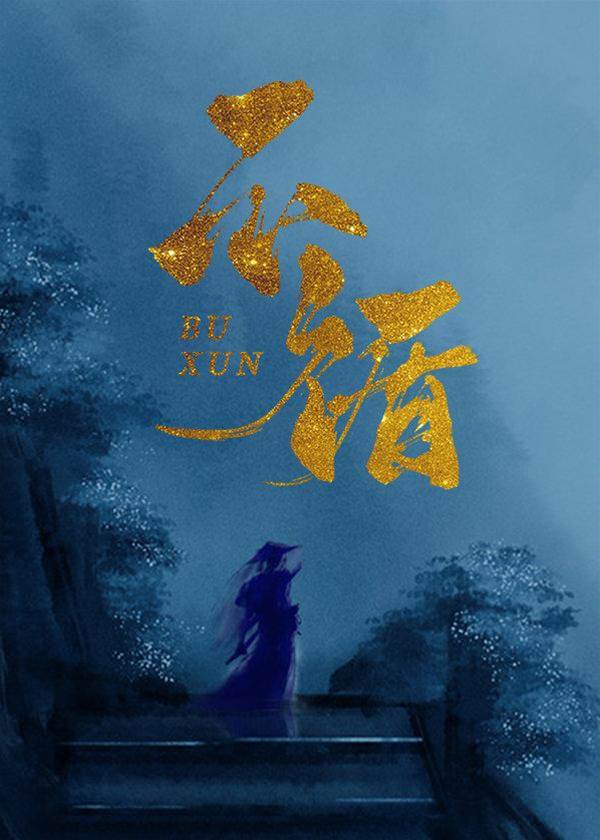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216 章

有嬌來
前世,定遠侯府滿門含冤入獄,身嬌體貴的宋五姑娘在被賣入勾欄紅院的前一晚,得那光風霽月的江世子相助,養於別院一年,只可惜宋五姑娘久病難醫,死在了求助江世子的路上。 【女主篇】 重生後的宋晏寧只想兩件事:一是怎麼保全侯府,二是怎麼拉攏江晝。 傳聞江世子不喜嬌氣的女子,被笑稱爲京都第一嬌的宋晏寧收斂脾氣,每天往跟前湊一點點,極力展現自己生活簡約質樸。 一日,宋晏寧對那清冷如霜雪的男子道:往日都是輕裝簡行,什麼茶葉點心都不曾備,可否跟大人討點茶葉? 後來,江晝意外看到:馬車裏擺着黃花梨造的軟塌,價值千金的白狐毛墊不要錢似兒的鋪在地上,寸錦寸金的雲錦做了幾個小毯被隨意的堆在後頭置物的箱子上...... 宋晏寧:...... 剛立完人設卻馬上被拆穿可如何是好? 清荷宴,宋晏寧醉酒拉住江晝,淚眼朦朧,帶着哽咽的顫意道:我信大人是爲國爲百姓正人的君子......,只想抓住幫助侯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晝聞言眼底幽深,又些逾矩的用錦帕給人拭淚,看着姑娘因低頭而漏出的纖白脖頸,心裏卻比誰都清楚,他對她可稱不上君子。 世人都道江晝清風霽月,清冷剋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縱容和徐徐圖之......
34.9萬字8.18 10522 -
完結144 章

與君同
朔康五年,齊皇室式微,諸侯四起。 爲籠絡權傾朝野的大司空藺稷,天子接回遠在封地的胞姐隋棠長公主,賜婚下降。 大婚當日,隋棠獨守空房。 直到七日後,月上中天時分才迎來新郎。卻被他一把捏起下顎,將藏於牙中的毒藥摳了出來。 彼時隋棠因在婚儀路上被撞,雙目暫且失明,正惶惶不安時,昏暗中卻聞男人道,“今日天色已晚,先歇下吧。” 這夜隋棠做了個夢。 夢中她看見自己,難產誕下一子,後不到兩炷香的時辰,便毒發身死。 死前一刻,她抓着藺稷的手,平靜道,“不必喚醫官,不必累旁人,無人害孤。是皇弟,曾讓太醫令鑿空了孤半顆牙齒,在你我二人大婚之日將一枚毒藥埋入其間,用來毒死你。” “非孤仁心下不了手,實乃天要留你。送親儀仗在銅駝大街爲賊人驚馬,孤被撞於轎輦瘀血堵腦,致雙目失明,至今難尋機會。所以,司空府數年,原都無人害孤,是孤自備之毒,漸入五臟。” “大齊氣數盡,孤認輸,君自取之。” 她緩了緩,似還有話要說,譬如她幫扶的皇弟,她家搖搖欲墜的江山,她才生下的孩子……然到底再未吐出一個字。 所有念想化作一聲嘆息,來生不要再見了。 隋棠在大汗淋漓中醒來,捂着餘痛未止的牙口,百感交集。不知該爲毒藥被除去而慶幸,還是該爲毒藥被發現而害怕…… 卻覺身後一隻寬厚手掌撫上自己背脊。 男人嗓音暗啞,“別怕,臣明日便傳醫官來府中,給殿下治眼睛!” * 藺稷攏緊榻上人,他記得前世。 前世,隋棠死後,他收拾她遺物。 被常年監控的長公主寢屋中,幾乎沒有完全屬於她自己的東西。他整理了很久,纔在一方妝奩最底處,尋到一份她的手書。 久病的盲眼婦人,筆跡歪扭凌亂。 此生三恨: 一恨生如浮萍,半世飄零久; 二恨手足聚首,卻做了他手中棋; 三恨雙目失明,從未見過我郎君。 世人道,藺氏三郎,霸道專權,欺主竊國。 但他是第一個待我好的人,我想看一看他。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
37萬字8 1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