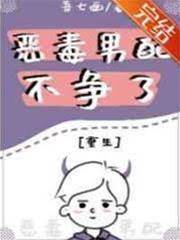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沉舟》 第57章 渣渣們的世界①
對顧新軍和衛誠伯這種政府高而言,政治上的發展路線一經確定,隨之而來的行必然有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前后不到五天時間,等顧沉舟再次出現在京城圈子里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通過“小道容”,知道了顧衛兩家加汪系這一消息了。
這時聚集在顧沉舟旁的人又在不聲地發生變化,首先就是汪博源的兒子汪榮澤,幾次下來都坐在顧沉舟旁,有之前顧沉舟和衛祥錦的覺——當然事實上差遠了;其次一些靠著汪博源的家里的二代三代也聚集過來,與此相對的是一些偏向郁水峰的就自然而然地走遠了。至于那些和之前的顧新軍一樣決定中立的,則態度曖昧,試圖兩邊都不得罪。
但總來說,這些變化都屬正常,唯一不太正常的,大概只有在顧沉舟出來的第一天,就跑到他面前刷存在的賀海樓了。
金莎會所里,和汪榮澤一道的顧沉舟正和以賀海樓為首的一群人打了個照面。
賀海樓看上去心很好,笑瞇瞇地同顧沉舟打了個招呼:“顧。”卻直接無視了一旁的汪榮澤。
汪榮澤心頭暗怒,皮笑不笑地說:“我之前還沒發現,賀也在這里啊!”一個‘也’字意味深長。
賀海樓朝汪榮澤了一下眼皮,漫不經心地說:“彼此彼此,其實我也沒有看見汪呢。”
新仇舊恨啊,汪榮澤差點當場火起來,還是站在他旁邊的顧沉舟出聲打斷。
相較賀海樓,他做得更直白點:連眼皮都不對方一下,徑自對汪榮澤說:“汪,我們進去吧。”
這下旁的兩人都不樂意了,汪榮澤正要說什麼,卻聽賀海樓搶先開口:“既然都到了,不如我們就合起來一伙玩吧?”
Advertisement
這可正中汪榮澤的下懷,他沖賀海樓假笑一下,然后對顧沉舟詢問道:“既然這樣,那我們就一起玩吧?”
顧沉舟神淡淡,但還是笑了笑:“這次是陪汪來的,一切由汪決定。”
汪榮澤十分滿意,暗道這顧沉舟可不是一般的上道——其實顧家和賀家的那點事,他多多也有些了解,誰讓他有一個伯父姓汪名博源呢?
“賀原先是定在哪里?”心好了,汪榮澤臉上的笑容就顯得矜持有風度了一些,他問賀海樓的同時又說,“我們是定在三樓第二間,位置不特別大——要不然,就去賀那里?”
賀海樓笑道:“恰巧了,我是三樓第一間。不過——”他拖了拖聲音,“還是去汪那里吧。”
“那好,就去我那里。”汪榮澤一揮手,拍了板。
堵在大廳里的兩方人終于達協議,站在旁邊懸了好半天心,不住汗的經理長出一口氣,忙不迭地將人迎上三樓。
三樓上,不論是賀海樓還是汪榮澤預定的那間包廂都早早做好準備,就等客人上來。現在雖說兩方人馬合并一方,但事也不復雜,只要把一號包廂里的人和東西全都挪到二號包廂就夠了——反正任何一間包廂都足夠大,再來二三十個人也夠放的。
眾人在二號包廂里的沙發上坐下,自然而然分了左右兩邊。二號包廂,穿高開叉旗袍的服務員和一號包廂過來的斜襟長的服務員分別將酒品和小吃擺上桌,顧沉舟抬眼看了看周圍的服務員,心道有賀海樓和汪榮澤兩個在,這周圍的人還真是環燕瘦,應有盡有了。
金莎里的服務員服務非常到位,一個個都跪在厚地毯上,平舉雙手,將手中盛放各種食的餐盤流水一樣環繞傳遞著。
Advertisement
汪榮澤拿了一枚綠葡萄,低笑著湊到顧沉舟耳邊問:“不知道顧喜歡哪種的?——顧喜歡的話就點一個,算是我的,怎麼樣?”以為顧沉舟平常不近是因為家里管得嚴。
“哪有這麼麻煩?”顧沉舟笑了笑,在他眼里,這里的人從男到也沒什麼區別,隨便抬手指了一個看上去端正大方的,說道,“就吧。”
被指到的人抬頭沖顧沉舟抿一笑,接著站起,走到顧沉舟旁坐下。
一旁的賀海樓立刻就看對方不順眼了,他垂一下眸,臉上反而浮現出幾分似笑非笑來,跟著抬手一指,就指向了材最好、容貌最艷麗、就跪在汪榮澤旁的那個人:“過來,”復又對汪榮澤說,“這個看上去倒像是汪喜歡的類型,不過我剛好想換換口味,汪不會不舍的割吧?”
馬匹的,你既然知道是我喜歡的,還敢點還特意問我?這小子是跟我杠上了啊!汪榮澤心里火燒得實在旺,但要現在就為一個出來賣的人拍桌子和賀海樓翻臉,在他伯父那邊又說不過去……
“賀可真是了解我,”一旁的顧沉舟忽然話,沖賀海樓淡淡一笑,“我也剛好看上了這位——汪,你不會舍不得割吧?”
兩句一模一樣的話,賀海樓說來是地上的臭狗屎,顧沉舟說著就變了天上的天籟。汪榮澤神舒展開來,手一揮笑道:“顧真是太客氣了,我們是什麼?你想要有什麼不能拿去的?”低下頭對腳邊的人說,“好好服侍顧,有你的好。”最后又沖賀海樓一攤手,假笑道,“賀,你看這個,真是不好意思了。”
賀海樓看了眼汪榮澤,又看了眼一左一右坐在顧沉舟旁的兩個人,神自若地笑了笑:“既然是小舟想要,我當然沒有異議了——別說是一個人,就算是一個月亮,我也讓出來的。”
Advertisement
一句話讓包廂半數的人嗆了酒,顧沉舟臉上完的表又裂了裂:“賀是在誰?”
等的就是你這一句呢!賀海樓很歡快地再了顧沉舟一聲:“小舟~”尾聲居然還飛揚起來,帶了波浪音。
這個走向……怎麼有點看不懂啊。同樣屬于嗆酒的那半數人,汪榮澤拿著紙巾了上的酒,看著顧沉舟和賀海樓兩個人,心里暗自忖度道。
顧沉舟心道想跟他好好玩一局的自己可真是個傻子,他笑了笑:“不敢當!賀還是回我的名字吧。這個小名我聽家人習慣了。”言下之意是你賀海樓算哪蔥,也敢這樣我。
賀海樓笑道:“小舟這就見外了啊,我怎麼聽衛一直這樣你?”
顧沉舟看了看賀海樓,然后掃了包廂中的眾人一眼:“賀是后頭來的,所以大概不知道,我和祥錦一向是一家人。”
賀海樓樂意當著眾人的面多幾個‘小舟’,他一邊琢磨著搞死衛祥錦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一邊說:“既然顧和衛能為一家人,那顧和賀也是——”
顧沉舟立刻出聲打斷賀海樓的話:“汪,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了。”
一旁看熱鬧看得都神了的汪榮澤連咳兩聲,說:“顧去吧。”
這下顧沉舟真是一眼都不看賀海樓,直接推開包廂的門離開了。一離開包廂,顧沉舟一邊往洗手間走去,一邊撥了個電話,只沖那里說了“按計劃手”幾個字,就直接掛掉。接著他也沒有再打算回去,給汪榮澤發了條短信之后就直接下樓拿車離開。
一個多小時后,同樣無聊的賀海樓和汪榮澤和平友好地分手了。他們各自分開,分別去停車場開車,但在停車場里,賀海樓看著自己的白保時捷,愣住了。
“這是怎麼回事?”
旁邊的經理早在賀海樓下來的十分鐘前就到了,那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是一輛被人敲碎玻璃和車燈,敲凹車又劃花車漆的車子;而十分鐘后的現在,擺在他面前的就了一輛被砸的車子,一位不好招惹的車主,還有一群唯恐天下不的公子哥。
值班經理真的想要淚如雨下了,不住地冒著汗,賠著笑說:“賀,這是我們管理的問題,管理的問題,我們一定全額賠償,您千萬包涵著些……”
但出乎眾人的意料,賀海樓似乎沒有太多的憤怒。他看了看自己的車子,又問:“有拍攝到對方砸車的畫面嗎?”
“這個有,這個有!”經理迭聲說,“賀您要看看嗎?那些人都套了頭——”
“不用,”賀海樓擺擺手,“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一個半小時前?十分鐘之前?”
“十五分鐘之前,我們看監視的人馬上趕下來,但是車子已經被砸了……”
“掐好了時間啊。”賀海樓嘀咕一聲,接著角就浮現出一點笑意來。
旁邊的經理和同行的公子哥看得一愣:難道這是怒極反笑?
但事實上,賀海樓確實不太生氣,他就是沒有想到,顧沉舟居然會做這樣的……怎麼說呢,單純發泄的舉?
“算了,”賀海樓擺擺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大家混鬧著玩呢,你們把這輛車拉走吧。”
經理:“那賠償……”
“我和自己兄弟鬧著玩的,跟你們金莎有什麼關系?”賀海樓頭也不抬地說,打開車子從駕駛座里取出了一個跟顧沉舟有八分相似地串竹簽上的泥人,又把房子的鑰匙拿出來,就直接說,“行了,車子連同里面的東西,你們都理掉吧。”
原本以為很難辦的事出乎意料地快速解決了,經理連聲謝,亦步亦趨地跟在幾位公子哥后面,甚至還聽見旁邊有人對賀海樓笑道:“賀,這次的事是顧——”但話說到一半沒沒有了下文,經理好奇地抬頭看過去,正好從側面看見賀海樓滲人的眼神。
賀海樓看了看說話的人,輕輕拍了拍對方的肩膀說:“被砸的是我的車,我都沒有說話,你急什麼呢?”
說話的人訕訕笑了,當自己是個蚌殼把給閉了起來。
有了一個舍己為人的先鋒死在沙灘上,其他人怎麼會不知道自己該干什麼?自然一個個裝作不知道這回事,分開走了。
賀海樓跟眾人分手,直接打了一輛車回家,走到一半想了想,又吩咐司機拐去另一個地方——是那套用于SM的房子。
幾天不見,這套房子里的擺設又有不同了。那些刺眼的和各自然還在,但除了這些之外,還多了在墻上、麻麻、許許多多的另一個人的不同的照片。
賀海樓從吧臺上拿起剪刀和線,將一直拿在手里的那支泥人系好了綁到窗戶前,在這里,已經綁了有好幾個著不同神迥異,但面孔都一模一樣的泥人了。
他噙著微笑推開窗戶,風敞開的窗戶灌,將懸在窗前的泥人吹得四下搖晃。那些纏繞在泥人上的線,要麼圈在泥人的脖子上,要麼鎖住泥人的四肢,還有一些更匝匝地環繞在泥人軀干上,將其牢牢綁住。
他出手指,從泥人的面孔往下,過泥人小小的脖子,再過軀,再過四肢——然后狠狠穿泥人的!
“不會太久的……”賀海樓自言自語地說,出手指,任由面上帶著笑容,腹卻穿了一個大的泥人在空中打晃,自己則拿出手機打了一個電話:“你們準備準備,我有事你們去做。就在幾個小時之后,知道天香山莊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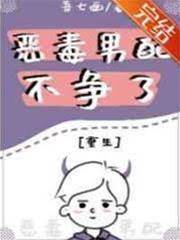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