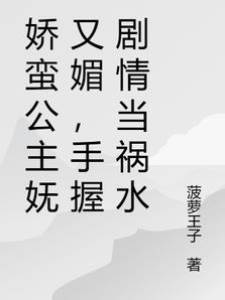《獨步天下》 夢境
哈日珠拉 1 夢境
白的天花板,白的牆,牆表面的牆有些斑駁落……空氣裡瀰漫著醫院獨有的消毒水味。
我眨了下眼,確認頭頂上吊著的,果然是一臺貨真價實、蒙塵生鏽的大鐵吊扇。
“醒了呢,這下子可以趕得上飛機了。”
我詫異懵懂地扭頭,一旁穿白羽絨服的男人正笑嘻嘻地盯著我——那是……有宏!
“我……”我略略擡頭,卻覺子很沉,腦袋暈暈的,一點力也使不出來。
怎麼回事?
我回來了?又回到現代了嗎?這麼說,我沒有死?
門口快步進來一名穿白大褂的男醫師,後跟了一名護士小姐。
護士徑直過來給我量溫,醫師則是直接手按在我額頭上,大拇指一擡,將我眼皮很魯地給掀了起來。我疼得齜牙,接著聽到他衝護士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長串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好容易等這一男一出去了,我奇怪地問有宏:“到底怎麼回事啊?這是在哪?他們剛纔說什麼?”
“在醫院啊!”他將牀邊的凳子拖近些,“不?”
我搖頭,急問:“你小子講話能不能一口氣講完啊,白癡都知道這是醫院了!我是問你……”
“才醒過來就有力氣罵人了!嘖嘖……真不愧是阿步啊!”
我氣惱地擡起右手,卻發現手背上正打著點滴,不愣了下。有宏趁我發怔的間隙,早跑到門口去了,臉上仍是笑嘻嘻的:“我去找Sam!不是我不給你翻譯啊……只是剛纔那蒙古大夫說的是啥鳥語,我也聽不懂……哈哈!”
蒙古大夫?
迷茫地扭過頭,我開始仔細打量四周——很簡單的一間病房,擺了三張牀位,除了我這張牀位外,另外兩張都空置著。牆上了一些標語,寫的卻不是中文——是了,我應該還在外蒙古,並不在國。
Advertisement
腳步聲徐緩響起,我回過頭,Sam沉著臉站在病房門口。
心沒來由地一,Sam臉上那種冷冰冰的神似曾相識。
“沒事了?”他淡淡地問我。
有宏從他後進門,笑說:“醒來就能兇人了,當然不可能會有事啦!”
我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慢騰騰地從牀上坐了起來,背靠在枕頭上,覺四肢有些僵痠麻:“我睡了多久?”
“三十五個小時!”Sam一不茍地回答。
果然……我擰了眉頭,心在作痛。
三十五年的夢,恍若隔世。流飛舞,恨糾纏,而真正從指中不經意流逝的卻僅僅是三十五個小時而已。
好荒謬!好……可悲!
“阿步,怎麼了?還會不舒服嗎?”有宏見我表痛苦,忙收了玩笑之心,“我去醫生吧,可別是煤氣殘毒沒有清除乾淨。”說完,他急匆匆地轉走了。
“煤氣?”我瞪眼。
“嗯,煤氣中毒!”Sam脧了我一眼,冷淡的眼眸中漸漸有了幾許暖意,但語氣卻是不容置疑的嚴厲,“我們住的那間旅店設施不是很好,通到你房裡的那段煤氣管道老化了。昨天晚上你一個人待在房裡打電腦,結果就這麼在房裡昏過去了。要不是當時你正和你朋友正在MSN上聊天,及時打我手機,我想……”
“等……等等!”我糊塗了,有種對時間概念的強烈混淆,“昨晚上旅店煤氣中毒?那怎麼可能?我和白晝月聊完天,保存好照片是凌晨一點多,我記得我後來睡了會兒,兩點多的時候明明還被你們起來了,去喀爾喀草原看墓……”
“那是你在做夢吧?!”Sam很肯定地斷言,有些憐憫地瞟了我一眼,“你早昏過去了,兩點多你正在急救室裡搶救呢!”
Advertisement
“啊?那……古墓呢?布喜婭瑪拉的墳墓,明明……”
“什麼古墓?布喜婭瑪拉是什麼東西?”
一切都已空!不過是場太虛夢境……
我很想告訴自己現實就是如此,必須得認清事實,看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幻。可是,夢裡的一切都顯得太過真實,清晰得可怕。不管這是否真的只是個夢,我的心曾經真真切切地爲這個夢而痛過,爲夢裡的人魂牽夢縈過……
有宏取笑我說:“阿步醒來後變乖了,以前老張牙舞爪的,病了以後居然有幾分人味了!”聽了這話,我真想拔了針頭,直接跳起來掐死他。敢他以前一直都沒把我當過人!
Sam則固執地認爲我的神狀態不佳,是因爲還沒痊癒,於是自作主張地退掉當天下午的回程機票,強迫我留院觀察,順便接全檢。
其實這家小醫院的醫療條件有限,病房裡甚至都沒通暖氣,更別提空調、電視什麼的了。我越住越不耐煩,每每一躺下滿腦子就會更加胡思想,夢境裡的一幕幕景會自發地在腦海裡浮現重演。
我就快被這種似假還真的幻象弄得神崩潰了。
第四天,再也忍不了的我強烈要求出院。Sam拗不過我,在醫生確診我已無礙的況下,替我辦了出院手續。
簡單地收了幾件,回到原來住的那間小旅館,其他同事早退了房,三天前搭乘飛機回了上海,留下來的只剩下Sam、有宏和我三個人。
其實想想他們也是關心我,不然早走了——喀爾喀草原環境則矣,只是條件太差,對於在大城市住慣的人來說,這裡簡直可以比擬四百年前的……
Advertisement
啊,不能再想了!真的不能再胡想下去了!沒有四百年前,什麼都沒有!
“阿步,好了沒?”
“好了!”我背上簡單的行李揹包,將最最寶貝的相機一腦地全掛在脖子上,最後手裡提了筆記本電腦。
有宏撲哧一笑:“逃難的又來了呀!”
我擡踹他:“去!給姑閃一邊去!”
“真的確定不用我幫忙扛行李?”
“就你那心大意的腦子?謝了!上回去趟韓國,就讓你幫忙提了一下電腦,十分鐘的工夫,你就有本事把它給我摔了!”我拿眼惡狠狠地瞪他。
“那多久以前的事啦,你還記著?”
說話間出了房門,Sam簡單地背了個單肩包,筆直拔地站在走廊的過道里,手裡揚著三張彩印的飛機票:“晚上十點的飛機,還有三小時飛機起飛。從這裡趕到機場最快也要兩個半小時,你倆確定還要繼續留在這裡拌嗎?”
有宏聳肩,我撇了撇,低下頭,從Sam側經過,默不作聲地往外走。
Sam說話做事老是怪氣的,雖然有時候也明知道他本意不壞,可就是不說笑,老喜歡繃著張酷酷的帥哥臉,迷死膽大的,嚇死膽小的。
“等等!”Sam突然在後喊住我,我低著頭踢著鞋子轉過,“這是送你到急診室時,醫生從你手上摘下來的……還給你!”
沒等我擡頭,眼前嗖地飛過來一件綠油油的東西,吧嗒撞在我口,我一時急慌了手腳,狼狽地低呼一聲後,趕忙用空著的左手抓牢了。
手冰涼,凍得像塊寒冰。
我先是一愣,待看清那東西時,只覺得眼前一陣眩暈,的似乎在下一秒奔騰逆流。我使勁眨了下眼,手裡的東西並沒有消失,那冰冷的真實地停留在指尖。
“什麼東西啊?”有宏好奇地道,“有點眼!”說著,手過來拿,我下意識地退後一步,五指收攏。
“慈禧太后的陪葬品,十八翡翠碧璽珠串!”Sam淡淡地說,“仿真度很高啊!不像是地攤上賣的次貨!”
有宏驚喜地道:“我瞧瞧!給我瞧瞧!”
我心咚咚狂跳,一時震駭得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見有宏手過來搶,忙閃過,將手串塞進服口袋裡:“有什麼好看的,贗品而已,不值錢的東西!”見他還不死心地不停糾纏,不很不耐煩地叱道,“跟你說了沒什麼好看的!你一個大男人看這種人飾品幹什麼?煩不煩啊?”
有宏尷尬地頓住形。
接收到Sam投過來的若有所思的目,我心裡一慌,覺察到自己剛纔的態度和語氣都顯得過於激烈,忙訕訕地一笑:“好了,快走吧!不然真的要誤點了。”
機艙溫度適宜,頭等艙座位寬綽,只坐了十來名乘客,此刻都在閉目休息。
窗外一片漆黑,窗面如鏡,清晰地映出我略顯憔悴的面容。我無聲地嘆了口氣,將視線緩緩收回。炭筆無意識地在手指間飛快轉,著紙上素描的那張悉臉孔,我的心一點點地爲之悸痛。
“在畫什麼?”側有宏放下報紙,低聲音湊了過頭來。
我張地將畫紙走:“沒什麼,隨便塗……”
沒想到有宏的作比我還快,唰啦一下,我手裡一空,畫紙被他搶走。
“這……你在畫Sam?”他興趣地低呼,“畫得傳神啊!早就聽說你人素描功底不錯,什麼時候也給我畫一張呀?”他低聲說著,將畫紙還給我,指著那張臉的額頭,“爲什麼不加上頭髮?這樣腦門禿禿的Sam看起來好好笑……”他忍住笑,往左側過道瞥了一眼。
Sam正戴著眼罩,耳朵裡塞著耳機,窩在的椅墊假寐,也不知到底有沒有睡著。
“嘁!”我不悅地將紙團,“我畫的,也只有你這個大近視纔會把這看是Sam。”
“不是畫他?”
“不是。”我頓了頓,紙團,“我的素描水平還沒那麼高。”
“哦……”有宏顯得有些失,重新撿了報紙,蓋在臉上,含含糊糊地說,“我先瞇會了。阿步,你也打個盹吧,你臉不是很好……”
“嗯。”我隨聲應著,目不經意地穿過有宏,投向Sam。
紙團被重新打開,紙上被凌褶皺扭曲了的英俊廓,有著令我心驚悸的悉棱角鋒芒,我狐疑地再次看了眼Sam——像嗎?很像嗎?
不……我覺不出!
即使那冷峻的氣勢有些相似,但是Sam就是Sam,他永遠不可能爲我夢裡的那個他!
眼角不知不覺地溼潤起來,我吸了口氣,手進旁的羽絨大的口袋裡,指尖到僵的圓潤冰冷。我不一,將那串翡翠珠子取出,和的燈下,圓潤無暇的珠玉淡淡地散發出溫潤的澤。
沒錯!是那串手串!
我心魂劇,這的的確確是皇太極送給我的那串翡翠手串!難自抑的,我抖著雙手,將珠串湊到脣邊,輕輕印上一吻,眼淚嗦的一聲墜下,濺在了畫紙上。
淚水將紙潤溼,畫像的臉孔漸漸變得模糊起來,我急忙了餐巾紙去吸,慌間手串不小心掉落在地毯上。我低呼一聲,彎下腰去撿。
手指抓到珠串的一瞬間,忽然覺子一震,隨著往前衝的慣力,我從座位上摔了出去。
機艙的燈管啪啪響,一盞盞照明燈逐一炸裂,電線短路得火花四濺,然而座位上的乘客沒有一個被驚醒,包括有宏、Sam在,全都渾然未覺似的照常閉著眼睛坐在椅子上。
我心生懼意,沒等張尖,下一秒機整個顛倒翻轉過來,我被拋離地面,驚駭間一個悉的聲音在空中響起:
“布喜婭瑪拉……布喜婭瑪拉……布喜婭瑪拉……”一聲又一聲,像纏綿的息,像痛徹的低,更像是一聲聲絕而又悲涼的呼喚,“布喜婭瑪拉……布喜婭瑪拉……”
我呼吸一窒,心臟像被人猛地狠狠住。
“爲什麼……不回來……爲什麼……要離開……回來……回來……悠然……求你……回來……”
手中的珠串突然發出一團強烈的綠芒,刺眼奪目地從我的指間穿出,陡然間照亮整個機艙。
那團芒由綠變白,最後籠住我的全,眼前頓時顯出白茫茫的一片……機艙、座位、乘客,統統都不見了,只有那團熾熱的白越來越亮,越來越亮……
猜你喜歡
-
完結1274 章

農女傾城
沈曉曉穿越了,穿去了一個叫閔澤國的旮旯朝代,悲催的是由集三千寵愛于一身的世家大族豪門千金穿成了奶不疼,爺不愛的賠錢貨。但是上天從來都是待她不薄的,作為補償贈送給她一個隨身空間。且看她在這落后的古代怎樣發家致富,幫助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讓整個閔澤皇朝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福星王妃傾國傾城。
237.3萬字8.18 617785 -
完結1010 章

嬌寵攝政王
少年謝珩(héng)殺人如麻,心狠手辣!滿朝文武膽顫心驚,日日跪求神明收了這小閻王。直到某天半夜,有人看見謝小閻王被關在門外,低頭哄著門裡那人:“阿酒乖,把門開開,老子回家給你跪算盤!”片刻後,門開了。那姑娘把他摁在牆上親:“你乖一點,我給你買條街!”小閻王低眉含笑任撩撥,一點脾氣也冇有。朝野上下震驚不已:哪路神仙下凡?您辛苦了!
187.8萬字8 20435 -
完結492 章

特工皇妃:皇上我要廢了你
“跟我走,我娶你為妻。”女子緩慢里拉開頭發,露出魔鬼似的半臉,淡淡的道:“這樣,你還要我跟你走嗎?”她是帝國家喻戶曉的丑女,廢物。卻一言驚天下,王子,不嫁。王妃,我不稀罕。金麟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變化龍。誰知道如此的廢物身后卻是那驚才絕艷的…
89.3萬字8 48271 -
完結106 章

見卿卿
心死前妻從不回頭看爆炸VS男人撒謊要吞一千根針薑家是世間第一門閥,權傾天下,薑宛卿是家主庶女,生得風流嫋娜,美貌驚人。上一世被人暗害,與太子風昭然有了肌膚之親,風昭然不得不擱置下與薑家嫡長女的婚事,娶了薑宛卿。但風昭然心儀的一直是她的長姐,薑宛卿隻不過...
37.6萬字8.18 10119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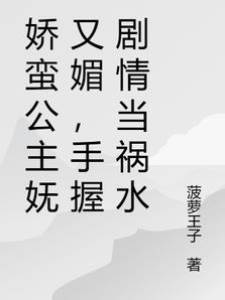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