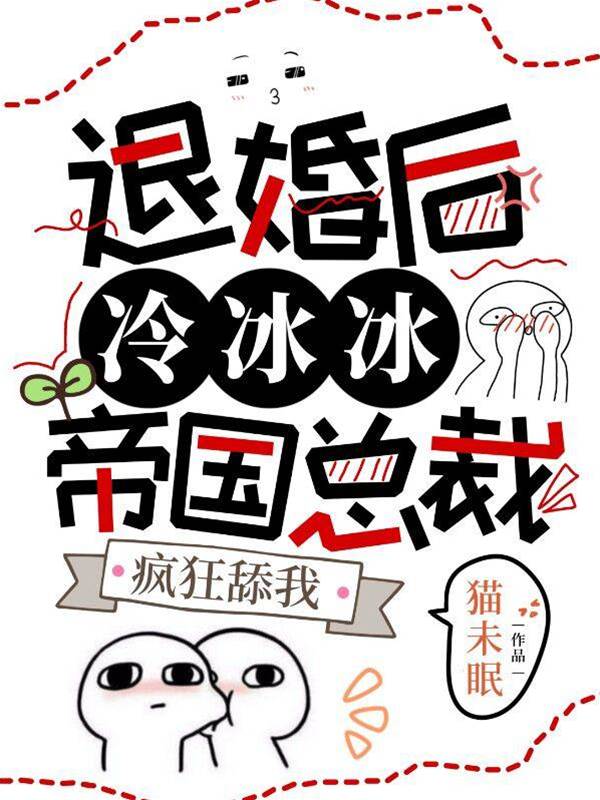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17章
因為集自殺事件,學校拒絕再讓學生休息日留校,周五剛打了下課鈴,學生們便收拾好東西,熙熙攘攘的出了學校。
大門外停滿了各豪車,其中一輛紅跑車格外顯眼,和他們走在一起的周植努努,道:“我姐過來接我了,我先走了,周日見。”
“周日見。”
目送周植離開后,時暮看向了傅云深。
他雙手兜,皎皎如玉,就算學生們懼怕他染的雙手,也不沉醉在那幽深的雙眸,著四周生們視線,傅云深眉眼依舊淡薄。
“走吧。”
時暮愣了下。
走在前面的傅云深說:“你不是沒地方去?”他輕笑下,“你以為也會有跑車來接我們?”
時暮了下耳垂,訕訕跟上。
英南附中建的偏,要走幾公里才能到唯一的車站,兩人并肩而行,后暖將影子拉至修長。
這條路筆直又孤寂,傅云深依然習慣,如今邊多了個,倒略顯不自在。
“傅云深,你現在一個人住?”
“嗯。”
眸閃爍,沒有再多問。
腳步聲颯颯,過了會兒,耳邊傳來他聲音:“你呢。”
時暮很快回答:“我家人都不在了,只留了點錢給我,也花不了多,這幾天我可能就要找到工作,不然支付不起上學的費用。”
這一點就有些羨慕傅云深了。
傅云深的父親原來是開店鋪的,后來店鋪拆遷,得到大筆拆遷款,加上生母那邊留下的,價說上億。
不像是,除了個沒用的系統,屁都沒有。
[系統檢測到宿主有辱罵行為,扣除兄弟值X100,大腦里也不是不法之地,請宿主謹言慎行。]
???
這沒天理了鴨!!
天完全黑下后,傅云深和時暮總算來到了就近車站,站牌,四下無人,走累的時暮毫不猶豫坐在了凳子上,安靜等車。
Advertisement
寂靜的暮里,看到燈閃爍,車輛已經接近。
時暮剛抬手準備攔車,傅云深卻猛然握住了手。
[叮!與傅云深牽手功,獲得得兄弟值X100]
這就握上了?
驚喜來的太突然,時暮有些承不住。
視線一轉,看到傅云深沖輕輕搖頭。
時暮心里一個咯噔,不抬頭看了過去。
向他們開過來的車通紅,車,方向盤自己轉。
這不是生人該上的車。
急忙屏住呼吸,慢慢把腦袋低了下去。
等車影消失在視野后,時暮才松了口氣。
“來了。”
公車在站牌前停下,傅云深登上車門,往里面投擲了兩枚幣。車很人,他們坐到了最后一排。
時暮看著窗外夜,漸漸有些昏昏睡,眼皮子,最后沒忍住,慢慢把腦袋往車窗靠去,前方一個顛簸,的腦袋正要磕上窗戶時,一雙手從后繞過,輕輕拖住。
傅云深小心翼翼朝那個方向看著。
燈很淺,白皙的臉頰暈染上溫的暖橘。時暮睫纖長,雙眉濃有形,鼻梁秀,瓣是淡淡的紅。
傅云深眨眼,這才注意到間平坦,若這樣一不,旁人本分不出男。
“滴——!”
鳴笛聲響起,睫了兩下。
傅云深有所驚覺,緩慢把自己的手了回來,默默往一旁側了側,和時暮拉開了距離。
一個多小時后,車子在終點站停下。
時暮醒了過來。
年起,聲音冷淡:“到了。”
“哦。”惺忪的睡眼,拿上書包下了車。
兩邊路燈映照著街道如同白晝,現在已經九點,睡懵的時暮踉踉蹌蹌跟在傅云深后,走著走著,就覺得這路有些悉,再走著走著,覺得更加悉,等花都嘉園四個字落眼底時,時暮像是墜冰窖般,立馬清醒。
Advertisement
“你、你住這兒?”時暮察覺到自己的聲音有些哆嗦。
傅云深看過來:“有問題?”
“沒……沒問題。”
就是有些…震驚。
時暮追上去:“你住哪一單元啊?”
傅云深說;“三單元五號。”
“……”媽的,要是沒記錯的話,那便宜父母住在三號,就和傅云深隔了一棟。
眉頭死死皺著,臉上寫滿糾結。
此時已經路過了時宅,小洋樓的燈亮著,時暮不由停下腳步,朝里面看了眼。
所住的閣樓一片漆黑,里面的所有歡聲笑語和溫暖都已和無關,此此景,此宅子,突然讓生出了萬般的難過。
原本啊,有個很圓滿的家庭,父慈母,對教導有方,可是后來一場惡意的縱火,讓那個圓滿的家只剩一個人。
“怎麼不走了?”
傅云深的聲音讓時暮回了神,疾步跟上,再也沒有回頭看一眼。
“哥,你在看什麼呢?”
他們離開后不久,時蓉趴在了臺前,看到時黎正向下面著。
“沒看什麼。”時黎收斂視線,指尖輕了下心臟。
這個作立馬讓時蓉眉頭皺起,一臉關切:“哥,你又不舒服了?”
“沒有。”他目落向窗外夜,睫,轉走向里屋。
傅云深一周才回來一次,家里衛生都是小時工過來打掃。
屋子很大,關著燈時顯得格外冷清,他開了客廳的燈,時暮看清了房間全景,很簡單的裝修,除了灰白就是黑,連多余的雜都沒有。
撂下書包,傅云深卷起了袖子:“我記得冰箱還剩兩袋泡面。”
“除了泡面呢?”
“蛋和掛面,還有一些菜。”
“沒問題。”時暮拍拍脯,“你坐著,我下面給你吃。”
Advertisement
“……嗯?”
時暮回味起自己話來,耳一紅:“小小年紀想什麼呢,思想真不健康。”
傅云深眼神茫然:“嗯?”
“……”
,才是思想不健康,齷齪,有罪,完全忘記傅云深是高中生了。
“你、你坐著,我去給你做飯。”
“你會?”傅云深的眼神寫滿了懷疑。
“我當然會,我做飯可好吃了。”
這話不是吹牛,時暮沒啥天賦,就是做飯比較好吃,這點隨了爸,也還好隨了爸,要是媽,下輩子保不準就死了。
時暮翻出圍系上,整理出食材,作絡的搗鼓著那些廚房用品。
傅云深雙手環斜靠著門框,眼瞼垂下,眼睛眨都不眨的看著做飯。
傅云深對做飯這些一竅不通,周六日都是靠泡面過活,由于不喜歡接人,平常也不點外賣,更不會下館子,這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別人在自己家,自己的廚房,自己的面前,做一碗面。
奇妙的。
傅云深抿抿,向來冷清的眉眼中,第一次染上了煙火的暖。
“用我幫忙嗎?”
“不用。”時暮搖頭,“你把碗筷準備好就行。”
“哦。”
他擺好碗筷,乖乖坐在餐桌前等飯吃。
時暮做的面條簡單,但香味俱全,傅云深第一次吃這種家常飯,加上不挑食好養活,吃的格外香。
一碗面下肚后,他突然瞇了瞇眼,說:“你那本漫畫里也有這樣的劇,他們最后好像……”
“噗——!”
一口面嗆在了嗓子眼,時暮捂咳嗽幾聲,表變得格外難看。
“你、你還真看完了?”
他輕描淡寫:“有趣的。”
……有趣??
這位小老弟是認真的嗎?
他單手托腮,目深沉:“最后好像是那個攻洗的碗。”
“……”
這、這小子還懂得攻?
他怎麼了解的這麼全面??
他都這樣說了,這個碗還必須要洗了!事關攻尊嚴!
時暮放下筷子:“我去洗,我去洗。”
他角勾了下,自顧自起上樓:“我去幫你整理一下客房,慢慢洗,不用急。”
時暮嘆了口氣,認命整理好碗筷。
等清洗完畢后,傅云深也收拾好了客房,客房正對著他主臥,估計是怕時暮覺得寂寞,傅云深不知從哪兒搜羅出一只破舊的布偶放在了枕頭前。
“洗發沐浴那些都有,床上是我的睡,沒穿過,你先湊合一下。”
“不用了,睡我帶了。”
“嗯,那你睡吧,晚安。”
“晚安。”
把門反鎖,時暮開心撲到了那張的床榻上,三下兩下了小背心和束縛的假,出手機翻找著容院信息。準備去找個靠譜的地方做日浴,不為別的,就為黑,只有黑了,才有男兒氣概,才能讓傅云深認做大哥!
只是……這些價格好像都有些貴。
看著那巨額數字,時暮疼的關閉了網頁。
算了,太足的時候出去曬曬就好,做什麼貴的日浴,這些都等有錢了再說,實在不行,就等明天出去買一瓶黑油,效果都差不多。
打定主意后,時暮洗漱睡了覺。
這一夜睡的平穩舒服,等第二天醒來時針已指向了八點,翻了個,還有些不愿意起。
睡意朦朧時,時暮約聽見門鈴響起,打了個哈欠,從床上爬起,拉開窗簾,朝外面看著。
日很足,院子里的花兒開的艷,時暮眼角半垂,瞥見進門的年姿清雋,當他抬頭那一瞬,所有的睡意,冷靜全部消散。
傅云瑞。
傅云深的弟弟……過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98 章
女總裁的極品贅婿
絕世兵王變廢物贅婿? 老婆看不上,小姨子瞧不起。 譚浪感覺上天給他開了一個莫大玩笑……
57萬字8.18 29163 -
完結63 章

愛如夏花般璀璨
餘歆檬愛了一個男人十二年,卻被他親手挖了腎,丟進了監獄三年。三年的折磨,一千多個日夜,把她對他的愛消磨殆盡。再次見麵,他紅了眼,她卻微笑著說:“先生,我們認識嗎?”她想遠遠的躲開他,他卻死皮賴臉的纏上了她。 …
5.9萬字8 36173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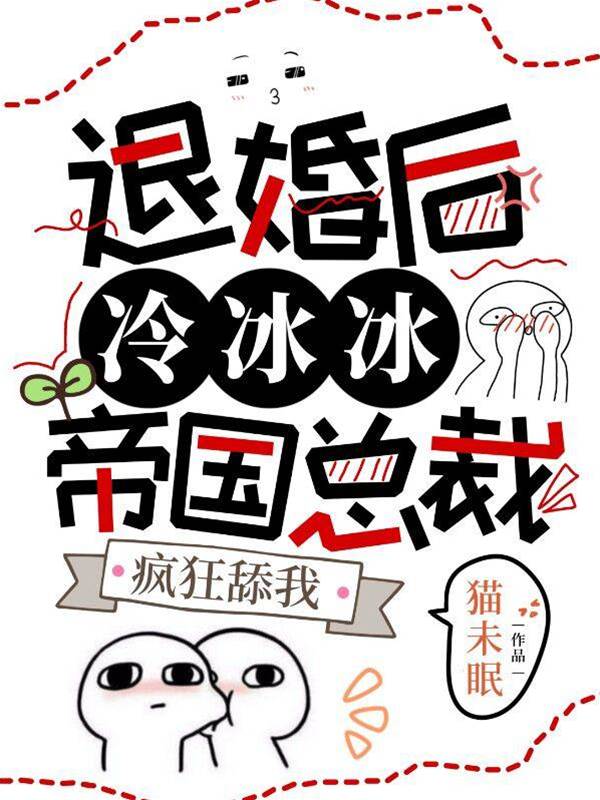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144 章

上位游戲
【嬌軟勾人釣系美人×薄情兇戾太子爺】【曖昧拉扯+上位者發瘋文學+人前不熟,人后猛親】 宋初晚自小便清楚,她是慕家的私生女,上不得臺面見不得光,只能任由與她長相一模一樣的姐姐隨意欺凌。 直到那一日,姐姐因為天生不孕,威逼利誘她成為她的替身,與她的未婚夫祁硯洲圓房,生下孩子。 所以那次密謀過后,她做了一個決定。 讓那個姐姐做夢都想得到的男人,成為她的囊中之物。 * 京圈盛傳,祁硯洲天生薄情,兇戾狠辣,除了他那個白月光,沒人能把他拿下。 宋初晚代替姐姐與他結婚,千方百計接近他,誘他,引他上鉤,卻沒想到這男人一開始不為所動,在她想要放棄時反又被他撩到紅溫—— 怎麼感覺?劇本不對? 她更想不到的是,在做回妹妹、被迫與其他男人訂婚那日,他會氣勢洶洶當著所有人的面握住她的手腕將她帶離現場。 向來矜貴自持的男人第一次失控,將她強制帶進黑暗的角落,抵在墻上吻到窒息。 她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姐夫,你認錯人了,我不是姐姐——” “我知道。”男人的嗓音沙啞低磁,揉著她的手,紅著一雙眼貼近她,“宋初晚,從頭到尾,我都知道。” * 沒有人想到,那年冬天,人人嫌棄的小可憐,成了太子爺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29.2萬字8.18 90 -
完結88 章

頂級新婚
賀氏是燕北赫赫有名的鐘鼎之家,賀徵朝作爲集團話事人,不僅未婚也鮮少有花邊新聞。 溫知禾從未想過這麼一尊大佛,竟會坐在自己面前,提出結婚的意向。 她是灰姑娘,但這位賀先生並不是白馬王子。 他說,他需要一位聽話懂事願意配合的妻子,協議結婚,到期則離。 溫知禾本不願做這差事,直到看見卡上那串這輩子也無法企及的數字。 “有什麼要求嗎?”她問。 面前的男人溫文爾雅,脣邊的笑很淡:“聽話就成。” - 婚後,賀徵朝雖把她當成雀兒逗,對她也確實稱得上有求必應,足以忽視某些方面的高要求。 但溫知禾一直清楚,這場婚姻於他們而言只是各取所需,不平等的關係總會到盡頭。 成婚不到半年,賀徵朝疑似出軌的消息不脛而走,豪門貴婦體驗卡即將到期,溫知禾雖遺憾,倒也沒什麼無法接受的。 當晚下鄉取景前,溫知禾謹慎細微地發消息詢問,是否要提前結束關係。 大雨傾盆,雷轟電掣,賀徵朝從車上下來,撐傘拉起她。淡漠持重,卻又音色溫和:“跑什麼?鞋都掉了。看到我很意外?” - 溫知禾最怕的是卸下溫潤外衣的他,強制,平靜,反抗不得。 而他總是佔據高位,似笑非笑頷首垂眼,箍着她,低聲說:“你要記住這種感覺,離了我,沒有人能給你。” 習慣是件可怕的事,她對他的掌控羞於脣齒卻又依賴、成癮,深入骨髓。
34.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