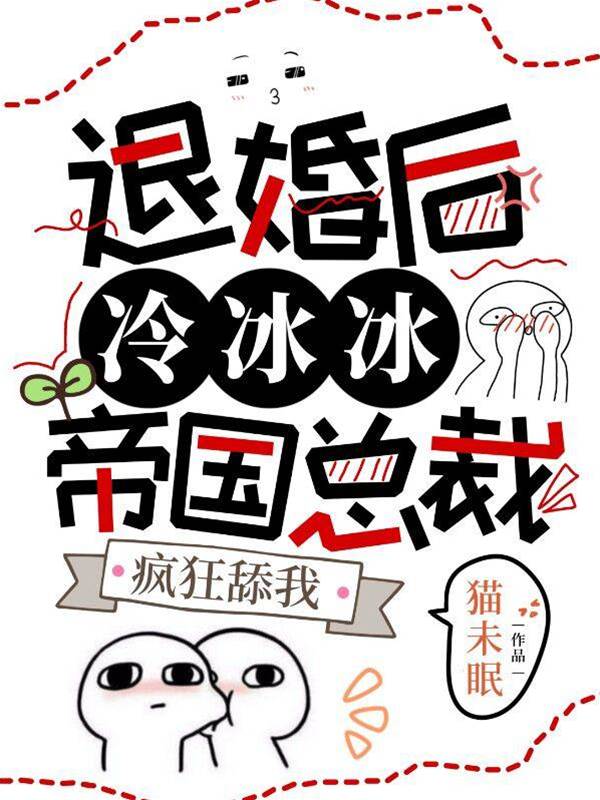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傾盡時光來愛你》 第38章 那就這樣吧(大結局)
他有些頹廢的微垂下了頭。
他送獄五年,奪走了的自尊與傲骨。
他將他的自尊與傲骨給,能回到五年前嗎?回到五年前那個他如命的人。
接下的日子,天天陪著孩子,陪孩子玩,陪孩子學習,陪孩子睡覺,的人生裏,仿佛隻剩下了孩子。
麵對任何人都可以笑的燦爛,唯獨見到他,立刻就會變平靜淡漠的樣子。
隻要他一靠近,就會抖。
秦時霆坐到後車座上時,意外的拿起了當時查到景明月在監獄裏時的資料。
他盯著資料沉思片刻,最終打開……
從裏麵掉出一大堆照片來,他一張一張的看了起來,從最初的平靜,到雙手攥,再到緒激!
每一張照片都是景明月被打的樣子,有幾張是被打斷胳膊的,有幾張是被打傷的,有幾張是腳踩玻璃的照片,剩下最多的就是……被一群人按著紋的……
Advertisement
心狠狠的搐了一下,最後,這裏麵放著一張盤。
他握著盤的手輕輕抖了一下,心口越來越!
最終,他還是將盤放到車上麵自帶的電視裏,畫麵上立刻就出了披頭散發的景明月,正在被人按在水裏,不斷喝著髒水……
畫麵再切換,到了被打的場景……
直到他看完,他整個都繃著,完全沒有了反應,甚至到了秦家,他都不知道,目直直的盯著景明月的視頻。
秦時霆被喚了好幾次,才回過神來。
他匆匆下了車,急步走進房間。
到了房間,他從景明月的後,用力的將抱。
景明月全一陣抖,剛想要反抗,秦時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高傲如他,卻一連著說了三聲對不起,甚至還帶著一卑微。
Advertisement
景明月的心裏猛的一。
秦時霆的聲音又傳了過來。
“你不要原諒我,一輩子都不要原諒我。讓我傾盡時來彌補。”
景明月張了張口,千言萬語,隻是輕輕的“嗯!”了一聲。
————
軒軒的墓碑前。
秦時霆與秦一恒,還有景明月,一家三口第一次同時站在這裏。
“軒軒哥哥,聽說你很媽媽!我也很媽媽,現在,我帶著你的,會加倍的!”秦一恒靜靜的對著墓碑說道。
景明月手兒子的腦袋,臉上帶著寵溺。
“軒軒,害你的人已經都被抓去做牢了,這一輩子可能都出不來了,媽媽現在才來看你,對不起!”景明月說到這裏,微微垂眸。
秦時霆上前一步。“雖然我不是你的親爸爸,但在我心裏,你就是我親兒子,以後,爸爸媽媽和你弟弟會經常來看你。”
Advertisement
三個人就這麽靜靜的站著。
景明月左手拉著孩子,秦時霆手去拉的右手!
景明月卻本能的避開了。
秦時霆卻霸道的將的手牽住。
景明月掙紮了兩下,沒有掙開,也就放棄了。
五年了,的恨意也該消一點了吧,就算是冰山一角,萬事也有個開頭。
就這樣,站在軒軒的墓碑前,牽著孩子,他牽著……
猜你喜歡
-
連載532 章

野中帶勁
【女主尤物美人 男主偏執大佬 瘋批 性張力 追妻不擇手段 強取豪奪 雙潔】(人間富貴花x套路深大灰狼)那夜,她為了活命,被迫爬上了大佬的床。本以為事後就此分道揚鑣,殊不知,他已經暗地謀劃有備而來。一次拍賣會上,他光明正大地將她和未婚夫堵在走廊,往她衣服裏塞房卡。她忍了!直到婚禮當天,新郎出軌的視頻被曝光淪為人人唾棄的對象,她才暗暗慶幸,大仇終於得報。殊不知,一張曖昧不堪的豔照很快將她拉下水……“天涼了,蘇氏集團該破產了!”“雲梔意……”高大挺拔的身影將她籠罩,“你、也該回到我身邊了。”厲閾野,那個與她有過一夜糾葛的男人,找上門來了,沒日沒夜的纏她,寵她。她的仇家被人報複,公司破產,家破人亡。而她,也因一場婚禮鬧劇成了全城的名人。不管走到哪,都有人知道,她是厲閾野的女人。她逃,她躲,藏進每一處犄角旮旯,卻總能被找到……
84.8萬字8 9335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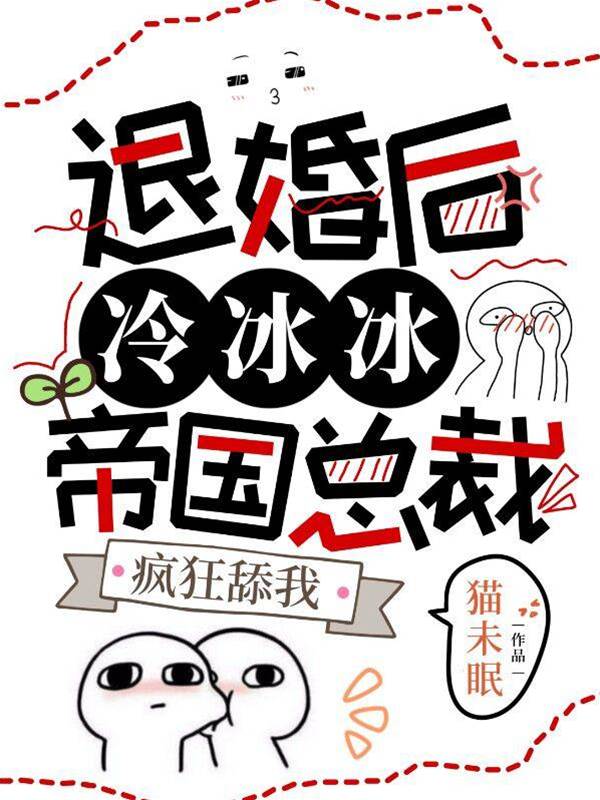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578 章

億萬寵婚:神秘老公狠兇猛
他是A市帝王,縱橫商界,冷酷無情,卻唯獨寵她!“女人,我們的契約作廢,你得對我負責。”“吃虧的明明是我!”某宮少奸計得逞,將契約書痛快粉碎,“那我對你負責!讓你徹底坐實了宮夫人的頭銜了!”婚後,宮總更是花式寵妻!帶著她一路虐渣渣,揍渣女,把一路欺負她的人都給狠狠反殺回去。從此人人都知道,A市有個寵妻狂魔叫宮易川!
106.2萬字8.18 5443 -
完結375 章

我曾嫁給你想到就心酸
一次意外,讓本來陌生的兩個男女不得不奉子成婚。 蘇冉成了宋庭遇眼中不擇手段的女人。 新婚之夜,他冷笑著對她說:“蘇冉,你的目的達到了,可除了宋太太的頭銜,其余的,你休想得到。” 婚后的第一天,他收拾了東西飛往國外去安慰他心愛的女人。 一夕之間,她成了整個安城的笑柄。 一別四年。 他在國外和別的女人雙宿雙棲,幾乎要忘了她這個妻子,還有他們三歲的兒子。 后來,兒子病危,他不得不回國,和她準備生下第二個孩子,用臍帶血來救他。 四年后相見,他對她依舊疏離冷漠,依舊溫暖不了兩顆冰冷的心。 他甚至還不忘提醒她他們在一起的原因。 她冷艷而笑,裝作不在乎,可指甲卻掐進了肉里:“宋庭遇,我比你更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他既然心心念念別的女人,那她就成全他,可當她將簽好的離婚協議書遞到他面前的……
101.5萬字8 4786 -
完結156 章

溫柔掌控
【先婚后愛+蓄謀已久+甜寵+救贖】【外柔內剛古典美人x腹黑陰戾商界大佬】 北城孟家千金孟幼笙冰肌玉骨氣質出塵,臉蛋美得不似人間凡物,被譽為百年難遇的古典美人。 外界傳聞,孟小姐身體嬌弱性情溫和與世無爭,將來要配一個性格同樣溫和的夫婿捧在手心里嬌養才行。 然而,未等孟幼笙婚配,孟家就瀕臨破產,百年家業岌岌可危,為了維持家業于北城名流之首的賀家聯姻。 - 北城人人皆知賀祁言手腕上常年掛著一串小葉紫檀,為人佛口蛇心在商場上更是殺伐果斷,令無數世家名媛望而卻步,把冷淡自持發揮到了極致。 聯姻消息傳出,眾人感嘆兩家聯姻不過是為了利益,可憐了孟小姐這般柔弱仙女般的人兒,落到那位手上怕是要被磋磨死。 直到一年后,孟家起死回生坊間也傳出兩人離婚的消息。 就在眾人翹首以盼時,有視頻流出—— 傳聞中薄情冷血的男人,從身后把孟幼笙圈在懷里,小心翼翼視若珍寶地吻著,嗓音低啞:“笙笙,不離行不行……” 【小劇場】 某天,有人拍到賀祁言在拍賣會上一擲千金拍下天價紅鉆,主持人好奇詢問用途。 男人抬眸,聲線低磁:“哄我太太開心。”
30.1萬字8 1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