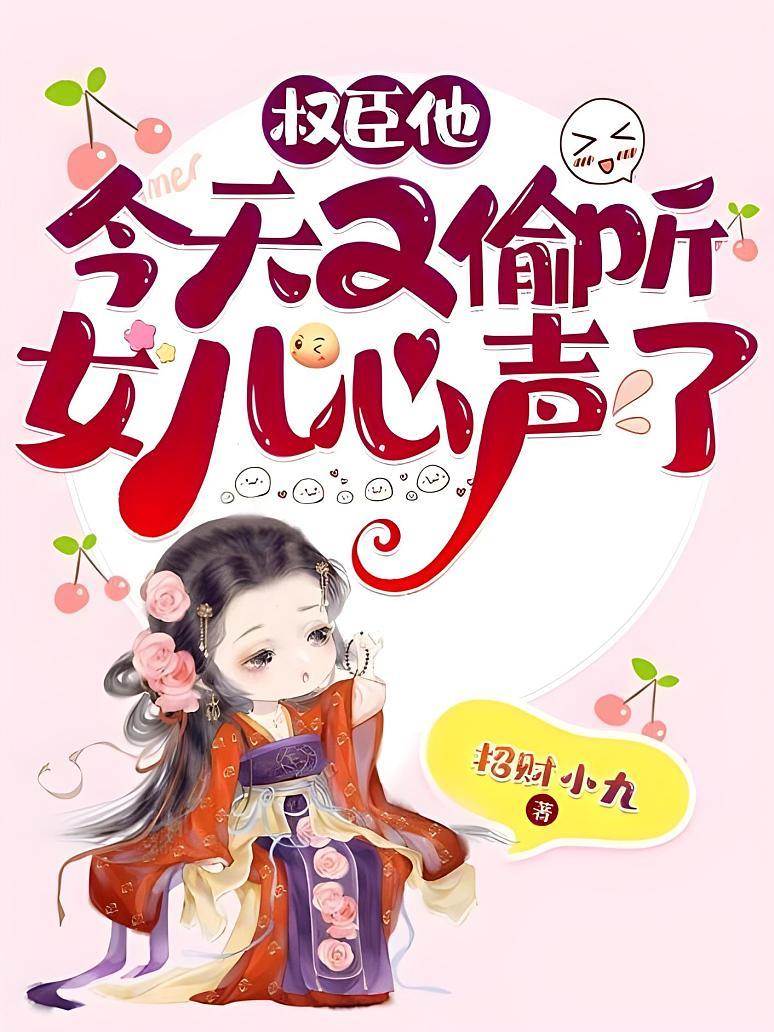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123章 第 123 章
杜仲大概十六七歲, 個頭在同齡人里其實不算矮,只是他彎腰躬背垂著眼睛,加上骨纖人瘦, 量生生矮了半個頭,把自己了一個謹小慎微的模樣。
“這兒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趕走!”
唐荼荼他拉扯了一把,卻沒被扯, 腳下略略后退半步, 便止住退勢。杜仲胳膊上沒二兩, 反而沒下盤穩當, 倒往的方向趔趄了兩步。
“當心。”唐荼荼抓住他手臂扶穩了,“我要進去記一份醫案。”
杜仲皺著眉:“你連醫書都沒讀過,哪里會寫醫案?別胡鬧, 趕出去。”
帳簾旁守著褚家幾個仆役, 都出狐疑目,唐荼荼忙拉著杜仲往帳走, 快說了句“我是王太醫跟前的”。
做事雷厲風行,一白大褂上,醫的架勢也足,褚家仆婦放進去了。
“我看過你們的醫案了。”唐荼荼低聲道:“寫得不夠細致,只寫個病由,畫圖圈出病灶, 手過程只記寥寥幾行——這不行,如果醫經要大量印刷、廣泛傳播, 需得……”
見王太醫站到了病床邊,已經開始給小公爺查了,唐荼荼松開杜仲的手臂:“回頭再說, 等我寫完了給你看。”
“你……”杜仲眉頭展不平。
見師父那頭沒人手,杜仲只好先過去幫忙。
唐荼荼尋了個離帳窗最近的角落坐下,此天最亮,卻也遠遠不夠手,帳篷里采限,門簾又不能敞口,里頭的線都得靠明燭補足。
“怎麼還在咳?!藥怎還沒喂進去!”
劉院判大汗淋漓,奪過醫手中的細銀管,這管子上下細,形似一個袖珍的斗,進病人里,方便喂藥。
Advertisement
可一勺子沒灌完,小公爺猛地嗆咳起來,他分明暈得人事不省的,純粹是咽部反,藥一口沒喂進去,全嘔出來了。
“大人,這可怎麼是好?”
醫驚惶,又不敢聲音大了,怕外頭的褚家人聽見了。有醫機警,瞧劉院判已經慌了手腳,悄悄退出去催請院使大人了。
王太醫皺著眉道:“你再喂他藥,就要嗆死了。”
劉菖臉青青白白,一時間恨不得給自己兩掌。
昨日院使大人本來是委派他去康王那頭的——康王世子狼給咬了,銜下一口來。這傷不算重,可畜生咬傷往往難治,夏天悶熱,弄不好就是淋淋漓漓的一場疽毒,最后還是得送命。
劉菖不敢那霉頭,跟另一位院判調換了差事,他來照管這位小公爺了。
肋骨折了不是什麼要命的病,劉院判也是瘍醫出,早年未宮前治過十幾個這樣的病患,只需正骨復位,再開點強筋健骨的方子慢慢養就是了。
病人泰半能痊愈,數會留下膛凹陷、不能大氣的病,命都保住了,這點小事不值一提。
傷在口,起碼要挨一個月的疼,中間每一回請安脈、每一回調整藥方,都必得他往褚國公府走,一來二去的,方便跟國公府好。
京城誰人不知褚家對這小公爺有多看重,那真是全家人當祖宗養大的,其父褚家大爺管著戶部度支,劉菖了心思,想將長子往里填塞。
可眼下,劉菖汗如雨下,恨斥了一聲:“王常山!你還磨蹭什麼,趕施刀!”
王太醫微闔著眼睛,略略俯在小公爺腔上叩診,他左手五指張開,食指與中指扁平地在小公爺膛上,隨右手敲擊而緩緩移。
Advertisement
如此,在左右兩邊每肋條上篤篤篤地敲了一遍,膛聲音時清時濁。
人都一腳踏進鬼門關了,他竟似在認認真真地弄一把琴!
劉院判氣得倒仰:“你到底能不能治!起開,還是我來施針!拿參片來!”
他手推了王太醫一把,急得沒了分寸,哪里有往常的面樣?
那年杜仲猛地抬頭,他生著一雙極利的眼睛,人又過分清瘦了,套著醫護服,像在地上的一白骨,這麼著死死盯著人,頗讓人慎得慌。
“杜仲!”王太醫喝了聲。
杜仲繃的雙肩松塌下來,抿起,低頭繼續檢查醫箱里的手械。
大帳里里外外匆忙準備著,院使大人帶著兩名醫進來了,聽王太醫說要“剖”,幾人都沒敢應聲。
院使大人視著他:“你有幾分把握?”
王太醫道:“脈細卻疾,上叩擊聲如鼓,下濁音,想是積。”
院使驚道:“怎的不能確診?”
王太醫行醫多年,臉上竟出踟躕來:“……我沒治過這樣的病患,只在老祖宗留下的醫書上看過此例。”
“那怎麼能行!”劉院判失聲起來:“紙上談兵,猜嘗試,那不是草菅人命麼!還不如先止了咳,出積,再用藥仔細溫養著。”
幾位醫再往榻上一看,小公爺一口一口的沫往出嘔,手臉指甲發紺,也失了溫,都是衰竭之兆。
溫養需要工夫,咳咳這樣了,什麼靈丹妙藥能養得住?
院使神變了幾變,終于拿定了主意:“行,按你說的開,治好了,我親自為你請功,治不好唯你是問。”
王太醫愕然,苦笑了一聲。
他本綿,在太醫院這麼個染缸里浸多年,也不改本心,年時背過的醫德訓誡全下了口頭,融了心頭,不矜名,不計利,自認配得起“大醫誠”這四字。
Advertisement
同僚立了功了,升上去了,又貶了了,他始終在這麼個不尷不尬的位置上,看盡宮里人冷暖。
爭功時,沒力氣爭,攬責時也沒力氣推諉了。
可他不敢說的,杜仲敢說。
“你們欺人太甚!”杜仲深深了幾口,嗓音尖細,似被死死掐住了脖子:“師父,咱們不治了,他們灌藥溫養去!”
像一掌呼在臉上,唐荼荼在兩步遠的地方坐著,都替他師徒二人窘迫起來。
順序錯了……想:順序全錯了。
灌了一晚上的湯藥,此時想起來查了;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想起來開刀了;一腳踩在鬼門關上了,要從頭開始找病灶了。
而這看上去很明事理、拿得起主意的院使,也是個不敢擔責的糊涂蛋。
唐荼荼想起前日在校場上,摔角比賽時那個頭水腫窒息的老太太,那是宮中姚妃的親娘啊,九皇子的親姥姥,盛朝最尊貴的那一小撮人之一。
這位院使問也不問,就喚王太醫上前開刀。
萬一那一刀下去要了老太太的命,是誰的責任自不必說。
可選擇開刀還是保守治療,這不該是由大夫拿主意的。他們了一個環節:通知家屬——人家全家人都在外頭,尚不知,生死大事,治療方案、中風險,都得讓人家家屬聽明白。
唐荼荼驀地掀帳出去,在幾排褚家親屬中環視一圈,揚聲問:“您家里誰主事兒?太醫爭執不下,需要您家拿個主意。”
褚家人七八舌吵了起來。
“都到這關頭了,太醫還爭什麼?”
“這不是庸醫麼?咱們又不懂,能拿得了什麼主意?”
唐荼荼一眼掠過他們。
直系親與隔了房的叔伯姑嬸區別就在于此,一家人七八舌,而全得需被兒架著、才能勉強站住的大夫人,竟是第一個走出來的。
“我是泰安他娘!姑娘與我說。”
褚大人和他家的老夫人也跟著應聲,幾人朝著醫帳走近幾步,唐荼荼飛快把兩種治療方案講了一遍。
語速很快,搶時間似的,聲音卻四平八穩。分明是個屁也不懂的外行,可這時候但凡是個口齒清晰、能把話說清楚的,都會有種人信賴的魔力。
一聽要“開”,褚大人咬牙點了頭:“藥灌不進去就別費工夫了,不要耽擱,趕開刀!”
大夫人哽得說不出話,卻隨夫君一同點了頭。
帳篷里頭幾位太醫聽著了外邊的說話聲,院使和劉院判連忙掀帳出來,細細解釋。
瞧他們啰啰嗦嗦、說得晦難懂,還沒這胖丫頭說得直截了當。褚家老夫人重重一砸拐杖,銅杖底叩出一聲清脆的嗡響,鎮住了幾人的話。
“不必再說了。”老夫人沉聲道:“泰安命里該有此劫,救得救不得,都是他的命,王太醫下刀罷。”
這便是允了,沒有后顧之憂,能踏踏實實地開刀了。
唐荼荼長松了口氣,鉆回了帳篷。
杜仲愣愣地看著,低頭,悄悄眨去了眼里的酸意。
屋里眾人再次凈手,片刻工夫進進出出,閑雜人都出去了。手臺是拿兩張矮塌臨時搭起來的,院使、劉院判,并上兩位醫、兩位醫,圍著臺子站開。
帳窗另一側也停駐了兩人,和唐荼荼之間只隔著一張小桌。掃了一眼,紗窗低,而日頭高,左邊這兩人一坐一站,只能照亮半,看不著臉。
沒顧上細看,手已經開始了。
這對師徒不知磨合了多年了,不待師父說,杜仲立刻接手消起毒來。
唐荼荼拔下竹錐筆的筆蓋,蘸墨在小本子上寫字,盡量抓住王太醫吩咐杜仲的關鍵詞。
——病人咳沫,寒戰,呼吸短促,面慘白,間歇休克。觀察到反常呼吸運,吸氣時肋骨上舉,廓反而下陷,太醫懷疑,準備開。
——辰時一刻,開刀剖。
從辰時一刻開始,唐荼荼腦子里和鐘表幾乎無差的讀秒,逐幀流轉起來。
的時間觀念強到可怕,以前規劃院的同事們開玩笑喊“人形自走鐘”,唐荼荼腦子里似埋了一顆準的讀秒計時,只要潛意識里開始留意時間,半小時時間段里的秒數誤差,上下浮不會超過十秒。
且讀秒的同時,能一心二用。
唐荼荼盯著手臺,視線在手臺和自己本子上快速替,每看一眼,在本子上落兩筆,落筆時自系。
跟杜仲說的那話不假,這陣子翻看王家祖上那位外科大牛所載醫案時,蒙蒙昧昧地意識到一個問題。
本朝大夫記錄的醫案,往往只是一紙方劑,醫患雙方手頭各留一份,要是病人吃出了病,府依方查案。
那位外科大牛是后世來的,記錄醫案的辦法要高明得多,每篇醫案著重描述了病人癥狀、病診斷和分析,手過程,乃至后保養和用藥記錄,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
唯一的憾,是他記錄的手過程不夠詳實,中每個步驟都是文字版本。所有配圖都準地畫出了人結構和病灶位置,下刀和合手法,一場手配3到5張圖,靜態地分解了手步驟。
可歷史上,刨開零星的個例,古醫整從藥草走向針刀的這一步,足足了幾千年。
如果沒有師父口口相傳、手把手地教,天下沒有大夫敢拿著靜態、零碎的幾張圖片,對一個活生生的人下刀子,敢像王太醫這樣,眼也不眨地從活人側肋破開皮。
但如果,能讓手過程態地呈現出來……
唐荼荼沒見過后世的手記錄是什麼樣,可末世時,為了避免醫患沖突,大型手全程都會錄像,院方、患者和家屬都可以查看。
這種手影像會作為珍貴的教學資料,用AI、VR、超算技搭建出骨架來,充實智能數據庫,做出全套虛擬的手系統,方便醫學生模擬演練。
拆解手中的每一個小步驟,重復學習,對比別的治療方法的優劣……
這是數字醫學。
有龐大的數據智庫輔助,能迅速擴充醫生隊伍,填補醫護資源的不足。
不止醫科,所在的時代,各行各業皆如此。
猜你喜歡
-
完結345 章

火鳳凰
穿越醒來,被X了?而且肚子里還多了一個球?一塊可權傾天下的玉佩掀起亂世風云,太后寵她無度目的不明,皇帝百般呵護目標不清,庶妹為搶她未婚夫狠毒陷害毀她清白?那她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她堂堂影后又是醫學世家的傳人,更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特工身份,她…
73.9萬字8 71033 -
完結275 章

首輔大人的小青梅[重生]
【嬌軟小青梅x表面如圭如璋,實則心狠手辣的未來首輔】 【女主篇】:阿黎九歲那年,隔壁來了位身受重傷的小郎君。小郎君生得眉目如畫、俊美無儔,阿黎偷偷喜歡了許久。十四歲那年,聽說小郎君被人“拋棄”了。阿黎壯著膽子跑去隔壁,對霍珏道:“你別傷心,她不要你,我要的。”話落,她被霍珏丟出門外。明媚春光下,小郎君看她的眼神比開陽湖的冰垛子還冷。姜黎委屈巴巴地走了,沒兩日又抱著個錢袋上門。只是這一次,門後的小郎君卻像是換了個人。他靜靜看著她,深深沉沉的目光彷彿邁過了漫長時光沉沉壓在她身上。良久。他勾住阿黎肩上的一綹發,素來冷漠的眉眼漾起淡淡的笑,柔聲問她:“阿黎那日的話可還算數?”阿黎:“算,算的。”阿黎一直覺著霍珏是自己追回來的。直到後來,她翻開一本舊書冊,裡頭藏了無數張小像:九歲的阿黎、十歲的阿黎、十一歲的阿黎……一筆一畫,入目皆是她。阿黎才恍然驚覺。或許,在她不曾覺察的過往裡,霍珏也偷偷喜歡了她許久許久。 【男主篇】:霍珏身負血海深仇。上一世,他是權傾朝野的權宦,眼見著仇人一個個倒下,大仇終於得報,可他卻後悔了。他只想找回那個在他淨身後仍一遍遍跑來皇宮要將他贖出去的少女。再一睜眼,霍珏回到了十六歲那年。門外,少女揣著銀袋,眨巴著一雙濕漉漉的眼,惴惴不安地望著他。霍珏呼吸微微一頓,心口像是被熱血燙過,赤赤地疼。指尖輕抖,他開口喃了聲:“阿黎。”從不敢想。踏遍屍山血海後,那個在漫長時光裡被他弄丟的阿黎,真的回來了。 【小劇場】:某日霍小團子進書房找他爹,卻見他那位首輔爹正拿著根繡花針補衣裳。小團子一臉驚恐。他爹一臉鎮定:“莫跟你娘說。你那小荷包是你娘給你新做的吧,拿過來,爹給你補補,線頭鬆了。”後來,長大後的小團子也拿起了繡花針。只因他爹下了命令,不能讓他娘發現她做的衣裳第二天就會破。小團子兩眼淚汪汪:長大成人的代價為何如此沉重?嘶,又紮手了。
43萬字8.33 95745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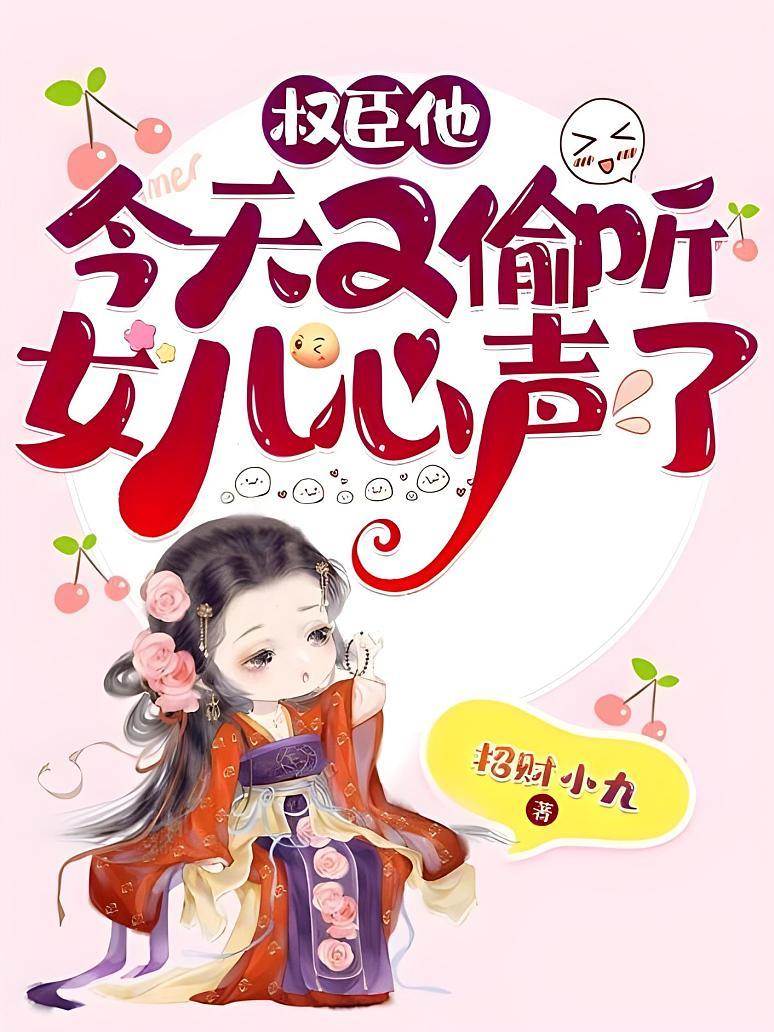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
完結256 章

如果賤婢想爬墻/替身男主:霸道丫鬟必須愛
大公子高大威猛,已有妻室,是個有婦之夫。 二公子心狠手辣,滿眼陰戾,是個不好惹的病秧子。 只有三公子溫潤如玉,文采斐然,是萬千少女的一場美夢。 爲了成功從丫鬟升級爲三公子的頭號小妾,寶嫿想盡一切辦法勾搭主子。 終於某天寶嫿趁虛而入,從此每天快樂得迷醉在三公子身邊。 直到有天晚上,寶嫿難得點了蠟燭,看見二公子敞着領口露出白璧一般的肌膚,陰森森地望着自己。 二公子笑說:“喜歡你所看見的一切嗎?” 寶嫿轉頭朝河裏衝去。 後來寶嫿被人及時打撈上來。 二公子像每個讓她迷醉的晚上一般把玩着近乎奄奄一息的她的頭髮,在她耳邊溫柔問道:“說你愛誰?” 寶嫿結巴道:“二……二公子。” 二公子掐住她脖子森然笑說:“三心二意的東西,誰準你背叛我弟弟?” 寶嫿白着小臉發誓自己有生之年再也不勾搭主子了。 對於二公子來說,遇見寶嫿之後,沒有什麼能比做其他男人的替身更快樂了~
38.2萬字8 1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