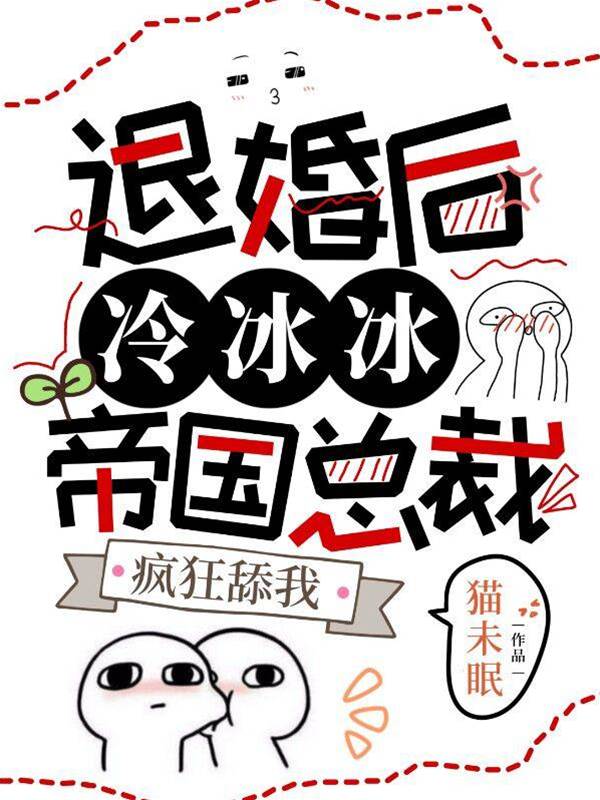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度今宵》 第70章 豌豆黃 突然膽怯的理由
第70章 豌豆黃 突然膽怯的理由
-
隔日清晨, 天氣昏沉得厲害,山間薄霧朦朦,縷縷系在青杉古松之間, 一眼去, 由眼到心的寒涼。
今宵穿一黑從公墓臺階走下來, 一步一頓,心不在焉。那單薄瘦削的軀被一冬裝包裹還顯纖弱, 好似一張薄薄的紙片,沁滿濃墨,風一吹就會輕飄飄地翻過去。
祭拜結束, 與父親說了很多話, 沒讓沈修齊聽。
此時同樣穿一黑的男人站在臺階底部,側一排雲杉森綠, 襯他一清冷,深邃眉眼被冷霧隔絕, 忽地想起父親剛去世那段時間。
因徹夜難眠,整日傷心,的狀態非常不好,整個人渾渾噩噩的, 可能前一秒還認認真真畫著畫, 下一秒眼淚就洇紙上的墨痕, 一幅畫就這麽廢去,被團一團一隨意扔到地上。
那段時間, 一有空就來墓園, 有時候是清晨,有時候是黃昏。跪坐在父親墓前,也不說話, 就癡癡地著墓碑上的照片流淚,直到眼淚流幹了,雙跪麻了,才拖著疲憊至極的子一步步往下走。
有一日天氣熱,來時沒吃早飯,已經是最後兩步臺階,卻突然暈眩,兩眼一黑就往下摔去。
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興許幾分鐘,興許更久,無人發現摔倒在地,醒來周圍只有一個人。
雙膝都摔破了,掌心也見了紅,忽然回頭,隔著林與遙不可及的距離坐在地上自言自語:“怎麽?你不想讓我來,就故意絆我一跤嗎?今霖?”
著墓碑的方向又哭又笑又罵:“你好狠的心吶今霖。”
哭夠了,麻木了,再站起來,拍拍上的塵土,一瘸一拐地離開。
Advertisement
那天之後,再沒來過墓園,恍眼已是半年多,滿山寂靜依舊,只在階梯底部多了個人等。
忽然加快腳步朝下跑去,沈修齊心中一,直慢點慢點,卻毫不減速度,臨到最後兩三級臺階,忽然縱一躍,像一尾小魚,力一擺,輕盈地跳進了他懷裏。
“你會一直接住我的,對嗎?”
他衫微涼,鼻息溫熱,在的脖頸地吻,明明靜立著不,他的氣息卻如跑完一般沉。
“當然,”他說,“我會一直接著你,穩穩接著你。”
今宵腳尖點地,平穩著陸,雙手卻還吊著他脖頸不放,看進他雙眼時,忽然疑:“你怎麽看起來有點張?”
“怕你摔了。”
沈修齊牽著往墓園外走,步態輕盈,全然不見往日從這墓園離開時的沉重。
“之前你讓我往樹下跳的時候可不是這麽說的。”
沈修齊的手,恢複了一貫輕松的笑:“要是讓你看見我後怕豈不是壞了我的形象?”
今宵哼哼兩聲:“沈先生的形象在我這裏早就壞掉咯。”
“是嗎?”沈修齊饒有興致,“現在是什麽樣了?”
今宵張口就來:“香,竊玉心,平生風流難休,獨春宵。”
沈修齊失笑,手過跑的發,誇有水平。
今宵睇他:“不愧是沈先生,被人當面揭本還面不改心不跳,您才是有水平吶。”
他收回手,笑得寵溺:“但你這說的不準確,得改‘香,竊玉心,平生風流難休,獨今宵’才對。”
一句逗趣話被他說了骨的表白,今宵嗔他一眼,牽著他的那只手悄悄收了幾分。
上了車,今宵掉外套依到沈修齊懷裏,問他要不要去看媽媽。
Advertisement
昨夜他從老宅回來,對的興致一如往常很高,可低迷的緒瞞不過的眼睛。他習慣了沉默,很會讓緒外顯,那夜在槐安居忽然將結婚口而出是意外,唯一不變的,是他強烈的念。
水汽繚繞的浴室裏,甜香彌散,熱水從頸後淋下來,滴滴答答沖擊薄弱的皮,像是一場黏稠的太雨,讓仿若置熱帶雨林,空氣重,息困難。
為找一個恰當的高度與他配合,沈修齊將塌陷的腰肢一遍遍往上提,繃了足尖高高踮起,雙手撐在浴室玻璃,拂一層薄薄霧氣。
後因高度實在不匹配,蹙著眉心輕輕喊疼,他便退出停下,抱著一遍遍安。安到最後他擡高一條,被抵在冷的牆,仍是繃了足尖想要盡量往上拉開距離,稍稍洩一點力,就要潰敗在他滾燙的舌裏。
第二次被放在鋪好浴巾的置櫃上,沈修齊打著幫塗的旗號將渾上下都遍。
浴室鏡忘了開除霧,昏影朦朧,他扣著的腰與,好幾次都覺自己就快從置櫃邊沿下去,他又擡著發抖的雙幫緩解酸麻。
鏡面水汽一寸寸往下沉,第一次目睹自己時的緋紅神態,懸空的雙足一搖一搖,的長發將他手臂纏繞,像與他共生的藤蔓,他盛則生,他衰則亡,一共生,不死不休。
事後想起來,他緒不高時便是這樣,整夜埋頭苦幹,不發一言。
扶著他側臉去輕吻他角,期待著他的回答,他卻說:“不必了,每到我母親忌日,妙喜寺都會閉寺一日為我母親設法會,到時候再去不遲。”
今宵分辨不清,不知他是因思念母親還是別的什麽,他不願提起,也不追問。
Advertisement
直到晚上,永嘉趁著沈修齊洗澡的時候端著熱牛來書房找,說是要看畫畫,實則是向報。
他說,昨夜胡旋小姐一家都去了老宅赴宴,氣氛很是融洽熱鬧,叔叔甚至與胡旋小姐獨了一段時間,看不出他心好壞,更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麽。
話說到最後,永嘉湊上前撚著擺,神裏著幾分不屬于他這個年紀的焦急,還說:“嬸嬸,你別讓胡旋小姐把叔叔搶走好不好?”
今宵思緒一頓,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
放下了畫筆,手將永嘉拉到前來,想了想說:“我和你叔叔如果走到需要我去爭去搶的地步,那證明你叔叔已經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也無法與我在一起了。不過我會盡力去維護我與你叔叔的這段關系,也會好好他,但我無法確定未來會發生什麽樣的事,興許你叔叔不會像現在這樣我都有可能,如果到那時候,你也不必傷心,我和你的關系永遠不會變,你隨時都可以來找我,知道嗎?”
今宵不確定永嘉能不能聽懂的話,又能聽進去多,沒辦法去承諾自己做不到的事,只能盡力去把握當下擁有他的時刻。
永嘉顯然是聽懂了,在瞬息之間紅了眼睛,子往前一傾就來抱,埋在肩膀就開始流淚。
今宵這時候才知道後悔,撒一個小謊就能哄他開心,何樂而不為?這時候再想去哄,便已經難了。
輕輕拍著永嘉聳的背脊,低聲安著:“我會和你叔叔好好在一起的,我也會努力爭取,好嗎?你叔叔馬上就洗完澡出來了,別讓他看見好不好?”
靠在肩膀哭泣的小男孩悶悶嗯了一聲,說不哭,便自己站著抹了兩把眼淚,瞧著可憐得很。
今宵紙給他了淚痕,這時隔壁傳來腳步聲,趕推推他:“快跑快跑,你叔叔來了。”
永嘉反應迅速,怕被沈修齊看到拔就往外跑,兒顧不上臉上的淚還沒幹。
沈修齊走出主臥的時候,看到的就是永嘉一溜煙兒跑遠的場面。
書房門開著,線比走廊亮個幾度,他走上前,今宵正在收拾桌面的畫,擡手撳滅臺燈,起就朝他走過來。
“怎麽了?”他靠在門邊。
今宵笑笑:“沒什麽啊,永嘉來看我畫畫,看時間太晚了,怕你出來說他,就趕跑去睡覺了。”
沈修齊視線落在桌面那杯完好無虞的牛上,又注意到肩膀那片詭異的痕,他很確定,今宵在撒謊。
凝神間,今宵已經走到門口,擡手關了燈就來抱他,展沖他笑時,眉目含。
“我們也去睡好不好?”
他擡手一掐腰將抱起來,任由靠在肩膀,一步一步朝主臥走過去。
關了燈躺上床,今宵翻往他膛趴著,什麽也沒做,只是牽著他的手,靜靜聽他的心跳。
昏暗裏沉默愈發漫長,呼吸一起一伏間,逐漸趨于均勻,就在今宵被困意裹挾無法掙時,耳朵的腔傳來一點低沉,他在說:“怎麽不和我說說?”
今宵懵懵的,問他要說什麽。
他反問:“永嘉都跟你說了是嗎?”
輕輕笑,說:“是的。”
似乎是的反應出乎了沈修齊意料,他略略撐起了上半,半靠在床頭,今宵也跟著坐了起來。
沙發邊的小夜燈被阻擋了不線,今宵睡意淡褪了幾分,在昏暗裏用眼神描摹他此刻的模樣。
他忽然正,眸中蘊著散不開的霧靄,給了他以為需要的肯定。
“我永遠都是你的。”他這樣說。
今宵忽然失笑,那樣的笑意,只會出現在醉酒人的邊,被酒麻痹了理智,一開口,說的是真心話還是瘋言瘋語,人分辨不清。
說:“我知道。”
這樣的肯定配上這樣的笑容,的確讓沈修齊不解。
今宵知道他在想什麽。
擡手勾住他脖頸,靠在他肩膀喃喃低語:“我不說,并不是我不在意,我在意,也害怕有人會將你從我邊搶走。興許我哭一哭鬧一鬧,你會更在乎我一點,可我不想那樣做。”
“你給了我那麽多肯定,給我吃了那麽多定心丸,那我也想為你生命裏無比堅定的那一部分,我不想讓你那麽累,既要面對家庭的重,還要時時刻刻照顧我的緒。我和你在一起很開心,我想把這種驗也帶給你,讓你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開心,沒有煩惱。”
“不要說這種話,今宵。”
他忽然氣息很重,像是緒抑已久被這段話劃開一大條口子,部的氣爭相往外瀉,連帶著他的也在微微發。
擡眼,想要去分辨他此刻的緒,眼前卻是一片昏蒙,看不清。
“你這樣......”
他的聲音突兀地停滯了一下,說:“會讓我覺我隨時會失去你。”
今宵突然心,心髒猛地一,想起沈泊真同說過的那些話。
他的母親,在騙他外出買豌豆黃的那一日,便是如這般輕言細語,溫嫻靜,好似生活平靜好,多一份豌豆黃的甜,會更增進他們的母子誼。
沒想到滿心歡喜等來的,是驟然跌崖底摔得碎骨的劇痛。
料想他的母親在哄他離開的那一刻,一定是給出了這輩子能給的、最後一點點。
這樣的,便為了他現在面對的與堅定時,突然膽怯的理由。
竟不知,他心的傷痕從未愈合。
忍住了想哭的沖,努力笑著去逗他:“沈修齊,你是狂嗎?非要我折磨你嗎?”
“嗯。”他笑著說,“為今宵小姐當牛做馬是我榮幸。”
今宵攀著他肩膀去咬他的,本是輕輕一銜,想一想又加重了幾分力道。
松開時,問他:“疼嗎?”
他說:“一點點。”
騎在他上虛聲恫嚇:“那你可得記清楚了,下次再讓我知道你私下跟別的人見面,可就不止這一點點疼了。”
“好。”
他抱著翻,被他住深吻。
神思往外游走時,突然困。
究竟要用什麽樣的方式去你呢?沈修齊。
猜你喜歡
-
完結229 章

那就跟我回家
父母雙亡,知眠孤單長大,直到她遇到一個狂妄不羈的少年,成爲她生命中唯一的光。 她被他領回家,和他戀愛,一腔愛意卻只換來他對狐朋狗友說:“養只貓挺好玩兒的。” 那晚暴雨夜裏,她拖着行李箱離開。 她剛走時,朋友問起,男生只滿不在意:“鬧脾氣而已,過幾天就回來了。” 沒想到,她一走就再也沒回來。 - 段灼,某類生存競技運動某隊隊長,所有人都知道他右手手腕口上有個刺着“ZM”二字的紋身。 有朋友問這有什麼特殊含義嗎,他沉默後,自嘲一笑: “我最愛的。” “但弄丟了。” 直到有人看到他出現在知眠的漫畫展上,大家恍然大悟,然而問起知眠,對方只是淡笑:“我不認識段先生,ZM可能是他養的一隻貓呢。” 晚上,段灼把知眠困在車旁,他眼底血點赤深,試圖拉住她:“九兒,跟我回家。” 知眠往後退了步,看着他,神色平淡:“我早就沒有家了。” - 段灼領隊拿到世界冠軍後,幾天後記者就拍到商場裏,他牽着個烏髮紅脣的姑娘。 女生咬了口冰淇淋,他吻上她的脣,冷厲的五官卻滿了溫柔寵溺。 當晚,熱搜爆炸,段灼換了條置頂微博: “這輩子我吻過的,一個是槍,一個是你。前者是夢想,而你是信仰。@知眠”
33.5萬字8 15812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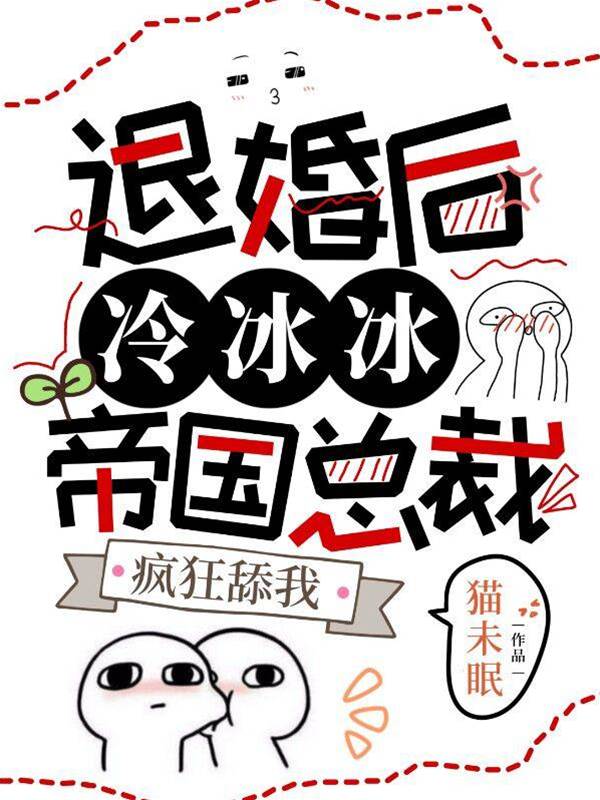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709 章

玫瑰美人
【港城商圈大佬X明豔玫瑰美人】【婚戀 豪門 極限拉扯 占有欲強 暗戀成真 年齡差】許歌是港圈頂級大佬嬌養長大的女人。她乖巧也驕縱。直到他的未婚妻出現。她被他親手放逐國外。他說:“走吧,離開港城別再回來,別逼我親自送你。”他給了她十年寵愛卻又盡數收回。再見麵。她紅唇勾人作者:“躲什麼,以前我都睡在你懷裏……”他表情冷淡,不為所動。背地裏,卻狠戾宣言:“敢動她,我要你們的命!”
126.6萬字8.33 156915 -
完結343 章

夫人,顧總又在求復婚了!
結婚三年,顧妄川白月光回歸,提出離婚。蘇渺死死捏著孕檢報告:“倘若我不愿意呢?” 顧妄川卻與她說:“蘇小姐,請遵守契約。” 蘇渺血染白裙的那天,絕望的簽上協議,遠走高飛。 待她高調回歸的時候,卻被顧妄川抵在墻角,無路可退。 “顧太太,該回家了。”
60.7萬字8 111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